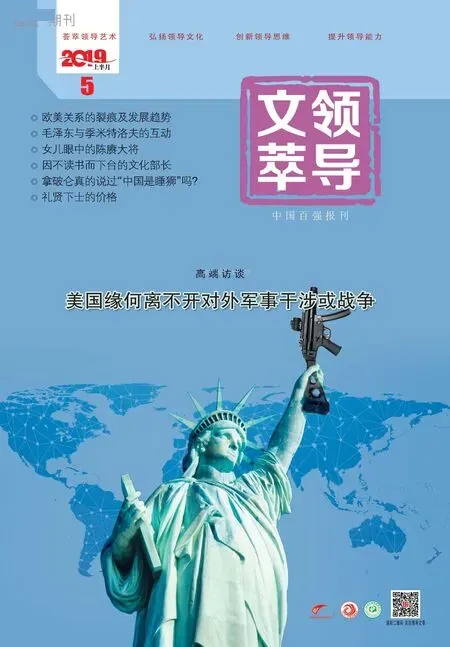深切懷念范式人同志
1983年春,我有幸認識范式人同志。當時我在壽寧縣委黨史辦工作,為征集、編寫壽寧黨史,多次赴北京拜訪葉飛、范式人、曾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范老是壽寧同鄉,我們在京的工作和生活均遵他指示安排。當時范老已年逾古稀,健康欠佳,但無論是嚴寒冰雪還是酷暑烈日,他每次都按約定時間,從國務院機關宿舍驅車到郵電部招待所,給我們談閩東黨史,幫助我們修改、訂正收集到的黨史資料。因路途較遠,范老中午不回家、不休息,與我們暢談革命歷史,暢談改革開放,暢談人生經歷,暢談家鄉變化,一談就是一整天,一談就是一星期。在范老的悉心幫助下,1983年11月,我執筆完成了約25000字的壽寧黨史資料——《范式人同志談壽寧黨史》。
在數次拜訪范老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范老對中國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對黨史征集工作的高度重視,對家鄉發展的深切關心,對青年干部的親切關愛。與范老的交往,激發了我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比敬仰。雖然時間已經過去26年,想到那段時間和經歷,依然歷歷在目,感受至深。
范老尤其關心革命老區的建設和發展,經常仔細詢問許多老區基點村的情況。在拜訪范老之前,我曾在壽寧革命老區調研一個多月,全縣的老區基點村幾乎走遍,老區的貧困狀況十分清楚,因而能夠為他提供大量準確、翔實、有分析、有思考的資料和情況。范老對我們關心老區、深入貧困老區基點村調研感到十分滿意,對老區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也由衷地高興,但對絕大多數老區基點村依然貧困則倍感憂心。他說,我們共產黨搞革命,老區人民作出了多大的犧牲啊!老區發展不起來,我們愧對老區人民,我們不能安心啊!他還反復叮囑,你們這些年輕干部要多想老區,多為老區人民做事。
范老對年輕干部為老區建設作貢獻寄予厚望,但后來我在工作選擇上卻違背了他的意見,至今想來,依然深感內疚。
我于1982年7月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分配在壽寧縣委黨史辦。1983年底,因上海復旦大學推薦,福建省委黨校兩次派人到壽寧聯系調我。作為一個連助教職稱都不具備的普通大學畢業生,能受關注,我決意調往黨校。開始縣委不放,由于時任福建省委黨校副校長的季德吉同志在寧德行署吳副專員陪同下親自到壽寧協調,最后才同意放我,并將我的人事檔案寄往省委黨校。鑒于1984年5月寧德地區要舉行閩東蘇區成立五十周年慶祝活動,范老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將回閩東參加慶祝活動,壽寧縣委與省委黨校商定,待我協助做好慶祝活動有關工作后再去報到。1984年春赴北京拜訪范老時,同行的王道亨同志對范老說起我調動一事,范老當即表示,不要去黨校,還是應該留在壽寧,為老區人民做事。
1984年5月初,范老回閩東參加慶祝活動,在到達福安以及隨后返壽寧老家的行程中,縣委安排我跟在范老身邊,協助安排行程活動和記錄范老講話。行程即將結束時,范老小范圍會見時任寧德地委書記呂居永同志和時任壽寧縣委書記李林清同志,我也在場。在他們三人談完工作之后,范老談及我的調動之事。他明確說,王宜新不要走了,省委黨校方面他去說,請何若人同志(時任省委常委兼福建省委黨校校長)不要到山區調人,山區需要有知識的干部。至于留下來之后的工作怎樣安排,請地委和縣委考慮。盡管我知道范老對我調動一事的態度,但在這樣的場合、以這樣的態度、表達這樣的意見,確實出乎意料。在當時,中顧委委員范式人同志能為一個干部說這樣的話,那是多少人熱切盼望的啊!然而,我調往省委黨校的意向已定,確實不希望他講這樣的話。
范老離開閩東后,我要求辦理調動手續,縣委領導說,范老有話,我們不能放。只有范老同意,才能走人。為此,我兩次致信范老,坦言因大學畢業分配的曲折經歷,自己希望專心從事專業工作。我還在信中引用蔣學模老師的一句話——“部長只有一個,教授則可以很多”,我相信自己專心致志從事專業工作,將來有可能成為福建省委黨校的教授。然而,時間過去三個多月,未獲答復。到了8月,時任福建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室副主任的李光榮老師多次來電催促我盡快成行,并說再不去報到,可能將我檔案退回壽寧。萬般無奈,我第三次致信范老,除了繼續表明自己希望從事專業工作的心志,還寫下了一段相當無理的話。我說,您希望我為老區人民工作我理解,但不該勉強我放棄專業。我還說,您的子女范希健、范希耿也是老區人的后代,您能勉強他們回壽寧老區工作嗎?在十分急迫心態下,未及細想就將信件寄出,隨后又萬分后悔——深感這些話不僅辜負了范老的期望,還傷害了這位可尊可敬的長者。但木已成舟,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歉疚。沒想到,兩三周后,壽寧縣委組織部就通知我辦理調動手續,并說是范老給有關領導寫信,同意我調往省委黨校。我感激范老的寬容與理解,想要致信道謝,卻無勇氣提筆。
同年12月,我作為福建省委黨校助教到北京大學進修人口經濟學,期間不敢主動去拜訪范老,只是給他掛了個電話,在致問候的同時,向他報告已經調到省委黨校工作。范老說他早已知道,并熱情邀請我到他家中見面。我也想找機會當面向他道歉,就擇日前往拜訪。進他家門時,茅玲同志就對我說范老身體不好,談話時間不能超過15分鐘。可見面之后,范老談興甚濃,從壽寧談到福建,從黨校談到北大。我多次接近于講到自己的歉疚,但他總是把話題岔開。談了一段時間之后,我幾次表示不能再影響他休息,該走了,可范老依舊侃侃而談,絲毫沒有倦意。他特別告誡,既然選擇到黨校,就要安心黨校工作,當好黨校教師,要成為優秀的黨校教師,成為黨校教授。雖然這目標在當時說來是高不可及,但我還是承諾一定努力做到。談話持續近兩個半小時,范老不讓我找到道歉的機會,并留我吃晚飯。臨走,還要我代他向過去的老部下——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程序同志、省委黨校校長何若人同志以及省委黨校老領導何山、田若等同志問好。同樣抱歉的是,由于當時我只是省委黨校的一名助教,除了幾年后熟識何山同志,對他講起范老及問候外,范老給其他同志的問候都沒能轉達。
1986年10月31日,范老因病逝世。我在內心默默哀悼這位可尊可敬的長者——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深切關心老區人民、深情關愛我的長者。
雖然范老離開了,但范老對我的關愛與期待,特別是他那大海般寬廣的胸懷,對年輕人狹隘和冒失的寬容,無時無刻不激勵著我,無時無刻不鞭策著我。從1984年至今,我在福建省委黨校工作25年,期間有順境也有逆境,有前進也有徘徊,有成功也有挫折,有歡樂也有痛苦,但無論何時何地,每每思及范老的關愛,我始終不敢停頓、不敢懈怠、不敢放棄、不敢放任。這25年中,不是沒有更好的機會,不是沒有更佳的選擇,也不是沒有更高的追求,但我始終不敢忘卻那沒有第三個人在場的承諾——安心黨校工作,當好黨校教師。而且,每當我的承諾哪怕只是實現一點點,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范老。1995年我被評為全國黨校優秀教師,在中央黨校接受頒獎,當兼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胡錦濤同志為我戴上金燦燦的獎章時,我想到范老;1996年入選福建省百千萬人才工程時,我想到范老;2001年順利評上教授時,我想到范老;2002年進入福建省委黨校校委班子時,我再次想到了范老。想起他,我深感有幸,有幸得識這樣的忘年之交,有幸得識這樣的良師益友,有幸得識這樣的人生楷模;想起他,我又深感慚愧,慚愧自己不理解那偉大的情懷,慚愧自己對老區人民感情的浮淺,慚愧自己的狹隘和冒失。可惜再也不能和范老暢談,真希望能向他道出深深的歉疚,真希望能再次聆聽這位慈祥長者的諄諄教誨。
(作者現任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