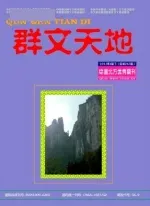從“話青海”到“唱青海”的心路歷程
紫 云
滕曉天先生的《青海花兒唱青海》,作為《青海花兒話青海》的姊妹篇,一經推出,在青海“花壇”再次引發一場“話青海、唱青海”的熱潮。在民眾審美情趣普遍提高、藝術眼光日益挑剔的今天,這部“唱青海”何以能再次讓“花兒”界注目,依我看,這個話題值得琢磨。滕曉天先生作為一名久經“花”海的護“花”使者,一名熟諳花兒格律與表現意境的學者,之所以信心十足地推出這部花兒集,除了與時俱進,“老瓶裝新酒”,賦予古老韻律以時代氣息之外,他的治學精神與人格魅力,以及近二十年以來日積月累的社會威望也與此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進而言之,我們有必要把眼光放在一個比較寬泛的時空內,去研究這種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文化現象。
二十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大潮的沖擊,現代傳播媒體的快速普及,以及國內民間文藝研究熱點的轉移,“花兒”的研究逐漸進入了近十年的消歇期,而“花兒”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呈現出的喜憂參半的景象,一時成為廣大民眾關注的焦點。一方面,“花兒”音像制品大量上市,魚龍混雜,充斥城鄉,甚至出現某些商家急功近利,奉迎低俗需求而“惡搞”“花兒”的現象。同時,大量“花兒”歌手紛紛進入城市,立足茶園等娛樂場所,在簡陋的條件下實踐著“花兒”的創收功用。這種對“花兒”資源的多重性開發。以及“花兒”群體進入城市、尋求發展的自發行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論,而缺乏的則是相關部門正確的引導和扶持。
難能可貴的是,這一時期,仍然有部分學者執著地堅守在“花兒”研究的陣地上,一往情深地耕耘著“花兒”園地。不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這一時期對“花兒”的理論研究也顯得良莠不齊。一方面,“花兒”理論研究,缺乏新的視角和理論支撐,加上此前的學者們嘆為觀止的學術成就,使得這一時期的“花兒”研究,難以再有新的突破,學術界出現相互承襲,舊調重彈,對類似于“花兒”起源及稱謂等陳舊話題糾纏不清,進行無謂紛爭的現象。(其實,許多涉及“花兒”的常規性的問題,在此前不久趙宗福先生的《花兒通論》問世后,不應再開口水戰。)另一方面,部分學者另辟蹊徑,挖掘整理“花兒”所包含的深層次的社會學信息,使得“花兒”研究,在歷史、人文、民俗等領域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世紀更替之際,朱仲祿選編的《愛情花兒》、羅耀南編著的《花兒詞話》、滕曉天編著的《青海花兒話青海》等專著,以“花兒”為媒介,從民俗研究、“花兒”的修辭手法及文學欣賞的角度,對青海地方民俗文化進行了全面的回顧和介紹,提升了“花兒”在民俗學研究領域的地位和在民眾心目中的文化品位。這其中,《青海花兒話青海》以其深邃的史學信息、翔實的民俗及人文資料、優美的散文筆調、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敘述手法而備受各階層民眾的關注。時至今日,許多人提起這本書,依然是津津樂道、興趣盎然,甚至出現讀者四處尋求而書店無書可售的狀況。單就“花兒”論著的出版隋況而言,多年來,這種“洛陽紙貴”的情形是很少見的。可以說,這本科普讀物影響了許多人對“花兒”的偏見和一知半解。
《青海花兒話青海》在沒有正式出版之前的幾年間,其中的許多篇章曾在報紙上陸續發表過,和許多人一樣,忙里偷閑剪裁報紙上的“花朵”也成了我業余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我從中受益匪淺。所以,當《青海花兒話青海》一經出版,就毫不含糊地成為我的收藏對象。我平生藏書有兩大陣營,一是各代文史資料,二是各種古典詩詞及其他文學論著。說實話,當時我首先是將這本書作為文史資料來收藏的,在這一點上,我的許多文友都有同感,包括那些甚至不知“花兒”為何物的人。由此可見,《青海花兒話青海》在眾多的層面上有著廣泛的讀者。另外,“花兒”與古典詩詞在修辭手法上的異曲同工之妙,在我研讀了這本書之后,也有了更為理性的認識。世間萬物,皆有詩情畫意,“花兒”作為包納萬象的百科全書,演繹賦、比、興的通俗藝術,自然不能例外。已故的青海名士李文實先生,曾寫過一篇論述“花兒”起源的文章,在文中他將“花兒”與二千多年前的《詩經》相提并論,可謂立論大膽,神乎其神。這與其說是學術上的一次推論,還不如說是一位飽嘗了人生五味的傳統文人與古人的對話,一次跨越時空的文學上的演繹,只可意會,難以言傳。可以說,《花兒通論》、《青海花兒話青海》等著作,是我最早系統地研究“花兒”的最為全面的教材之一,是與五彩繽紛的“花兒”世界溝通的媒介。有了這些資料的引導,我得以在幾年的時間內,在“花兒”的海洋中暢游了一番。這也是我之所以要將這些書推薦給那些對青海歷史和民俗一無所知的人的眾多理由之一。也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花兒”愛好者要將這一系列的論著放到一起來論述的最重要的原因。
2004年6月,青海花兒研究會第二屆代表大會召開。以朱仲祿、滕曉天、井石等為核心的第二屆理事會,集思廣益,順應潮流,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打造青海花兒品牌”的理念。當年,在召開著名“花兒”演唱藝術家朱仲祿先生從藝六十周年紀念會之際,青海省花兒研究會和青海省江河源文化研究會聯合召開了“打造青海花兒品牌研討會”。自此以后,“打造花兒品牌”成為“花兒”研究與開發的熱門話題,也成為青海花兒研究會的中心工作,相應的研究、實踐、開發等活動均在較高的層面上再次引發“花兒浪潮”。此后的幾年間,有許多綻放在“花兒”園林的奇葩值得我們回顧和關注。如,2004年起,青海省文化館主辦的連續多屆“西北五省(區)大型花兒演唱會”;2005年,由師守成等主創的花兒風情歌舞劇《六月六》所獲得的巨大成功;2006年,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會、青海花兒研究會和青海省文化館合編的《青海花兒論集》和《青海花兒新篇》所展現的論題新穎、見解獨到的風格和給人的耳目一新的感覺。青海“花兒”在經歷了歷次風吹雨打之后,終于迎來了輝煌的金秋,2006年6月,青海“老爺山花兒會”、“丹麻土族花兒會”、“七里寺花兒會”、“瞿曇寺花兒會”列入國務院頒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無疑是“花兒”成長史上的又一個歷程碑。在我們享受成功喜悅的同時,社會各界對多年來辛勤耕耘的“花兒”園丁們也給予了崇高的敬意和榮譽。2006年,中國唱片總公司出版《“中國原生態演唱系列”之“西北花兒王朱仲祿”》。2007年6月,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授予朱仲祿“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榮譽稱號。2007年7月,由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會、青海花兒研究會和青海省文化館聯合舉辦的“花兒的明天暨朱仲祿花兒藝術研討會”在西寧召開。同時出版《文壇瞭望—青海花兒研究專號》以示紀念。2008年,以朱仲祿原創“花兒”《雪白的鴿子》為引子的現代舞臺劇也以宏大的場面、唯美的藝術手法而轟動藝壇,倍受社會各界的關注。2009年上半年,青海電視臺和青海花兒研究會又成功地承辦了青海花兒電視大賽。所有這些輝煌的成就,無不傾注了許多不計名利、只問耕耘的藝術家們的心
血和智慧,這當中,身為青海“花兒”研究會會長的滕曉天先生無疑是眾望所歸的領軍人物。當我們回顧這一段歲月時就會感覺到,這一時期的“花兒”理論研究與創作,著眼于“花兒”品牌的打造與藝術創新,一直在高品位上運作,時代特色愈加明顯。2009年3月,青海省花兒研究會和青海省文化館聯合出版《青海花兒選》。其上篇以“花兒”的不同表述內涵進行分類,從浩如煙海的傳統“花兒”中精選了五百余首,構勒出了一個了解傳統“花兒”全貌的輪廓。下篇選編了青海地區“花兒”學者和歌手們近年來創作的飽含時代氣息的“花兒”五百余首。與此同時,滕曉天先生繼《青海花兒話青海》之后,又隆重推出其姊妹篇——自創新式“花兒”集《青海花兒唱青海》,其中編入作者多年來創作的描述青海風物、贊美地方風情的當代敘事“花兒”近千首。在人們的印象當中,“花兒”首先是勞苦大眾渴望幸福、傾訴苦難的心聲。所以,傳統的抒情“花兒”大多辭令凄苦、聲調哀婉。容易給人造成苦難深重的壓抑感。而真正能流傳下來的節奏歡快,賞心悅目的敘事“花兒”并不多見。《青海花兒唱青海》緊緊扣住“唱青海”這個主題,對青海山川、人文景觀。乃至建設成就、人們的精神風貌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贊美。敘事風格清新自然,詼諧靈動;遣詞造句通俗易懂,瑯瑯上口。通讀全篇,你感覺不到一點悲觀的感情色彩和對漫長人生的無奈之聲。展現在你眼前的都是五彩繽紛的高原景色,充滿朝氣的田野風光,有滋有味的富足生活,催人奮進的時代新聲。我們在品味這兩部姊妹篇的時候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由于兩者的出發點和視角不同,所以兩者表現出了迥然不同的藝術風格,給人以不同的藝術享受。如果要將《青海花兒話青海》和《青海花兒唱青海》做一番比較的話,兩者之間既有淵源上的承接關系,同時又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前者如同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人在品嚼自己的五味人生,顯得厚重而古樸,又如同一壇封存了百年的青稞老窯,口感濃郁,意味深長。而后者則如同一位風姿綽約、善解人意的少婦,眉目之間分明蘊藏著成熟誘人的溫馨之氣,又如同一杯流光溢彩的現代五色雞尾酒,韻味酣暢,令人陶醉,無不折射出新時代鮮活的氣息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同一個釀造高手,同樣的釀造工藝,由于所添加的生活佐料不同,而釀造出了兩種風味迥異的美酒,但萬變不離其宗,美酒的特質依然如故。
我之所以要回顧從“話青海”到“唱青海”的心路歷程,還因為這一時期,其實正是青海“花兒”研究與開發的復蘇期,是第二屆“花兒”研究會大有作為,卓有成效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是可以載入“花兒”史冊的。同時我認為,像滕曉天先生這樣在“花兒”的研究與開發進程中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人,比起那些動輒“稱王封后”的人,更應該受人尊敬,更應該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支持,更應該賦予其名至所歸的榮譽和威望。這既是對前者的肯定與勉勵,也是賦予后來者的啟示與信心。因為我們需要這樣的文化氛圍,需要這樣的學術準則,也需要以這樣承前啟后的精神去開創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