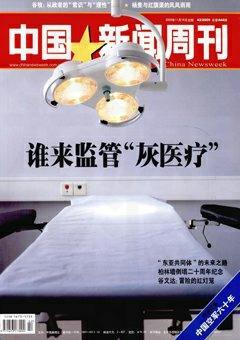柏林墻倒塌20周年:今天,他們如何紀念
王維博 陳 君

紀念的最好方式是思考,是傷痛教會了德國人思考。
11月9日,西德長大的阿克曼特意從北京飛回德國。“整個柏林都在慶祝。”阿克曼在電話那頭很興奮,“街頭放著老電影,酒吧里全是人,大家用酒精和歌聲來慶祝。”
米夏埃爾?卡恩一阿克曼,德國漢學家,現任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長,上世紀60年代曾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社會學、漢學,70年代中期在北京留學,80年代開始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向德國人介紹了從老舍到張潔等一大批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
“墻已經沒了這么多年了,還起什么哄?把日子過好是最重要的。”66歲的柏林人考夫曼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47年前,他生活在東德,是守衛柏林墻的普通一兵。
在柏林著名的波茨坦廣場旁邊,魯夫經營著一家古董店,“這幾天,柏林墻磚賣得挺好。”做墻磚買賣的生意人還有很多。這些被稱為柏林墻碎片的磚頭,被包裝好,根據大小以從1歐元到數十歐元不等的價格,一賣就是20年。
18歲的雅克和他的朋友則將一場行為藝術獻給了這個紀念日。他們把用塑料、紙板做成的“微縮柏林墻”擺到了柏林墻一段地基遺址上。
“說實話,我并不真正了解那段歷史,我出生的時候,墻已經不存在了。”雅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所關心的,是我們對國家前途的反思。你以為現在東德和西德就不分裂了嗎?”
筑墻者與逃跑的人
柏林墻倒塌的時候,德國駐華使館新聞官龍安德只有13歲。
在龍安德的記憶里,父輩的往事多與“逃跑”有關。龍安德的父親1938年出生于東柏林。母親于1949年,在西德一個北方的城市出生。蘇聯的紅軍打到柏林的時候,父親及家人連夜逃往了丹麥。
1945年到1947年,龍安德的父親在丹麥一個專門供德國人住的難民營生活兩年。兩年之后重返柏林,“柏林8層以上的樓幾乎都被推倒了”。雖然考慮到以后法、英和蘇聯還會有矛盾,但是他們還是決定安定下來。那時候,柏林市民能在城市自由活動,但隨著冷戰鐵幕開啟,1952年東西柏林的邊界關閉。
1953年,因為一場柏林的起義。龍安德的父親再次出逃到匈牙利,直到1961年才又回到柏林。資料顯示,從1949年到1961年,大約有250萬東德人逃入西柏林,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包括技術人員、熟練工人。
1961年8月12日,與西柏林接壤的東柏林街道上所有燈光突然熄滅,軍車連綿不斷地開上來。2萬多名東德士兵只用了6個小時,就在東西柏林間43公里的邊界上,筑成一道由鐵網和水泥板構成的屏障,這就是柏林墻的雛形。
“那道墻正式的名字叫‘反法西斯防衛墻,接到任務的時候,我只知道要去修筑工事。”考夫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考夫曼回憶道,柏林墻并非只是一堵水泥灰墻,它外圍有道3.5米高的通電鐵絲網,鐵絲網與柏林墻之間有50米寬的空地,埋有地雷。“包括壕溝在內總共有15道防線吧。有些墻體很厚,防止車輛沖撞;有些路段,翻過墻去還有河水擋著。”
重重封鎖,也擋不住對外面世界的渴望。“想要過另一種生活的人還是不少——可恥的資本主義,那時候就是這樣說。”考夫曼的語氣不容置疑。

彼時龍安德的父親已快大學畢業。東德政府要求他入黨,龍安德的父親不愿意,所以1964年又一次逃跑。柏林墻建成第三年,他先逃往丹麥,最后去了西德。
與大多數逃往西德的人一樣,龍安德的父親冒著生命危險半夜翻墻逃走,一同逃跑的朋友則被抓回去蹲了一年監獄。
“每隔一段距離就有多名士兵把守,24小時不斷人,常年倒替。發現叛國越境的,我們就鳴槍,逮住他或者擊斃他。這是政府允許的,也是士兵的責任。”考夫曼已經記不得抓獲了多少偷越國境者,“我沒有打死過人,所以后來也沒有接受審查。”他至今不后悔那段“為國守邊”的經歷。
龍安德的父親逃跑后的第二天,東德警察找上了門:“你兒子怎么敢離開我們偉大的東德呢?”龍安德的奶奶氣憤地罵:“這個傻瓜,這個笨蛋,怎么就離開我們自己的國家?”
那時的逃亡常常被解讀為對自由的向往。1963年6月25日,柏林墻建成兩年后,美國總統肯尼迪在西德發表了《柏林墻下的演說》,稱“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敵,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我現在覺得這是一種誤讀,過度渲染了柏林墻的政治符號作用。有些人拼命要到那邊去,因為那邊也是德國的土地,有骨肉朋友,想過去是自然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翻墻與‘自由無關。但當時聽美國人、英國人這樣說的時候,我也很激動,覺得尋找自由是自己的責任。”柏林市政廳退休辦事員施萊因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施萊因上世紀70年代正在東柏林居住,“最終我沒有冒險。因為我在東德生活得也并不糟糕。”
“我和他們沒有關系”
1976年,龍安德出生在西德的科隆市。8歲時,他到東德去看望祖母和其他親人。從西德到東德雖然要經歷嚴格檢查,但并沒有很多限制。
東德人很安靜,平常習慣在家里呆著。西德常見的大眾、寶馬、奔馳在東德幾乎看不到,街上跑的都是冒著黑煙的老式汽車,買一塊面包要排很長的隊。這對年幼的龍安德來說,簡直無法忍受。
漢學家阿克曼那時還是個少年,他在東德沒有親戚。唯一一次去東柏林,是因為學校安排去東柏林旅游一天,除了要等很長時間接受檢查外,對東德沒有特別的印象。
“我去了意大利、法國、西班牙,但是東德對我來講,就如同讓我去芬蘭一樣,讓我去那里干嗎?沒有這種意識,沒有這個必要,我和他們沒有關系。”阿克曼說。
那一次之后,阿克曼再沒有去過東德。實際上,很多西德人也都有類似于阿克曼的體驗。在他們的意識里,兩個德國已經成為一種思維習慣,他們并不認為德國的統一是迫切解決的問題。
在當時的阿克曼看來,西德進入歐洲,變成歐共體的一部分要比統一兩個德國重要得多、必要得多。“我承認,這些都是當時大部分西德人的想法。”
對阿克曼和龍安德來說,柏林墻的倒塌非常突然。前不久,德國的一個媒體把20年前東德和西德的新聞報道拿出來對比著播,龍安德才弄明白那段歷史。
一直在東邊的考夫曼記得起那一天的所有細節。“那天我一輩子都忘不了。1989年的11月9日,本來不是我執勤,但柏林墻這邊地動山搖,我也從宿舍跑出來,我看到人們喊口號,舞動旗幟,我沒有聽到槍響。”考夫曼說。
“推倒柏林墻!”“打倒墻!”有人站出來高呼著,結果一呼百應,數十萬人一眨眼工夫居然把延綿數十里的柏林墻推倒了。
“德國的統一,是東德人創造的,不是我們西德人創造的。這是一次沒有流血的偉大革命。”阿克曼這樣評價。
生活中還有很多這樣的墻
柏林墻倒下的第二天,在東德做研究員的默克爾就帶著妹妹到西柏林百貨公司“朝圣”,首次品嘗了來自意大利的奶酪。如今,作為德國統一后首位來自東部的總理,默克爾成為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真正的主角。
柏林當地時間11月9日下午,默克爾和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一起重新越過柏林墻一處檢查點“伯恩霍莫大橋”——20年前最早開放的東西柏林邊界關卡。“即使上世紀80年代,我都不敢相信柏林墻能在我有生之年倒塌。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讓我們想到,德國和歐洲能統一,這種幸運讓人難以置信。”默克爾說。
來到柏林墻的腳下,看到歡呼的人群,阿克曼再一次落淚了,但心境卻與20年前大不一樣。
1989年11月9日,阿克曼正在北京為剛成立的歌德學院奔波。當天晚上,通過電視他看到柏林墻倒的消息。東德人爬上柏林墻揮舞雙手的畫面擊中了阿克曼的內心,模糊的記憶變得清晰起來,他流淚了。
“生活中還有很多這樣的墻。”柏林墻已超越了政治意義,而是對生活的一種象征。這是時隔20年后,阿克曼再次流淚的原因。
柏林墻推倒后,每天都有幾萬人從東德涌入西德。當年,西德政府給每個訪客100馬克,作為歡迎的禮物。然而今天,這種不平衡似乎并未改變,“統一代價之大”也越發引起東西部同樣的不滿。
柏林自由大學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2%的前東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表示,如果柏林墻沒有被推倒,柏林形象會更好些。柏林墻拆除20年后,許多前東德居民認為,前西德接管了他們的文化和政治,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而前西德民眾說,他們不情愿再支付高昂的“統一稅”。
從1991年開始,聯邦政府累計向東部地區輸血總額已經達到了1.3萬億歐元,如此龐大的天文數字,居然還是未能拉平東西部之間的經濟和生活水平差距。而前東德人對共產主義時代的懷念也令西邊的人厭煩。
德國東部的失業率幾乎是西部地區的一倍左右,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社會福利保障等和西部有著明顯差距,有四分之一的東部地區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些都令聯邦政府頭疼。最樂觀的估計是,等到2019年,東部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E可以達到西部的平均值。
“紀念的最好方式是思考。傷痛的記憶固然重要,最需要的是未來的思考。是傷痛教會了德國人思考。”阿克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