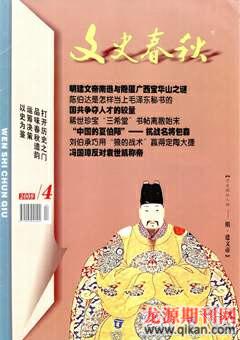陳伯達是怎樣當上毛澤東秘書的
孟昭庚
陳伯達(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后,先后在北平中國大學、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撰有《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當時中共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后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紅旗》雜志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并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革”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積極參與林彪、江青的陰謀奪權活動,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被開除黨籍。1976年9月被捕,1981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隨后保外就醫,1989年9月卒于北京。
一
陳伯達生于福建惠安縣嶺頭村一個破落的秀才之家,原名陳建相,字尚友。15歲那年,他以最后一名的成績考入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廈門集美師范學校。讀了兩年半后,回到惠安老家當上小學教員,一年后到廈門小學任教。
在廈門小學任教期間,18歲的陳伯達不但在三四所小學里同時兼課,還在廈門同文書院學習英文。忙里偷閑時,他還寫一些小文。1922年4月出版的第九卷第四期《學生》雜志上,登出《兵?否?》一文,署名:陳建相,這是陳伯達的“處女作”。19歲那年,陳伯達愛上了詩,傾慕中國詩壇“新星”郭沫若,一遍又一遍拜讀《女神》,情不自禁地致信郭沫若,大談感想。郭沫若給了他回信,他興高采烈。
1924年,陳伯達在中共早期黨員、福建人張覺覺幫助下來到上海,一邊在一家小報當記者,一邊進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學習。上海大學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與中共合作創辦的,校長雖為于右任,但總務長卻是中共黨員鄧中夏,鄧為該校的實際負責人。在校執教的除有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之外,還有一大批進步學者如陳望道、沈雁冰(茅盾)、鄭振鐸、俞平伯、施存統、蔣光赤等,均應聘在該校授課。陳伯達在這所大學里,受到了共產黨人的熏陶,初步接受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
1925年春,陳伯達回到廈門。當時正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21歲的陳伯達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經人介紹參加了國民黨。
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開始“清黨”,首先在上海向共產黨舉起了屠刀,趙世炎、陳延年等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人倒在蔣介石的槍口之下。就在這時,陳伯達由廈門乘船抵達上海。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陳伯達在回憶往事的手稿中,寫了他的入黨經過:“我是在蔣介石、國民黨清黨大屠殺的時候,在上海申請入黨的。在大屠殺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報紛紛登出共產黨組織被破壞和大批叛徒自首啟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偉大的共產黨隊伍中,于是就免了我入黨的候補期。”
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陳伯達很難在上海立足。他便奉黨組織之命,跟隨王明(陳紹禹)、李立山、羅亦農、王荷波等一批共產黨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漢。到了武漢,組織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出版科科長。不久,陳伯達接到黨組織的通知,派他赴蘇聯學習。
陳伯達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后,被分配在一年級二班。跟他同班的同學有凱豐(何克全)、陳昌浩等,同級不同班的有張聞天、王稼祥、孫冶方、伍修權、烏蘭夫等。
這時,被稱之為“蘇聯紅軍之父”的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逐出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斯大林正在全國發動聲勢浩大的“肅托運動”。在中國學生之中也開展了“肅托運動”。由于陳伯達與中國的“托派”學生十分親近,故而“肅托運動”也涉及了陳伯達,陳伯達受到了黨內勸告處分。
三
在蘇聯度過了3個春秋,1930年底陳伯達獲準回國。1931年春,陳伯達來到上海,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到了上海,陳伯達出乎意料,不但見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王明,還見到了校長米夫。盡管王明與陳伯達同歲(當時皆為27歲),可是他已經以“中央領導”的身份和口氣跟陳伯達談話了。
看了一些黨內文件,陳伯達才得知,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議竟是由王明主持。王明一躍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代了李立三,掌握了中共的實際領導權。
陳伯達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順直(今河北)省委宣傳部工作,任務是負責出版編輯《北方紅旗》刊物。
1931年4月8日,陳伯達由上海坐船抵達天津。這一天,中共順直省委機關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化名王通的陳伯達與省委組織部長陳原道、省委書記許蘭芝以及劉寧一、劉亞雄(女)等15人一同陷入特務的魔掌。由于省委書記許蘭芝的叛變,特務突破了全案。在法庭上,敵人讓許蘭芝與陳伯達當面對質。陳伯達看到是許蘭芝,大吃一驚說:“呵,竟有這樣的事!”這樣,陳伯達不得不承認是由上海來做宣傳工作的。
1931年9月4日,陳伯達與陳原道等人從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陳伯達被判處兩年半徒刑,關進“北平軍人反省院”,俗稱“草嵐子監獄”里服刑。陳伯達在獄中患病,不但鼻孔大出血,而且淋巴腺也一天天腫大起來。雖經開刀,可是淋巴腺不但不收口,反而更加蔓延了,膿流得更多了,樣子變得十分可怕。陳伯達不得不給福建軍閥張貞寫信求救。
陳伯達認識張貞,還是1926年夏天的事。當時陳伯達在汕頭擔任國民黨汕頭市黨部秘書,結識了駐防汕頭的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張貞。張貞也是福建人,頗為賞識陳伯達,看中了他的筆頭才能,便聘他為秘書。同年底,張貞升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四師師長,陳伯達也就變成了少校秘書。1927年初,王荷波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來到福州組織工人糾察隊,找到故人陳伯達,問他愿不愿意擔任工人糾察隊的顧問。陳伯達爽快地答應了,由此他的一舉一動引起國民黨右翼人士的關注。盡管陳伯達當時并不是中共黨員,但是那些右翼人士探知他與中共來往密切,稱他為“赤色分子”。一天,張貞收到來自南京的曾任閩軍司令的福建反共大頭目宋淵源的密電,要他就地處決陳伯達。張貞下不了手,秘密通知陳伯達立即逃離福州。
如今,張貞接到了陳伯達從“草嵐子監獄”發來的求救信,趕緊派專人前往北平,不惜花大錢為陳伯達打通了“關節”,將其贖出。
后來,陳伯達曾跟毛澤東談及張貞。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看國民黨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張貞就救過陳伯達一命……”
四
陳伯達于1932年出獄,1933年初黨組織派他赴張家口到吉鴻昌部隊工作。1933年春,吉鴻昌與馮玉祥、方振武等在張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軍。陳伯達在吉鴻昌部隊的主要任務是寫點宣傳鼓動文章,編編刊物。
蔣介石此時正大肆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吉鴻昌公開抗日恨之入骨,下令逮捕了他。可是,押解吉鴻昌的國民黨軍士兵卻十分景仰這位抗日英雄,悄悄地把吉鴻昌給放跑了。吉鴻昌潛往天津,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繼續開展抗日工作。
陳伯達無法再在吉鴻昌部隊立足,只得躲在北平西山,埋頭寫他的第一部史論著作《論譚嗣同》。書稿寫就,陳伯達去天津找吉鴻昌求助。吉鴻昌慷慨解囊,幫他出資印刷。《論譚嗣同》一書,是陳伯達出版的第一本書。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運動爆發次日,陳伯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趕到北平與李葆華、柯慶施等一道,領導當時北平全市學生的總罷課,并負責執筆起草北平學生運動的宣傳大綱。
1936年春,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天津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改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部長、林楓任秘書長。自此,陳伯達在黨內開始有了一定的地位。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此時,中央北方局任命黃敬、林鐵、陳伯達組成相當于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北平三人委員會”,負責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隨后,黃敬建議陳伯達還是到根據地為好。于是,陳伯達于8月上旬離開北平來到天津。天津在日軍鐵蹄之下一片混亂,陳伯達期望著能有稍微安定的環境,可以繼續他的著述,希望能夠前往延安。
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陳伯達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島,然后跟黃敬一道出發西行。黃敬在青島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車票,將陳伯達一家帶至濟南,然后轉車往西安。車到西安,黃敬前往華北抗日戰線擔任中共區委書記,陳伯達則帶著妻兒輾轉來到革命圣地延安。
五
陳伯達到延安時,正值陜北公學剛開始創辦,很需要教員。因陳伯達曾在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教過書,中共中央組織部便安排他到陜北公學當一名教員。
陳伯達只宜寫文章,不適合當教員。他那一口閩南方言,實在讓人難以聽懂。他講課時,要不斷地在黑板上寫粉筆字,學生才能明白他講的意思,與其說是講課,倒不如說是“寫課”。
在陜北公學教了一陣子書,陳伯達被調往中共中央黨校當教員。黨校校長是剛從共產國際回國工作的康生(趙容)。說起康生,陳伯達一點兒也不陌生。1924年,陳伯達與康生同時進入上海大學,只不過當時康生在社會科學系,名喚張叔平。
1938年5月5日,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這是中共中央培養理論干部的院校,院長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洛甫)兼任。張聞天跟陳伯達很熟,他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期同學。張聞天當即把陳伯達調到馬列學院當教員。
有一次開會,毛澤東來了。張聞天當眾向毛澤東介紹道:“這是剛從北平來的陳伯達同志!”當時,毛澤東并未注意到陳伯達。
教書畢竟非陳伯達所長,因為學員們反映聽不懂他的閩南話。常常出現這樣的怪事:陳伯達給中國學員上大課,往往要帶“翻譯”,將他的閩南話譯成普通話。
于是,陳伯達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被任命為出版科科長。1927年陳伯達入黨后不久便在武漢擔任此職,哪知在11年之后,他竟然仍擔任此職。
六
陳伯達初到延安時,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心境不那么舒暢。但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那是一次由毛澤東參加的理論座談會,內容是討論孫中山的思想。會上,大家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于“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于“民族資產階級”。
毛澤東很仔細地傾聽雙方的爭論,雙方各有道理,爭論頗為激烈。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發言了,他盡量講得慢一些,以便大家能聽懂。陳伯達高明之處,就是運用“對立統一”的方法加以闡述,他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堪稱“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注視著陳伯達。陳伯達發言完畢,毛澤東站了起來,很高興地說道:“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
散會之后,毛澤東把陳伯達留下來,問了一些關于他的情況。
那天傍晚,毛澤東派人通知陳伯達,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陳伯達聞訊急急忙忙趕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澤東要宴請一位美國記者。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美國客人。”
這次請客很簡單,毛澤東、翻譯、美國記者、陳伯達4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澤東跟美國客人說了一些客套話。后來,他轉向陳伯達,問起北平文化界的情況,問起張申府的近況。張申府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曾參與中共的創建活動和工作,他和夫人劉清揚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其后張又與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入黨。后來張劉夫妻雙雙皆脫黨。
陳伯達告訴毛澤東,張申府作為進步教授,正執教于清華大學,與夫人劉清揚一同住在清華園內。劉、張雖不在黨內了,但從不損害黨,與黨組織還有聯系,并積極組織學生跟國民黨的賣國“不抵抗政策”作斗爭,夫妻倆都曾被國民黨抓進監獄。現在,夫妻二人均在武漢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毛澤東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先秦諸子”課,而他本人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饒有興趣。這樣,他們之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越談越投機,竟把美國客人撂在一邊。
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人生的轉折點。
七
被毛澤東看中之后,陳伯達不再坐“冷板凳”了。
經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聽,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雖然陳伯達的話很難聽懂,但聽久了也慢慢習慣了。很快,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了這個學術團體的領頭人,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一文,發表于1938年9月的《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澤東,請求給予指正。
毛澤東很仔細地讀完《墨子哲學思想》,親筆給陳伯達復了一封信——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為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筆者注)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毛澤東的書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而這次因《墨子哲學思想》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復了信仍覺意猶未盡,便又寫了好幾頁紙的意見附在信后。
陳伯達所擅長的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正是毛澤東當時思索的熱點,當然毛澤東的見解要比陳伯達高出一籌。
陳伯達一見毛澤東對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澤東呈送上他所寫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兩篇文稿。
毛澤東讀后,興致依然很濃,于1939年2月20日寫了一封更長的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詳細地寫了7點意見,針對陳伯達的文章,談了自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看法。
陳伯達收信后,當即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呈毛澤東。
1939年2月22日,毛澤東又寫一封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
伯達同志的文章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伯達同志考慮。
……
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又補充了3點意見。
借助于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探討,以及呈送文章向毛澤東請教,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系日益密切起來。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和話題,這樣陳伯達為毛澤東所看中,就是勢所必然了。
1939年,張聞天找陳伯達商談調動工作的問題。張聞天告訴陳伯達,毛澤東提名調他到毛澤東辦公室工作,陳伯達以欣喜的心情一口答應下來。
八
陳伯達調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因此陳伯達也就是毛澤東辦公室副秘書長。
毛澤東給陳伯達擬定了四項任務,即四個研究課題:《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教育》、《抗戰中的經濟》。
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陳伯達做了大量的資料搜集工作。陳伯達說,是毛澤東幫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從古代轉向現實生活。
自此,陳伯達便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職務不斷地在變動著:他成為中共中央秘書處的秘書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長為張聞天,陳伯達任秘書長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后來,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陳伯達被任命為主任。
他的職務雖然在不斷變動,但實際上一直在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由于毛澤東的信任,陳伯達進入中共高層,接觸到中共高級機密。盡管他的職務并不很高,但工作崗位卻顯然占據要職。陳伯達以后得以飛黃騰達,起飛的起點便是毛澤東的秘書這一職務。
九
1945年,陳伯達在中共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那時,中共雖已有黨員120萬,但中央委員會卻相當精簡,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加起來才77名。按得票多少排列,陳伯達在中央候補委員中名列第三。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書: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江青,俗稱“五大秘書”,陳伯達為首席秘書。當時,中共中央主席是毛澤東,所以中共中央主席秘書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秘書。
“五大秘書”分工如下:陳伯達、胡喬木為政治秘書,葉子龍為機要秘書,田家英為日常秘書,江青為生活秘書。
緊接著,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論年紀,陳伯達這時才過“天命”,但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往往用“老夫子”戲稱之,由此可見陳伯達當時在中央的聲望。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排列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之后,一躍成為中共“第五號人物”。幾個月后,陶鑄被打倒,陳伯達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僅次于周恩來的中共“第四號人物”。
十
陳伯達成為毛澤東手下的一枝筆,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曾做過一些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但多年以來,陳伯達總是在揣摩著毛澤東的心思,摸測毛澤東的動態,察言觀色,憑著他那特有的看風向、摸氣候的本領,對于毛澤東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他都很注意,然后投其所好。
從1957年開始,毛澤東逐漸向“左”偏航,他對“社會主義階段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認識,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使其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以致在“文革”中陷入“左”的迷誤。而陳伯達在毛澤東的這一方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為毛澤東晚期的錯誤理論引經據典作論證,用他的筆闡述并發展了“極左路線”、“極左理論”、“極左政策”、“極左方法”,以至于最終墮落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成為歷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