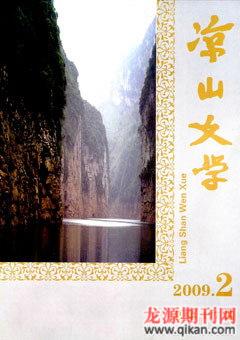深重的民族文化意識
張 紅
霽虹,真名祁開虹,彝族,1967年6月生于會理縣金沙江邊一個叫回頭山的村子。著有詩集《大地的影子》、《霽虹詩選》和《沿著一條河》。他以“一個彝人孩子的純真”,用他自己特有的語言,樸實的詩歌,表達了他對本民族的熱愛、憂慮和發展的信心,在彝族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華章。他的藝術成就反映了彝族這個古老的民族在面臨新的多元文化沖擊時,重新審視和思考自己民族的文化命運,以及一代文化人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對這種沖擊的憂患意識,在“沖擊”陽“保守”之間的心理矛盾和對本民族未來文化發展的巨大信心。詩人敏銳地抓住了時代的機緣,努力掙脫舊的民族文化傳統的束縛,差異與局限,他直接運用漢語言進行創作,用全新的視角觸摸了這片古老的文化土壤。他的詩歌創作,不論是從藝術風格,還是思想內容方面。都繼承了一代著名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的風格,卻又有著獨特的超越,突出反映了一代民族文化先驅者的文化心態和文化品格。他的詩歌有著濃厚的民族文化意識,無論是對本民族的精神頌揚,還是強烈的民族認同感,亦或是對民族文化沖擊的焦慮感,都有著深深的民族“根”性,積極地表現了一代代彝族文化人渴望為本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為本民族的新生而自愿獻身的心愿和犧牲精神。
霽虹是在我國遠古文明發祥地之一、有著悠久而厚重的歷史文化沉淀的登沙江及其兩岸世居族群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這條奔流不息而靜穆的金沙江,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這片雜合著彝漢兩族文化的混血地帶,賦予了詩人內心潛在的彝族靈魂血統和外在顯現形式的漢語表達。傳統生活方式和現代意識的沖擊,本土精神家園的召喚和現代意識的誘惑,在對地域文明的徘徊和堅守中,他的詩歌中的“鄉愁”顯得極為復雜和深重。
一、濃濃的故土之思
藝術來源于生活、正如霍加特所謂“一部藝術作品,無論它如何拒絕或忽視其社會,總是深深根植于社會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含義,囡、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藝術作品那樣的東西。”況且,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在特定的地域環境和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本土之子,對自己的故鄉故土總是懷著一種牽扯不斷的依戀之情。尤其當他們離鄉背井,在他鄉生聒時,故鄉之地就更是他們心中最值得掛念之處。霽虹生長在會理縣金沙江邊的回頭山村,只讀半學期初中便輟學回家務農,在西部涼山這塊溫暖的土地上,霽虹有著童年的歡樂、痛苦與希望。羅慶春老師曾經說過:“藝術是一種文化現象,特定的藝術是特定文化的象征性符號體系,在這一體系的建構過程中作為創造主體的藝術家,不可避免地面對這樣一種生存悖論:他既與生俱來地受到特定文化類型、審美規范的限制,又從藝術創作的獨特性方面不得不有意識地逃離和超越自己所從屬的文化模式,”因而這片土地上的同胞,這片土地上的十花一草一樹木,都在他的字里行間透著親切,他與這片土地結下了一生難解的情緣。他的詩從內容到表現的手法,都浸透著濃濃的民族風情。“苦蕎麥,她溫暖馨香的呼吸,充滿了世界,使我們的生命注滿新鮮的活力,對未來懷抱美好的向往。”(《苦蕎麥》出自《霽虹詩選》)大涼山長出的苦蕎麥,像母乳一樣哺育了一代代的彝族人,并賜予了他們美好的人陸和強烈的生命活力。這既是對苦蕎麥的歌唱,也是對故土的歌唱,對親人美好人性的歌唱,只有這樣的土地才能種出這樣的苦蕎麥,只有這樣的苦蕎麥,才能養育出具有美好人性的彝族人。霽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他身上流淌著的彝族血脈,也就是他獨特的第一母語文化的靈性和精神,卻讓他用僅有的文字,寫出了一個彝人對散土的殷殷深情。“有一道金光從天外飛來,旋繞在我們的頭頂,愛人——回轉家鄉,我們是幸福的人。”(《攀枝花紅》出啟《霽虹詩選》)詩人將自己的幸福和家鄉聯系在一起,具有強烈的鄉土意識和鄉土觀念,詩人將自身的幸福寄托在了自己的“根”——鄉土之上,可見詩人對這片土地愛得是那樣的深沉,自己與土地的精神融合在了一起。“我所見到的人,用他們獨特的語言,在談論著土地和河流。”(《我所見到的人》出自《霽虹詩選》)鄉人們所談論的土地與河流,同時也是詩人所向往和贊美的源泉所在。“如果我要選擇,我就選擇一條星光照耀的小路,去找回童年的夢想……”(《選擇》出自《霽虹詩選》)在這一首《選擇》中,詩人從出生寫到死亡,從童年美好的回憶寫到愿葬身故土的過程,表達出詩人愿將自己一生獻給故土親人,以求心之寧靜,死而無怨無悔的深沉戀鄉情結。“土地的歌唱,自父親布滿犁痕的額頭上升起,世界發出深沉的回響。”(《土地的歌唱》出自《大地的影子》)人和土地的聯系,是一種與生俱來,卻難以言明而糾葛不斷的精神情懷。每個人都具有一種“懷鄉”情結,民間諺語有“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一說。“懷鄉”是對“鄉村”的依戀,對“土地”的熱愛,由此引發的鄉愁、鄉思,往往成為作家創作的源泉。霽虹他更是再現了彝族美麗的民族風情,再現了家鄉的一景一物。他筆下的土地因為父親的辛勤勞作而歌唱,詩人在此贊美了土地,也贊美了辛勤耕耘在故土之上的鄉人們。詩人作為一個彝族人的后代,對彝族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深深依戀。他的詩中,既有著對民族氣節的歌頌,也有著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我想走過去叫他一聲兄弟”(《一個彝人面對著一條河》出自《霽虹詩選》),無論走到哪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驅使著每一個彝族同胞看見自己的同胞時,都從心底里認同是“兄弟”,他是代表著千千萬萬的彝族同胞們唱出了彝民們的心聲,他把自己融入到了那片溫暖而開闊的土地中,在那上面生根、發芽、茁壯成長而結出累累碩果。他筆下的山川風物,同胞血脈都飽含著作家的審美情趣,成為一種富有生命意味的形式,洋溢著作家內在的生命激情j演繹著作家的情感歷程和審美追求。也呈現著作家特別的藝術個性,折射著作家對本土文化的洞察和思考。
二、深重的民族文化焦慮感
彝族,作為一個有著遠古文明的山地民族,雖經過歷史的坎坷,卻帶著深重厚實的文化積淀,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模式,這÷模式中既有不可替代的優秀文化遺產,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少的惰性文化。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在各個新派名詞的出現,如“地球村”,乃至更遠的“太陽鄉”,“銀河國”的出現,文化的多樣性愛到嚴重的沖擊,文化的“市場性”起來越濃厚,隨之而來的文化“功利性”也日趨明顯,保護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成為一個迫切的主題。當這一惰性文化模式在面對當今社會多元文化的沖擊時,便給作為文化主體的文化人們帶來了無法避免的尷尬場面。作為本民族文化的宣揚者,在外來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的不斷沖擊、不斷斗爭中,霽虹作為一個有著民族靈性的詩人,對這種沖擊所帶來的問題表現出了深重的民族焦慮感。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咬牙面對這必須的挑戰,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堅守著內心靈魂的那一片凈土。
“那一年我沿金沙江走了一月,直到現在,我夜夜夢著的,都是堅硬的石頭”。(《石頭》出自《大地的影子》),“石頭”代表了本民族傳統的文化,反映出了本民族傳統歷史文化根深蒂固,頑強不息,既表現出了改造傳統文化所必須付出的心血和代價,又表現了詩人想要開拓創新的決心和毅力,也表現了他在本民族文化裂變過程中所呈現的痛苦和尷尬,常常使得這個具有現代意識的詩人在精神上顯示出了抉擇的艱難和評價的困惑,使我們感受到這個少數民族詩人比其它同時代詩人有著更多的孤獨和憂傷。“在一座小城,小城的黃昏,從城墻的一角,傳來美妙的琴聲……一個老人,正用他蒼老的手,彈拔著他滄桑的感覺。”(《在一個小城里聽見月琴聲》出自《大地的影子》),這里面,既有詩人對民族傳統樂器月琴的描述,那美妙的月琴聲,即是民族感情對詩人的強烈召喚,詩人用他的心感受到了,爆發出對飽經滄桑的民族涌現出的濃濃深情,也表現了詩人對重塑民族新形象的焦慮感和迫切感。在沖擊的痛苦中,他用激烈的方法,用民族傳統的方法來選擇了他的道路,“沮喪和血液里仍在流動的英雄氣,使他們不約而同地舉起槍,射出一排穿透云空的子彈。”(《最后的狩獵》出自《大地的影子》)“最后的狩獵”道出了詩人民族的魂靈,民族的精神在激烈的拼搏中守住了,暗示了本民族既不逞強,也不示弱的優秀品格,上升到文化的角度來觀察,詩人在對這場本土文化與外來異質文化的較量中,詩人既有贊揚,也有批判,希望無論怎樣的沖擊都要恪守民族精神,但同時不要不加分析地拒絕一切,要擁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辯證主義精神。詩人變得成熟起來,用他微弱的力量開始深層次地關注著本民族的未來和一些現實問題,“從那個月亮半圓的夜晚開始,我學會了沉思,我變得成熟。”(《那個月亮半圓的夜晚》出自《霽虹詩選》)詩人開始了“沉思”,開始反思本民族的一些問題,為本民族以后的發展擔心憂慮。面對現代社會精神文明的萎縮,霽虹深深地為之痛惜,同時,傳統與現代在他的心里激起的矛盾與沖突,喧囂與躁動,痛苦和不安,都折磨著他的內心,這在他的價值取向,道德觀念和情感方式等方面都對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比起物質生活方面的改善,這內心的痛苦與沖突更顯得沉重與深刻。他游移著,最終在沖擊中堅守著自己的理想,找尋著能使自己心靈平靜的“世外桃源”。“在澤中的精絕國,何時才能長出一絲生命的綠色,召喚它魂游久遠的國民。”(《沉睡的古精絕國找到了》出自《大地的影子》)表現出詩人雖經歷著內心的痛苦和沖擊,可是他還是在努力尋找著那夢中的“古精絕國”,那理想的神圣之地,同時,他對現實世界中的一些危機也提出了警醒,對當今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所帶來的民族地區的環境問題,他痛心故土之地的水土流失,強烈呼吁保護自己生存的大地,保持生態平衡,也表達了要保護自己精神家園的美好愿望,同時通過民族的新生和重生喚起人們的民族情感,沉重的使命感使他提醒本民族人民要將古老優秀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結合起來,重振民族優秀文化。詩人不僅僅是站在文化的角度上看民族的發展問題,而是站在民族的全面發展上,從社會的,環境的,人文的多重角度上呼吁民族全面發展。
三、對民族未來文化的發展有著堅定的信心和美好的愿望
毛澤東說過,事物總是運動和發展的,雖然在短暫的一段時期內,事物的發展是極其微小的,但是在發展的歷史潮流中,總會有它閃光的一天!霽虹讀懂了辯證法,更懂得了本民族文化只有在同外界異質文化的不斷碰撞中,才會不斷地創新,不斷地發展,雖然現在的發展微不足道,但是隨著世界的發展,國家與國家的聯系,人與人的交往,全球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強,到那時,只有獨特的才會屹立于世界。詩人相信,地域的,才是世界的;民族的,才是人類的,他對彝族未來的發展抱有堅定的信心。“那都是以前的事,再也不會復返,而今我們感到幸福。”(《我的民族》出自《大地的影子》),作者深深期望著美好的未來,過去的就讓它成為歷史,詩人相信民族會發展,珍惜現在的生活,感到幸福。鐘敬文曾語重心長地說:“大家要有一種民族的自覺,將中國的精神視為命根子,將中國的優秀文化視為命根子。”霽虹的詩歌正是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他在作品中弘揚了原有的人文精神和優秀傳統,將人與人,民族與民族,民族與社會的發展當作自己詩歌的精神主旨,他的詩歌便具有了親切的鄉土精神和強大的思想底蘊。“還有那一顆顆心啊,那心中的火焰,會把人類自下而上的這個空間,照耀得十分透明”。(《假如陽光不再升起》出自《大地的影子》)作者相信本民族的那一顆顆有靈魂、有意志、有民族精神的心所燃燒的火焰,會在人類生存的空間里寫下不可抹滅的一筆,作者對本民族充滿了信心,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激情。“不燃燒,太多的夢想裝得下嗎?不瘋狂,心中的激情堵得住嗎?”(《火把》出自《大地的影子》),詩人希望民族的發展就像火一樣地熊熊燃燒開來,不斷蔓延,在這首《火把》里,有著作者對美好生活,美好愛情的向往和信心,同時,也呼喚人們去創造,去開拓,去進取,只有這樣,人們才會有發展,才會有幸福的生活,“給我這水,給我這仁愛的水,我要把它揮發成霧,化作細細的雨點,輕輕的劃過天空,潤大地而濟蒼生。”(《長江之水》出自《霽虹詩選》)詩人在這里表現了對滋潤萬物的水的渴望,只要給他“水”,他就要用“水”“潤大地而濟蒼生”,暗示民族的發展需要機遇,呼吁人們抓住機遇。他有著如此博大的胸懷,要不是他對本民族深厚的感情,要不是他對民族發展巨大的信心,他能發出如此深沉的吶喊嗎?霽虹追隨吉狄馬加,和許許多多的彝族同胞一樣,有著一樣的民族情結。民族情結是一個民族對其歷史文化的深深依戀與固執心理,每個民族都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這些歷史和文化在本民族成員的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社會沖擊時期,民族情結則表現為民族成員對自己歷史與文化的懷戀與固執,形成解不開的心靈之“結”,民族情結對維系本民族的存在與延續起著自發的凝聚作用,霽虹保持著民族情結,又站在民族發展的全部歷史上,用愛的熱情鍛煉出來的理性來審視全民族的發展,具有久遠的整體意識。“我看見無數的彝人,一群又一群,穿過窄窄的小路,這都是因為這樣的一首歌啊。”(《歌唱》出自《霽虹詩選》),這首“歌”,是彝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們不斷地在追求,不斷地在努力。而詩人,將以自己的努力成為民族發展中閃光的一環,和他的彝人同胞們一起努力,并對美好的未來生活有著堅定的信心。
詩集《大地的影子》分為“透明的珠淚”“夢中的衣裳”“愛情的記憶”三個部分。《霽虹詩選》則分為“家鄉的人最親”和“故鄉的歌最美”上下兩篇。從這些題名中,我們不難看出霽虹詩歌的特色和他對彝族同胞的那種血濃于水的無限深情,在題名中更毫無顧忌地揮灑而
出,他的感情洶涌得厲害,隨時隨地噴發而出,毫無矯揉造作之感,濃情蜜意溢滿全篇。我們都知道彝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霽虹從小生活的地方人們經常唱著動聽的歌謠,跳著優美的舞蹈,從小便對民族的風俗有著濃厚深情。他的全詩篇都洋溢著對家鄉同胞的親切深情和對故鄉風情、故鄉母語的深情厚意,鄉土戀情溢于言表,我們把它歸納為霽虹的“鄉土文化情結”。從文學的角度看,故鄉故土已不再是個地域空間概念,而是已經逐漸成為詩人心目中的精神樂土和棲居地。霽虹的詩歌風格表現出一種蒼涼悲壯的感覺,讀來覺得是一個歷盡人間滄桑的老者所感所發,可是他卻是個連高中都沒有上過的“純真的孩子”,正是他懷著對彝族用水都澆不滅的熱愛,才會讓他有如此深的感悟,才會寫出如此蒼涼的文字。現在,人們都處在鋼筋水泥包裹而成的高樓大廈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來往如此陌生,使人們無處不感受到越來越重的精神壓迫和焦慮。人感覺到自身的渺小,一種莫名的躁動,無家可歸的迷茫,引誘著人們向往一種安穩、踏實、永久的精神家園。霽虹所描繪的鄉村的土地,鄉村的河流,遙遠的小屋,能歌善舞的女子等意象,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暫時的精神寄托之地。因為這些意象都代表著一種堅韌的生命和旺盛的生機,代表著亙古悠久的地域文明。他的詩歌表現出了他對本民族地域文明價值的認同和堅守。霽虹的詩篇中兩個最重要的主題,即是對生命和死亡的探索。“夕陽”與“影子”,代表即將逝去和已經逝去的生命,而“河流”和“大山”,則象征著生命的起源,生命的開始和生命的茁壯成長。霽虹是在對本民族的生存與死亡的不斷探索中,不斷地沉默與躁動,思索與憧憬,才迸發出許多躁動不安的妙語——民族心聲的宣揚。霽虹正是仗著“一個彝人孩子的純真”,仗著他未經文化污染與馴服的生命本真與文學對話,以無任何圖式的“原始靈視”感知本民族的存在方式,深刻而鮮活地體現了他的民族,認同了他的民族,并將自己純潔的內在精神世界,負載到了民族的精神世界上。可以說,我們的彝族作家,大多數都是從大山中走出來的,他們的作品,離不開大山,離不開大山造就的風土人情,總有他們父老鄉親的影子,這是真正的民族特點。如果離開了這一特點,彝族文學便和其他民族文學沒有什么區別了。“我們崇尚喝酒,騎上一匹馬云游,在有人群的地方,我們擁有火的溫暖,跳舞,歌唱”,“我們總想用我們的淚水,去洗盡別人的悲傷,我們就是這樣一個善良的民族。”(《我的民族》出自《大地的影子》),一首《我的民族》,彰顯了民族淳樸、善良的心靈,體現了作者的民族“根”性,是一首精神的頌歌!但是,彝族文學僅僅停留在大山中是不夠的,彝族作家們應保持可貴的大山情結,同時又與時俱進,這既是當代彝族作家所肩負的時代使命,又是彝族文學發展的必經之路。人類具有豐富多彩的人文精神景觀,越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才能越具有世界性和人類性。霽虹的詩歌實踐告訴我們,在全球化浪潮激蕩的今天,在普遍痛苦地感覺失去精神家園的今天,要弘揚民族的珍貴文化,離不開對本民族、本地域民間文化資源的珍惜和深層領悟,進而達到對地域文明的堅守和對鄉土文化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