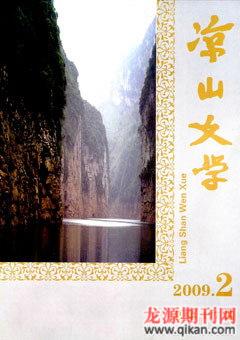“地域詩歌”的訴求與守望
倪秀維
引言
夢亦非說:“一個人如果不能設定一個地域讓自己的寫作馳騁,他的寫作便是無根的、虛妄的,中國許多詩人之所以沒有背景,就因為他們的寫作空間過于闊大,闊大到沒有。”
關于地域,發(fā)星自己的定義是:“即遺留異域色彩與保留獨特文化氣質的屬地”。
發(fā)星,一個閃亮而孤獨的彝族青年詩人,一顆大涼山上孤傲的星星,憑一己之力主持《彝風》、《獨立》兩份民刊之余筆耕不輟,曾在《詩刊》、《星星》、《詩林》、《詩歌報》、《中外詩歌》、《詩家園》、《詩歌月刊》、《守望》、《終點》、《存在》、《火種》等詩刊及美國的《新大陸》、日本的《藍》上發(fā)表作品,有詩作及文論人選《中國新詩白皮書》、《中國二十世紀民間詩人二十家》等。2000年編輯出版的《當代大涼山彝族現代詩選》在詩歌界很有影響,發(fā)星是上個世紀90年代西南“地域詩歌寫作”的重要倡導者之一,被譽為“中國當代重要的民間詩歌資料整理者之一”。
由銀河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的《地域詩歌》是發(fā)星二十年來的心血之作,該書收錄了《“地域詩歌”詩學隨筆輯》、《“當代大涼山彝族現代詩群”論》、《中國民間詩歌版塊,四川大涼山民間現代詩歌運動簡史》、《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個詞》等重要文論及部分詩稿,收錄了他與夢亦非、克惹,曉夫、馬德清等多位當代詩評家、詩人之間的精神交流,還有部分民刊的發(fā)展史以及民刊圖影,實屬一部具學術價值的文獻資料。
普格是彝族人的聚居地、火把節(jié)的故鄉(xiāng),一方水土養(yǎng)育一方人,獨特的地域環(huán)境賦予發(fā)星無盡的精神動力,其特殊的寫作背景和心理結構與情結積淀使得發(fā)星在地域詩歌的創(chuàng)作主體投入的情感上有較高的濃度、深度和強度,在創(chuàng)作的意趣指向和感情基調上略顯異樣品質,詩人是在民間世界里闡釋一個民族,在野性、雄悍的基調中呈現一個“半人半神”的世界。“地域詩歌”的出現填補了中國文壇理論的空白,在后現代主義席卷狂潮中給中國詩界帶來一股清新的蠻野彝風。品“地域詩歌”,聆聽那來自大涼山自由地域的脈動。
一、詩骨:蠻出一種精致的粗糙
“詩無骨則無以立”(老丹語),發(fā)星對地域文化的掌握有比較強的吞吐量,其詩作無論從深度、濃度來說都接近飽和,是完全站立起來的,不象大時代潮流中的虛浮、名利、變態(tài)、頹廢、陽痿等等那樣需要補鈣補鐵,發(fā)星的詩歌使人在閱盡城市的蒼白無力中品味出生機盎然與勃發(fā)奮進。司湯達說:“在熱情的激昂中靈魂的火焰才有足夠的力量把造成天才的材料溶冶于一爐。”發(fā)星以飽滿的熱情和熟練的語言駕馭技巧書寫地方文化,其詩作“在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個詞”汲取充滿濃郁的地域氣息的原基質來闡釋詞語,牧馬之地、黑石野溪、芳香的洋芋、送鬼、斗牛場、黑巫林等詞匯充裕著的野性的原始氣象與純質的詩意,蠻出一種精致的粗糙。
石頭堆咸的峽谷常常寂寞被點燃
死鷹的翅膀活了
在谷頂上空拖起一些樹枝煽動起上升欲
孤獨的男人喉嚨中很快形成一支歌
石頭開始晃動
進而碰響
黑色衣衫飄飛自如
漏出石頭堅硬似鐵的骨頭
據說先前此地倒下無數真正的男人
石頭成堆是他們的骨頭聚攏來
讓一種精神不至被歲月驅散
——《石頭成堆的峽谷》
誠然,每一個有血有性的男人都是激情澎湃的,而發(fā)星孤獨的心中奔放的熱情卻是令人敬佩的,“讓一種精神不至被歲月驅散”,石頭成堆,形成一定規(guī)模,那種宏大的氣勢“點燃寂寞”、“死鷹的翅膀活了”,是“先前倒下無數真正的男人”用他們的身軀與心血堆積而成的精神驅然。今天我們依舊激情奔放,不是為一己之欲望,而是讓“煽動的上升欲”點燃寂寞,讓“孤獨的男人喉嚨中很快形成一只歌”,我們需要的是繼承并發(fā)揚的精神,一種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讓石頭堆成的峽谷更堅韌,更不易被驅散。
詩人不滯囿于民俗風情的畫面的簡單描述,而是深入民族文化精神的內蘊,熔象征(Symbol)、隱喻(Metaphor) 、通感(Synaesthesia),暗示等多種藝術表現手法于一爐,煉出一種沉厚深邃的意境。再如:
堅硬的石頭上裂出青春的根須
——《肝》
一句簡單的話語凝聚了詩人對肝透徹的理解。“對于詩人說,最完滿的表達就是表達出不可表達之物的不可表達性”,從人體的一個功能器官迸發(fā)出對生命動力的詮釋,發(fā)星無愧于精神靈魂的引導者。其力度與內在張力來自發(fā)星對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自然積淀即“集體無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傳承與自覺超越。
在另一種生命中獲取另一種生命
——《宰殺》
與天空與大地平行
——《死亡》
死是一種再生,是另一種形式的永存,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按照“弗洛伊德Freud在《新導論講稿》(1933)中規(guī)定的公式,我們現在必須把作為生物的個人分為三層或三級意識(Conseiousness),也就是自我(ego)、超自我(the super-ego)和本能(id)”發(fā)星將生與死,現世與來世結合,把死亡看成是通往祖先的世界、連接歷史的一種方式,這種思想既存在于族群的祖先崇拜中,更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存在發(fā)星的思維及文本的創(chuàng)作中。“集體無意識”是一個民族從原初階段以來世代相傳的某些普遍的心理沉淀與生命體驗,榮格認為它并非來自于個人經驗,而是先天存在的,是以“種族的記憶”保存下來的。
發(fā)星的詩樸素地提示了彝族的生死觀、生命的存在形式,即在現代化潮流中逐漸被遺忘或忽略了的原始的哲學思想,將人性的關懷和天然的本質展現于人們面前。
二、詩藝:巫出一種藝術的真與美
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認為藝術是天才和技藝的共同創(chuàng)造,而天才就是判斷力,即理性的認識、判斷的能力。要寫作成功,判斷力是開端和源泉,它比技藝更重要,但又必須相互為用,相互結合。應該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寓教于樂”是詩人藝術創(chuàng)造的愿望、目的,又是詩人藝術創(chuàng)造的影響和效果。賀拉斯強調通過情感影響去實現教諭的目的,“一首詩僅僅具有美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魅力,必須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讀者的心靈。”而魅力來自作者的情感,發(fā)星以天才的判斷力和創(chuàng)造力,在地域詩歌里體現一種在繼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求創(chuàng)新的精神。
彝族的畢摩與蘇尼文化充滿神性與巫性,發(fā)星深受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浸淫,無論是創(chuàng)作的積蓄與儲備,還是生活的、知識的、感情的、文字技巧的積蓄與儲備都有深厚的積淀。其作品中的巫術文化描繪得精妙、詭秘、傳神、傳奇,卻又能使人讀出一種歷史的現實感。正如托馬斯。艾略特所說的那樣,一部作品的歷史感要“牽涉到不僅要意識到過去之已成過去,而且要意識到過去依然存在……他感覺到遠古,也感覺到現在,而且感覺到遠古與現在是
同時存在的。”在發(fā)星的“鬼”系列詩作中,在民族風情濃郁的意象之下,我們亦可以讀出現代“鬼”的詮釋。
彝人心中的鬼都是美麗絕倫的
她們穿著彩裙
唱著戀歌
被經師掛于山林的路邊
——《此為送鬼一》
交頭接耳的樹露出潔白的內臟
每一片樹葉蓋住一張黑色的面孔
——《鬼林一》
發(fā)星筆下的“鬼”刻畫的可愛傳神,真正的“鬼”是美麗無邪的,可怕的是人們心中的“鬼”。每個人心中都有鬼,物欲的社會同時蒙蔽了人們,人們被“鬼”驅使,“夜里偷木者丁丁的伐聲,砍傷月亮寂靜的表情”,而發(fā)星心里也有“鬼”,那是一種純凈的、令人愉悅的“鬼”。
直達地獄
——《鬼路》
直達天堂
——《神路》
詩歌是一種神示的語言,鬼路與神路是人生的兩條路,站在十字路口,驅除心中的惡鬼,我們能象發(fā)星一樣變得純靜!
人之初,性本善。在彝族這個邊遠的山地民族原始觀念里,男女交合如同生物呼吸一樣呈自然狀態(tài)。
那里的草
那里的石頭
那里的土地
每時每刻都在狂熱的野合
——《野愛之地一》
野地
可自然的盛開一朵美麗的裙
看里面
白色的雪花
洋洋灑灑
——《野地二》
性,是奔放的,如果說對性的描述是一種道德低俗的粗獷,那么對性的贊美則是一種藝術,與所謂的“青春寫作”中的激情描寫不同,發(fā)星對性、對欲望的闡釋是飽滿的,弗洛伊德(Freud)認為性欲乃一切人類成就之泉源。沒有欲望的生活如一塘死水,如行尸走肉,我們該做的是把欲望升華。發(fā)星將人性的美好展示于美妙的詩句中,其詩作里的性愛描寫是一種自然與美的結合,沒有一絲褻瀆之意。
三、詩風:黑出一種本色的藝術詮釋
“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序),詩人的靈魂根基深潛于彝族文化的黑色土壤,黑色地域文化與黑色詩歌的創(chuàng)作是一種根與花的關系,詩人只有植根于地域文化土壤的基質中,其作品才能開出奇葩。發(fā)星將彝族原住居民的生活場景及其山地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的體驗外射于作品,作出一種藝術詮釋。
雪之子
踏雪而來
在靈魂中種入虎經
——《黑祭師》
只剩下這一群黑眼睛的人在大西南的山梁上吟唱
他們把河流嘯起來
成為一個民族的狂血
他們把黑石滾起來
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
他們把養(yǎng)子奔起來
成為一個民族的呼吸
孤獨
是保留一種純粹族性的濃密意象
孤獨
是站立在天地間形成高大之軀的惟一姿態(tài)
孤獨
沉沒了那些古血的喧囂凝固了那些閃光的咒詞
——《黑石群像·龍之崛脊》
只有那些在詩中領受到孤獨的聲音的人,才能算是懂詩的人,發(fā)星是發(fā)自內心的直白,純靜的思緒接近一種自然而平靜的“妙悟”狀態(tài)。這種“孤獨”,是彝魂的凝聚,更是整修中華民族的素質體現。
在彝族的審美意識構成中,黑、紅、黃、幾乎是一致認同的“審美色素”。在彝族世界里,三色是一種精神,是族群長期的歷史積淀,紅色是火文化,象征神圣與榮耀;黃色是精神文化,是一種金子般的品德及道義;黑色是鐵文化,是彝族這個黑眼睛、黑皮膚、黑布粗衣的民族威武不屈、深沉凝重的精神氣質之所在。在這個崇拜顏色的族群里,三色凝聚了彝文化的精髓,象征彝族人民的內在精神。
在發(fā)星的詩作“在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個詞”中,“黑虎群”、“黑石群像”、“黑皮鼓”、“黑祭服”、“黑祭師”、“黑呻吟”、“黑水謠”、“黑裙子”、“黑皮膚”、“黑金水(男陽之血)”、“黑銀水(女陰之血)”等黑色系列現代詩歌,發(fā)星從黑色出發(fā),以本色抒情,制造出一種奇跡,塑造了黑色彝魂。
四、結語:地域文化的堅守與自覺
海德格爾(Matin Heidegger)曾說過:“詩人的天職是還鄉(xiāng),還鄉(xiāng)使故土成為親近本源之處”。地域文化,通俗說法也可叫做地方文化,融風俗、儀式、典籍等的地方性知識文化為一爐。在大西南尚存著彝族畢摩神性文化、麗江納西族的東巴文化、藏族的藏傳佛教、水族的巫端之術等原初的、粗糙的、野性的地方文明,正如狄德羅所說:“一般來說,一個文明愈是文明,愈是彬彬有禮,他們的風尚就越少詩意,一切在溫和化的過程中失掉的力量。”反之,愈是蠻野之地(當然這也是相對城市文明來說,在所謂的主流文化者心目中,地域與邊緣始終是蠻野、落后以及不屑之地的代名詞),越容易產生詩意的語言、詩意的棲居者。地方文化構成了地域文化的寫作,夢亦非認為地域寫作者首先應該是一位人類學者,他得知道本地的事物,本地事物中形而上意義、本地精神。遺憾的是中華民族在演進的歷程中由于傳承中的斷代、隔離與疏遠,使得很多詩人對地域文化中的民族性很陌生。而這也恰使地域詩歌顯露其先鋒性與優(yōu)越性,而發(fā)星筆下的地域文化就是以少數民族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隨社會發(fā)展而發(fā)展的地方性文化知識,運用現代詩技將傳統(tǒng)與現代文化相結合,開拓“地域詩歌寫作”的新景象。
在這個靈魂與精神信仰極度震蕩的時代,許多詩歌失去了最初的那種自然形態(tài),在全球化語境下,在各種新的詩歌不斷解構意義,消解情感之際,卻能看到發(fā)星仍孤獨地立足地域家園文化,其精神氣質是可嘉的。發(fā)星是混血詩人,在努力回歸族群的彝文化之旅中以詩歌為媒介,以強烈的情感為底蘊,以地域詩歌寫作來彰顯涼山彝族特有的畢摩神性文化。品發(fā)星的地域詩作猶如讀其人,靈魂深處總是深邃的、純靜的、愉悅的,在發(fā)星地域詩歌的背后是一個強大的民族,而發(fā)星以其“有根性的言說方式以及自由的語言之舞”將人們帶人一個彝族的民間世界,在言說與書寫大涼山彝族人民的同時也書寫了人類所共有的東西,締造了世界文明。正如發(fā)星自己所說:“作為一個民族詩人,不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些優(yōu)秀的東西,那是對這個民族的不敬。”發(fā)星用他的混血氣質,孤傲地屹立于大涼山的邊緣,又能超越封閉的自我,在現代思潮中制造一種耐讀的彝族原生文化文本,用詩歌進入到“一個民族的精神內部以及山脈的硬度”,以充滿強烈質感的語言傳達模式使其詩歌具有真正的民族性、地域性,越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才越是具有世界性、人類性。《地域詩歌》切實體現地域文化精神的同時也指向更為廣遠博大的世界性和人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