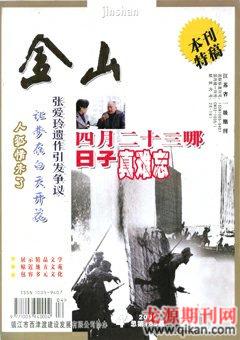四月二十三哪,日子真難忘
許益明 胡冰心
六十年前的4月23日,英雄的鎮江城迎來了解放。作為鎮江人民,自然不會忘記這一天。而對為此作出巨大犧牲的烈士家庭來說,這更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一批烈士后人回憶起那段崢嶸歲月——
4月23日,對每一個鎮江人來說,都是應該銘記的日子。
六十年前的這一天,英雄的鎮江城終于迎來了解放。作為親歷者的老鎮江,自然不會忘記這一天。而對那些為這一天的到來作出巨大犧牲的烈士家庭來說,這更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
值此鎮江解放60周年之際,筆者采訪了一批烈士后人,回憶那段崢嶸歲月。
“4·23”,我們生活的分水嶺
在鎮江新區大路鎮,提起王強,熟悉的人很多,甚至不少人會告訴你,那是烈士王思敏的兒子。
“王思敏,生于1908年,鎮江市丹徒區大路鎮王家村人,1938年參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新四軍四支隊特務連一排排長等職。抗戰勝利后,打入敵人內部,身份暴露后,繼續在圌山一帶堅持斗爭……”這一段刻在父親王思敏墓前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了王強的心里。“1948年11月22日,他不幸與國民黨軍隊遭遇,孤身單槍與敵人戰斗,終因寡不敵眾,流盡最后一滴血,為革命勝利獻出了寶貴生命……”當念到碑文最后一段時,年近七旬的王強已是泣不成聲。
父親犧牲那年,王強才8歲,但已經開始記事。印象最深的還是父親買的那把玩具手槍以及被父親帶著玩耍的一些片段。“因為組織上有紀律,連我母親也不太清楚父親的事情。關于父親參加革命的事,大多是解放后,父親的戰友以及政府告訴我們的。”
“1949年的4月23日,我這輩子也忘不了。”提起這個特殊的日子,王強激動萬分。他說,那一天是他們全家乃至全鎮江人民新舊生活的分水嶺。父親犧牲后,國民黨軍隊抄了他們的家。特別是到了1949年4月,不但他們家人生活度日如年,而且整個大路鎮都籠罩在恐怖氣氛中。“國民黨抓壯丁抓得兇,男女老少只好躲起來。”當時9歲的王強和很多人一樣躲在草垛里迎來了那個特殊的日子。
“當兵的穿的衣服不同了,說話也不同了……”回憶起第一次見到解放軍時的場景,王強連說了好幾個“不同”。他忘不了解放軍戰士臉上的笑容;他忘不了解放軍戰士解下干糧袋送給老百姓的場景;他也忘不了那位陪自己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解放軍軍官透著的那份親切……這就是大家日盼夜盼的親人解放軍,整個大路鎮沸騰了,不少老百姓紛紛走出家門,奔走相告,“解放軍來啦!解放軍來啦!”有老百姓還敲鑼打鼓歡迎解放軍,熱鬧得像過年一樣。
“可惜父親沒能看到這一天,”王強說,他們一家人很自然地想起了犧牲才5個多月的父親。此刻,撫摸著裱有父親半身肖像的鏡框,他的眼睛里飽含著淚水,講述了這張珍貴肖像的來歷。因為種種原因,王思敏烈士當時沒能給家里留下什么東西,甚至連一張照片都沒有。好在沒過多久,王思敏的一位戰友把一張王思敏贈給自己的照片拿了出來。眼前這張有些發黃、邊角有些殘缺的肖像,就是50多年前根據那張照片繪制的。“父親的戰友告訴我們,那是我父親犧牲前贈給他的。他說,當時我父親已經預感到這次任務充滿危險,所以把照片送給他留作紀念。沒想到,這一別竟然成了永別。”
在父親墓前,擦了擦碑上的灰塵,王強撥弄起數十年來自己陸續種下的黃楊等樹木,還拍了拍其中6棵連自己也叫不出名字,如今卻已是高大挺拔的大樹。“這里的位置很好,背靠秀麗的圌山,面向大路集鎮……”王強說,每年清明期間,常常會有一些鄉親前來掃墓。他相信,父親一定會把家鄉這60年來的變化發展看在眼里。
王思敏烈士墓前有一條路。據當地人介紹,這條路是鎮江解放后,大路鎮修的第一條馬路。在今年4月23日鎮江解放六十周年前夕,這條路又在經歷新一輪改造建設,正在向著更遠處延伸。
那一天,我也渡過了長江
在江蘇大學東北部的山坡上屹立著一座紀念亭,四周環繞著蒼翠挺拔的雪松、杉樹。這座紀念亭名叫王龍亭,它和附近那座王龍橋都是為紀念我黨任命的第一任鎮江市長王龍而建。
3月13日上午,筆者來到揚中尋訪王龍烈士后人。當天恰逢王龍烈士的大女兒王峰82歲生日,同在揚中生活的小弟王立榮也趕來大姐家祝壽。“我父親本名叫王隆恩,1908年出生在揚中翁家塘,1939年參加新四軍,不久便加入中國共產黨。”提起父親,64歲的王立榮言語中透著自豪。盡管父親犧牲時他才剛剛滿月,盡管父親都沒來得及抱一抱他,但絲毫不影響王立榮對父親的敬仰。通過母親的回憶、姐姐哥哥們的講述,父親的形象在王立榮心里崇高偉大。
據王立榮介紹,王龍參加革命后,先后擔任了揚中抗敵委員會主任、揚中縣縣長、蘇中五地委敵工部長等職務,1945年抗戰勝利后,又被黨任命為鎮江市市長。同年9月7日,在前往丹徒受降偽軍的途中,遭遇大批敵人,犧牲在丹徒江邊,年僅37歲。“那些年父親不但自己全身心投身革命,還動員家人親屬參加革命。在父親的影響下,我的伯父、堂叔、表哥等等10多位親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們一家都是黨員。”
年過8旬的壽星王峰精神矍鑠,口齒清楚。父親犧牲后,當年才17歲的她便和15歲的大弟王俠榮隨新四軍北撤,此后參加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轉業后她又扎根大西北,1987年離休后了回到故鄉揚中定居。“當時父親還未下葬,母親就把我和大弟送走了。”王峰說,這既是母親的決定,更是父親的安排。母親曾說,父親早就有過交代,如果他犧牲了,女兒不要出嫁、兒子不要經商,一定繼承他的遺志堅持革命。“父親希望我們能像他那樣剛強,有一次在躲避敵人追捕的途中,父親指著遠處的一座山峰說,‘看到那座山峰了嗎?鳳兒你的名字就改成山峰的峰吧!”
“揚中比鎮江早一天解放。4月22日那一天,我也渡過了長江。”王峰說,離開家鄉后,她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母親和弟弟們。1949年,在黨的培養下,她已經成了一名出色的隨軍醫務工作者。當年4月21日,她也參加了渡江戰役,而且就在揚中解放那一天,自己也和戰友們一起渡過了長江,只是她所在部隊是從安徽打到江西去。“我有預感,家鄉肯定也解放了。真希望在家鄉渡江啊!”
“其實那一天,母親也是直盯著來到揚中的解放軍,希望能從過江的隊伍中找到姐姐和哥哥……”王立榮說,盡管當時自己才5歲,但對大批解放軍來到家鄉還是有一些印象的。長大后自己也多次聽母親講起當時的情況。4月21日夜里,母親就聽到了槍聲。村里不少人都躲進了房前屋后的地洞里。第二天早上聽人說新四軍打回來了,母親非常高興,不住地向外張望。中午終于看到有一支部隊從遠處走來。“母親說,當時看到一位女戰士經過,以為是我回來了呢!”王峰接過話茬說,母女真正聚首已經是在1953年自己參加完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了,距離母親送自己離開家鄉已經快8年了。
“大弟俠榮當過新四軍話務員、后來又被黨送到中央團校學習,離休前在靖江市委黨校工作,今年也80歲了;二弟王堅今年也要有76歲了,曾留學蘇聯,回國后一直在中國農業大學教書;三弟金榮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后來一直從事航天工作;最小的弟弟立榮1970年清華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工作,你看看也已經是60多歲的人嘍……”提到這些有出息的弟弟,王峰非常欣慰。“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們都年紀大了,不過總算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
“最后的戰爭”中犧牲的鎮江人
在市烈士陵園有一座“無名烈士墓”,在這里安息的是1949年8月2日遭國民黨飛機轟炸犧牲的一批解放軍戰士。其中有個鎮江籍烈士叫武長江。
《最后的戰爭》,這是武長江的母親孟慕珍二十多年前寫下的一篇回憶錄:“1949年4月23日,鎮江解放了。在這之后,國民黨不甘心失敗,好幾次派飛機來轟炸。最后的一次是轟炸寶蓋山火車山洞,把一節車廂全部炸爛了……死了多少年輕人啊!許多人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我那伢兒是唯一的一個鎮江人……”讀到這篇回憶錄,我們強烈地產生了尋訪武長江親屬的念頭。
尋訪的歷程很是曲折。在孟慕珍的回憶錄中,提到武長江有個弟弟,于是我們嘗試尋找姓名中以“武長”二字開頭、七十歲左右的老人,“武長榮”,“廟巷”,這幾個關鍵字跳了出來。家住廟巷的武長榮是我們要尋找的武長江的胞弟嗎?
“1949年七月初八,那一天我終生難忘。聽說飛機炸了解放軍坐的火車時,我和媽媽正在大西路上……”談起60年前的事,74歲的武長榮打開了塵封的記憶。他就是武長江烈士的胞弟!武長江犧牲那年他14歲,哥哥比他大3歲。
武長榮說,他小時候家住在南門外大街。哥哥14歲那年,由于家中貧困,被母親送去了上海的姨媽那里學徒做生意。“哥哥去了上海后,陸陸續續給家里來過信和照片。哥哥17歲那年,上海解放了,聽大人說他瞞著姨媽去當了兵。”說起這些,武長榮眼中閃動著淚光。
武長榮說,哥哥平時為人正直善良,是家里唯一讀過私塾的孩子,有點文化,也比別的孩子有思想。哥哥參軍是在鎮江4月23日解放之后。武長榮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參軍后的哥哥第一次與家里聯系,寄回家一張穿著軍裝的照片,此外還給自己寄了一套軍裝和一雙皮鞋。“當時收到哥哥寄回來的東西,心里別提多高興、多自豪了!我們家兄妹三人,哥哥、我、妹妹,由于年齡相差不大,我和哥哥的感情最好了!”
鎮江解放幾個月后的8月2日,對武長榮來說,是個終生難忘的日子。那天上午,鄰居告訴母親和他,在南門火車站見到了武長江,“哥哥坐著火車隨部隊來鎮江了!聽說火車要在西站停,我和母親趕緊向西站趕,想過去見上哥哥一面。聽說國民黨的飛機在寶蓋山炸了解放軍的火車,母親仿佛已預料到了不幸,大哭了起來……”武長榮永遠忘不掉,他和母親趕到黑橋向部隊里的人打聽,聽說哥哥可能受傷了,于是他們被領著去了現在的第二人民醫院,結果沒有找到哥哥,隨后又趕到現在的江濱醫院,“結果在犧牲的烈士名單里,發現了哥哥的名字”。
武長江的墓在烈士陵園,武長榮每年清明節都會去祭掃。武長榮唯一覺得遺憾的是,當年哥哥寄回家的東西和照片等遺物都沒能留下來。“哥哥犧牲后,對我的影響和觸動很大。讓我在后來的人生中,一定要做正直、善良、愛國的人。雖然我已七十多歲了,但這個信念始終沒有改變過。我們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這是我哥哥和無數像我哥哥一樣的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我為有這樣的哥哥感到驕傲自豪!”
解放后,我和親人得以團聚
走進市烈士陵園紀念館二樓陳列室,在正對入口的地方有一組4張大小相同的照片整齊地排列在一起,總能引起很多參觀者的格外注意。這些照片和照片下方的勛章、筆記本、銅臉盆等物品共同記錄著一對烈士兄妹和一對烈士夫婦的革命歷程。
“這就是我的父親左治平,本名叫左濟生,解放前夕在常州被敵人秘密殺害;這是我姑父張仲英,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年他被敵人殺害;這是姑媽左冰,她渡江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60年病故,被追認為烈士;這張照片是姑媽隨新四軍北撤前和我父母拍的合照,上面的那個孩子是我的哥哥……”清明前夕的一個早晨,筆者在這些照片前,聆聽左治平烈士幼子左平講述父輩參加革命的往事。
左治平1918年出生在揚中一個生活相對富足的農民家庭。1939年春,上完師范回到家鄉不久的他,便參加了新四軍挺進縱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揚中三區區委書記、山北縣委副書記、鎮丹揚工委委員等職務。1948年左治平在丹陽埤城雀梅墩被國民黨保安隊包圍。被捕后,左治平受盡酷刑后,不幸于1949年解放前夕在常州監獄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年僅31歲。在胞兄左治平的影響下,1940年時年16歲的左冰也投身革命。1945年,左冰與志同道合的張仲英結為革命伴侶。解放前夕,參加新四軍北撤在蘇北堅持斗爭的左冰獲悉,留守江南的丈夫和胞兄已先后被敵人殘酷殺害。
“母親和姑媽很少對我們講過去的事,但姑媽寫了《懷念我的哥哥》、《懷念仲英》等文章……”今年61歲的左平說,有關父輩參加革命的詳細情況,自己大多是通過閱讀姑媽在1959年左右寫的回憶錄了解到的。1958年,9歲的左平到上海治病,從此和姑媽一起度過了將近3年的母子般生活。“姑媽是個很重感情的人。后來她一直沒有再結婚。經歷那么多打擊,她工作上更拼命了,最終積勞成疾,病逝在上海……”
“那一天,母親和我不在鎮江。但那天以后,我們回來了。我們的親人終于漸漸團聚了。”提起“4·23”這個特殊的日子,左平顯得非常興奮。盡管有關于那天的記憶都是來自祖父,但祖父講的每一句話都刻在了他的心里。“爺爺說,4月22日見到解放軍來到了揚中,心里別提多高興了。奶奶都激動得哭了。”左平說,當時祖父母還不知道父親已經犧牲了。對祖父母來說,看到解放軍,就等于看到親人了;看到解放軍,就知道一家人團聚的日子不遠了……祖父母原本有11個孩子,但因為種種原因,長大成年的就只有父親和姑媽兩個。而這雙兒女卻都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老兩口日夜盼望的就是早日得解放,一雙兒女平安回家鄉。”
1949年4月22日、4月23日,揚中、鎮江終于先后迎來解放。此時的左平還只有1歲多。母親抱著他在金壇一戶有錢人家里做保姆。“保姆只是掩護。其實我母親是地下黨,1940年入黨后,就一直在做交通員,為組織傳遞情報。母親帶著1歲大的我,很隱蔽,那戶有錢人家還要買下我當兒子呢……”左平說,當時母親只知道父親被捕了,但還不知道父親已經被敵人殺害了,只盼著早日解放,救出父親。而此時在揚中,黨組織已找到左平的祖父母,讓他們盡快將左平母子接回揚中。于是,了解情況的祖父很快把左平母子倆接回了家鄉,在上海工作的姑媽不久也回到家鄉看望父母。經過多方努力,父親的犧牲地最終得到了確認。盡管沒能找到遺骨,但左平和家人還是在栗子山公墓為父親建了衣冠冢。前些年母親去世后,左平又把母親安葬在父親墓旁。
“清明快到了。在北京工作的兒子前兩天打電話說,要帶兒媳和孩子回家鄉看看,拜拜爺爺奶奶。”左平欣慰地說,正是千千萬萬像父母、姑父、姑媽那樣舍生忘死的先輩,才有了今天的美好生活。“看到現在的孩子們懂得珍惜和感恩,我很高興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