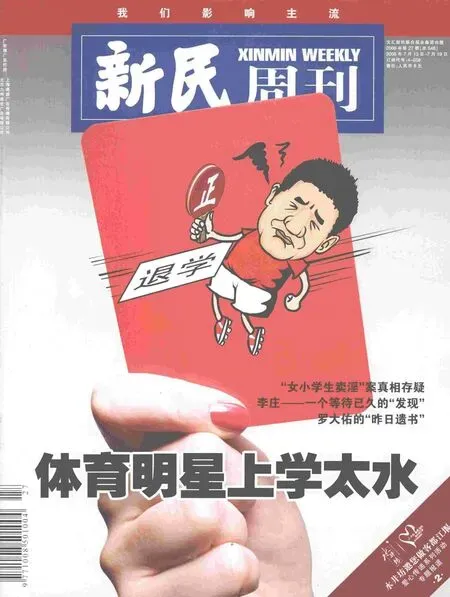洪都拉斯:軍事政變還是憲政之爭
馬曉霖
面對洪都拉斯危機,需要進一步廓清的問題是:總統、議會和最高法院這三者誰擁有憲法規定的最高和最終話語權?
洪都拉斯,一個人口不足800萬的拉美小國。6月底,曾有過100多次政變記錄的洪都拉斯再掀政治巨浪,出現總統被罷免和驅逐,臨時政府與國際社會嚴重對峙的局面。
28日凌晨,洪都拉斯總統塞拉亞被破門而入的士兵押上直升機,投放到鄰國哥斯達黎加的一個機場。同時,洪都拉斯最高法院以“違憲”和“叛國”等罪名罷免塞拉亞的總統職務,由頭號反對黨領導人、議長米切萊蒂出任臨時總統并組成臨時政府。顯然,塞拉亞在這場權力角逐中,貌似孤家寡人,不但失去黨內支持,還被左右政權命運的立法、司法和軍隊無情地聯手奪權、驅逐,甚至教會領導人也呼吁他別再回來。
國際社會乃至美國都對洪都拉斯的政變給予不同程度的譴責、抵制和制裁,拒絕承認其結果。面對被美洲組織除名、部分國家關閉邊境、召回使節、停止官方合作等威脅,洪都拉斯臨時政府態度強硬,率先宣布退出美洲國家組織,威脅不惜以武力阻止塞拉亞回歸和外來干涉。在地區和國際層面,洪都拉斯的政變力量又成為眾矢之的。
洪都拉斯,這個已在民主與憲政之路上走得比較平穩的國家正經歷著戲劇性的變局。被罷黜、驅逐的民選總統得到幾乎一邊倒的國際同情和支持,卻在國內遭受著反對派如此強硬的排斥和抵制;雙方都在指責對方違背憲法,也都在強調自己維護民主與法制。理與力的較量、左與右的碰撞、違憲與護法的是非、國家主權與外來干預的對錯,道義與利益的權衡,盡在塞拉亞的去留中得到體現。
塞拉亞原本出身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黨,2006年以中右翼保守派候選人身份勉強當選。執政后的塞拉亞順應地區和本國社會思潮的主流,采取一系列向左轉的措施,矛頭指向“三座大山”:官僚買辦和富裕階層、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國)和軍閥,提出還權于民、分享民主、加強民眾參政議政力度和利益向底層人群傾斜等主張。這些政策得到民眾擁護,卻開罪了勢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他們把持著議會、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軍隊。民意通過普選方式可以把塞拉亞推上總統寶座,卻無法在憲政框架內繼續給予他更多支持,缺乏強勁實力后盾的塞拉亞注定要遭遇致命反擊,這就是議會政治游戲規則的必然性,也是對總統有無能力擺平各種力量的一種考驗。
既然代表了底層利益,脫離權勢階層而躋身其對立面,塞拉亞的權力基礎就已經被動搖了,而他的特立獨行又加劇了對手的恐懼。這些年,拉美地區右翼失勢,左翼崛起,多數國家的左翼力量通過議會民主方式取得國家政權,并逐步形成陣營和聯盟。塞拉亞不但在內外政策上積極向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的左翼或中左翼政府靠攏,而且打算將其偏左的政策長期化,決意效仿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試圖借助修憲實現連任,這無疑徹底激怒了右翼的權勢階層。
還原事變全過程可見,塞拉亞和對手們在這場權力爭斗中都在利用憲政手段,都在遵循某種程序,似乎很難界定誰違憲、誰非法。塞拉亞提出今年11月進行全民公決,修正總統不可連任的憲法條款。反對黨主導的議會發表公告表示反對,認為這將導致總統終身制和專權。塞拉亞又堅持在6月28日就這一議題先行公決,并命令軍方押運、布置和看管票箱。軍方稱議會反對公決,拒絕服從總統命令,塞拉亞便將總參謀長撤職并接受國防部長以及陸海空三軍司令的抗議辭職。最高法院裁定塞拉亞的行為“不具法律效力”,要求他恢復軍方將領職務,塞拉亞拒絕接受最高法院裁決,執意按原計劃實施公決,總檢察長則要求議會罷免總統。于是出現了政變,而且最高法院認定軍方拘押驅逐塞拉亞的行動合法。
在憲政體制內、總統、議會和高法都是通過民選方式產生,具有相同的法源而相互之間存在制約關系。軍隊不能介入政治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但它需要向代表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最高權力效忠。面對洪都拉斯危機,需要進一步廓清的問題是:總統、議會和最高法院這三者誰擁有憲法規定的最高和最終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