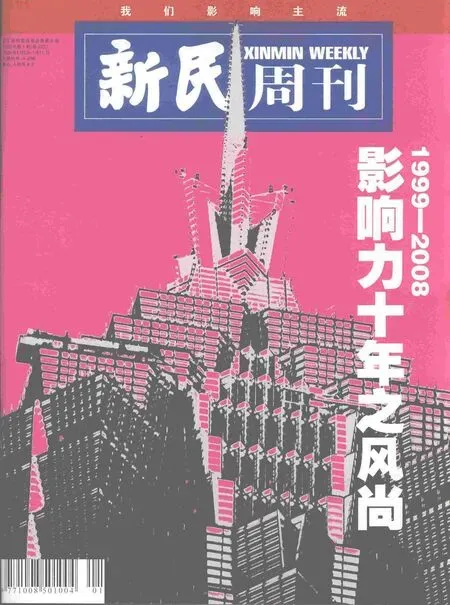不是“臺巴子”,是“新上海人”
賀莉丹
“我是新上海人!”趙世崇拍拍胸脯,朗聲道,“臺北是我的家鄉(xiāng),但上海就是我的家!”
上海1990
窗外車水馬龍,上海靜安寺的百樂門舞廳氤氳的燈光下,舞者翩翩。時間仿佛在這里倒流,“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懷舊的音樂舒緩極了。
趙世崇,上海百樂門董事長,此刻的他西裝革履,帶著淡淡笑意,架著金絲邊眼鏡,金戒指與金手表閃閃發(fā)光,跟他遞過來的名片如出一轍。仿佛舊月份牌上走下來的他,似乎就應該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的老上海。
趙世崇原本在臺灣從事證券投資業(yè)務,后進入臺灣的餐飲娛樂業(yè)。作為最早進軍中國大陸的臺商之一,到上海后,趙世崇的投資重點依然在餐飲娛樂業(yè)。

1990年,43歲的趙世崇第一次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土地,他的首選就是上海。畢業(yè)于臺灣商業(yè)專科學校的趙世崇算是祖籍廣東、生在臺灣的“本省人”,他有許多來自上海的“外省人”同學,念書時,他特別喜歡跟溫文有禮的他們在一起。
“我從小就對中國大陸情有獨鐘,改革開放了,我終于有機會到中國大陸來。我第一次來上海的時候,是晚上,當飛機下降時,我看到這個都市烏漆墨黑的,那時,從虹橋機場到市區(qū)有一段還是石頭路,顛簸得厲害”,趙世崇向《新民周刊》記者回憶,也在那時,他親身感受到上海的機遇與潛力,他也深刻意識到,“臺灣經(jīng)濟如果不跟大陸結(jié)合在一起,就沒有出路,我一到大陸就明白這個道理了”。
20世紀40年代末,10萬上海人遷徙到臺灣。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兩岸關(guān)系解凍,上海刮起“臺灣風”,“如果不想受shanghai(傷害),就請趕快去Shanghai(上海)”,臺灣人都知道這句話。實際上,關(guān)于上海的想象已在臺灣醞釀多年,從一個務虛的話題終究轉(zhuǎn)換成切實的投資浪潮。如今,許多臺灣人就與我們比鄰而居,帶著“臺灣腔”的普通話,甚至已經(jīng)影響到上海方言的語調(diào)句法。當年有些貶義的稱呼“臺巴子”,隨著交往的增多,也已經(jīng)淡出了滬上流行語。
1990年,趙世崇在上海長寧區(qū)建造了兆豐大樓,時為上海首屈一指的商業(yè)樓盤;1992年,他創(chuàng)辦了上海藍帶娛樂總匯;1994年,他與臺灣海霸王合作成立上海溫莎堡海霸王,將臺灣的自助餐帶到上海,一時間門庭若市,在斜土路上出現(xiàn)了三四千人共進晚餐、幾百人等候座位的盛景。“這19年來,我眼看著上海一步步走到今天,變化越來越大”,在上海創(chuàng)業(yè)的同時,趙世崇無疑見證了上海高速發(fā)展的歷程。
勤勉之質(zhì)
趙世崇一直有濃重的“百樂門情結(jié)”。初中時代翻閱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白先勇先生記憶中鏡花水月般的海上舊夢,由舞女大班演繹出百樂門的絕代風華,讓他記憶猶新。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灘,十里洋場,氣象萬千,極富代表性的是豪門名流的主要娛樂場所百樂門,號稱“遠東第一樂府”的它,曾是當年大上海的代名詞。
但在20世紀60年代,臺灣課本里的大陸,一如早年大陸課本里的臺灣,“水深火熱”。在當時,兩岸猶如堅冰,遙想百樂門,成為趙世崇一個不可觸摸的夢。
1990年剛到上海,到酒店放下行李,趙世崇迫不及待地跑去“瞻仰”百樂門,他見到的卻是“紅都電影院”的招牌,小賣部、咖啡座等不同經(jīng)營者各自為陣,“百樂門怎么如此凋零?”興沖沖的他極度失望,黯然離去。
10年后的2000年,趙世崇聽說百樂門建筑被列為上海市第一批優(yōu)秀保護建筑。當上海靜安區(qū)文化局想要恢復百樂門大舞廳時,他終于明白自己一直等待的是什么。
“要奪得百樂門經(jīng)營權(quán)并非易事,當時參與競標的有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區(qū)、馬來西亞等世界各地的雄厚財團,最后,讓我一個小臺商取得了經(jīng)營權(quán)”,趙世崇言談謙遜:“我在上海累積了10年正規(guī)的經(jīng)營經(jīng)驗,我很本分、守法地在做餐飲娛樂,得到政府部門肯定;并且,我的理念是把百樂門恢復成30年代的百樂門,所以政府部門很支持我。”
憑借在上海娛樂業(yè)穩(wěn)定的背景與資質(zhì),趙世崇順利地取得百樂門經(jīng)營權(quán),他投資了2500萬元人民幣,對總建筑面積3500平方米的百樂門進行恢復性改建,提案與圖紙進行3次審核認證后終于通過。爵士樂隊曾是百樂門的經(jīng)典之一,通過朋友引薦,2002年,趙世崇尋覓到當年曾在百樂門演奏的老樂手鮑正禎。趙世崇也有自己的設想,20世紀30年代百樂門的舞伴只有女舞師,“我找的舞師,男女都有,而且都有非常正規(guī)的專業(yè)背景”。
2004年12月1日,“上海1930懷舊舞劇”粉墨登場,趙世崇親自挑選節(jié)目,排練一個月,一場匯集“上海灘”、“飛虎隊”、“夜上海舞女陳曼麗”、“歌女周璇”等各種懷舊元素匯演現(xiàn)身百樂門新舞臺,前來觀演的人們仿佛進入了“時光隧道”,身臨其境。
“我想,在上海近20年,讓我感到非常驕傲的是:我能以臺商身份取得百樂門的經(jīng)營權(quán)。我覺得,這是對我個人的肯定”,趙世崇不止一次地感慨。懷舊氛圍濃濃的百樂門,讓趙世崇的許多朋友專程從臺灣趕過來,晚上跳跳舞,一睹老上海風情,“到了晚上,燈光比現(xiàn)在更漂亮,還有歌手唱歌,每個人的打扮都很講究,有些太太一晚上要換好幾次衣服。我小時候的夢想實現(xiàn)了!”趙世崇的眼神亮了起來。
上世紀90年代,每次回到臺北,都有許多朋友向趙世崇咨詢他的“上海經(jīng)驗”;現(xiàn)在,趙世崇形容百樂門已經(jīng)成為臺商們在上海的“商務咨詢中心”,“他們買房子、投資,不管做什么,都找我來問”。
“上海小臺北”
而今,趙世崇每年約有11個月在上海,春節(jié)、清明則按慣例回到臺北陪伴年邁的父親,他的兩個孩子在日本、美國完成學業(yè)后,也回到上海工作。“我是新上海人!”趙世崇拍拍胸脯,朗聲道,“臺北是我的家鄉(xiāng),但上海就是我的家!”
如今,趙世崇在中國大陸還有他龐大的版圖設想,他期望在昆山、合肥發(fā)展可容納千人的演藝廣場,將百樂門做成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大型歌舞秀品牌,“像法國的紅磨坊一樣,預計在世博會前后推出”,他躊躇滿志。
“不做第一,只做唯一”是趙世崇的座右銘,同許多勤勉的在中國大陸打拼的臺商一樣,時至今日,他依然未有懈怠,清晨6點起床,“幾乎醒過來就在工作”。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在上海及周邊城市定居的臺胞及親屬就高達50萬人以上。如今,坐落在上海西部的古北小區(qū),集中居住了眾多臺商,被譽為“上海小臺北”;古北新區(qū)與虹橋開發(fā)區(qū)一帶,已形成一個臺灣人社區(qū)。有人戲稱,近年上海房價的居高不下,有著臺胞的一份“功勞”。
雖然工作繁忙,但只要一有空,趙世崇還是喜歡聽音樂或打高爾夫,或者去百樂門跳跳舞。趙世崇與夫人魏美玉因舞結(jié)緣,他們本是高中同學,當時流行每個周末同學輪流組織家庭式舞會,他們有了機會跳交誼舞,跳來跳去有了好感,最終邁入婚姻殿堂。
與眾多在大陸投資的臺商一樣,趙世崇非常關(guān)注島內(nèi)的政經(jīng)狀況,阿扁的洗錢弊案、臺灣股市滑坡都是他們常常探討的話題。早在2007年年底,趙世崇就跟他的朋友訂好了2008年3月回臺灣的機票,“我們害怕誤了‘大選的投票,3個月前就訂好機票了,我的很多朋友甚至半年之前就訂好回臺灣的機票了。我想,幾乎90%的臺商都回臺灣參與投票”,趙世崇說,在大陸的臺商都不希望政治波動影響到經(jīng)濟發(fā)展。
趙世崇居住在虹橋,而他在臺北的家位于松山機場附近。以前,趙世崇與家人需要繞道從香港轉(zhuǎn)機回臺北,路上需要一天,因此,他們常是清晨出門,到香港接近中午,到臺北已是晚上,每次返鄉(xiāng),都興師動眾。而如今,海峽兩岸大三通夙愿完成。“十幾年來,我多花的交通費大概在人民幣300萬以上;現(xiàn)在,1小時20分鐘的飛行就能從上海到達臺北,比我從上海到昆山還要快”,趙世崇看看手表說,此時他的一個朋友已從上海起飛,“回到臺北正趕上吃午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