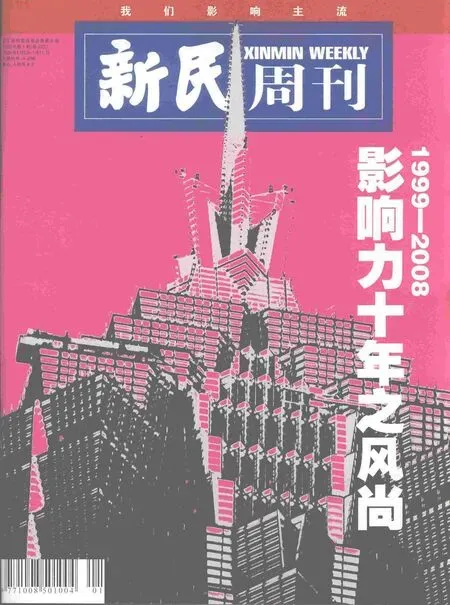從水師走向藍水海軍
倪樂雄
當下的觀點無非圍繞“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崛起論”作各方面的展開和揣摩。其實這兩種認識都帶有濃厚的主觀上的一廂情愿,嚴重偏離客觀真實意義。
中國政府為維護本國商船和國際重要水道的集體安全,于近日決定派遣海軍前出印度洋參與聯合國授權的圍剿索馬里海盜的各國海軍聯合軍事行動。這一決定引發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當下的觀點無非圍繞“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崛起論”作各方面的展開和揣摩。持“中國威脅論”者憂心忡忡,以為中國借清剿索馬里海盜之機,乘勢向印度洋拓展自己的影響,更有甚者,西方某些媒體懷疑這一舉動是中國外交軍事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信號。持“中國崛起論”者在民族主義激情鼓舞下,認為這是中國崛起的象征性事件,感到歡欣鼓舞。其實這兩種認識都帶有濃厚的主觀上的一廂情愿,嚴重偏離客觀真實意義。
護航艦隊不是“鄭和”
毋庸置疑,中國海軍這次前出印度洋具有史無前例的意義,但這種意義是文明和社會轉型結果賦予的,而非單純的軍事層面賦予的。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60多年來,中國實際上進行著從傳統原始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文明、社會、國家轉型的根本在于經濟生存結構或狀態的轉型,政治、外交、軍事、教育、法律、道德、倫理、宗教、風尚、習俗、意識形態、社會價值觀等等上層建筑都從根本上都產生于、并服務于經濟生存結構。

西方文明的歷史規律表明:在“霍布斯法則”支配下的人類社會,一個國家生存狀態從“內向型經濟結構”一旦變為“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就必然召喚強大的海軍,這一規律幾千年不變。海軍起源于依賴海洋貿易而生存的海洋國家對海外貿易的保護,海軍為涉及國計民生的國家海外利益保駕護航,自古以來就是天經地義的行為。從古希臘最早出現的科拉西城邦的海軍到今天的美國海軍,海軍維護海外貿易的職能千年不變。美國第七艦隊的宣傳手冊開門見山道:“美國為何需要全球軍事存在?因為我們的商業利益遍及世界。”西方文明的精髓之一是:“金錢到哪兒,炮彈跟到哪兒。”形象地講,海外貿易好比妻子在外做生意,海軍好比丈夫,妻子到哪兒丈夫跟到哪,不然遇到強盜會人財兩空。所以,中國此次派遣海軍目的在于捍衛國家的海外利益——商船和“海上生命線”的安全(一百多年前中國人根本沒有這種意識),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中國已從“傳統內向型經濟結構”轉型成“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它的海軍出動屬于海洋國家的行為,海軍功能不再僅限于“防止帝國主義從海上侵略本土”,從而擺脫了農耕民族的海軍永遠是“陸軍海戰隊”的千年命運。
也許有人會說,明代曾有過鄭和艦隊七下西洋,福建閩南海上商業軍事集團鄭成功的艦隊也曾進入印度洋。談不上史無前例,也有媒體稱:“鄭和艦隊又回來了!”這些都是皮相之見。鄭和下西洋同此次中國海軍派遣性質不同,前者是農耕文明成果在海外的展示,是東亞朝貢外交體制的政治行為,以海上軍事力量宣示、服務于中華文明的“禮制”觀念,表達的是農耕文明的政治訴求,維護農耕經濟區域本身需要的外部安全;后者是直接維護涉及國計民生的海外經濟利益和國家“海上生命線”。前者間接影響國家安全,沒有海上力量,本土依然繁榮富強,后者直接影響生死存亡,沒有海上軍事力量,國家生存岌岌可危,體現了西方地中海文明規律:海洋國家的命運與海軍興衰息息相關。這就是兩者背后所包含的全然不同內涵。鄭成功的閩南海上商業——軍事集團雖然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性質的海軍,也使用海軍保護海上貿易,但規模上屬于弱小的海上割據勢力,并不代表幅員遼闊的大陸農耕經濟結構的國家主體。正因為包含了如此豐富的歷史和現實內涵,從而使此次海軍出動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意義:中國作為國家主體歷史上第一次派遣海軍為國家海外商業利益護航,中國海軍代表國家主體首次被賦予新的職能,領受了前所未有的使命。
以上便是派遣海軍護航的實質意義所在和新奇之處,如果看成是中國崛起、中國強大的象征多少有些自作多情。那是一種在同他國相比較下、甚至相對抗下占有絕對優勢的狀態,而目前中國海軍還遠遠未達到這種狀態。即使和當時鄭和艦隊、鄭成功艦隊在印度洋的地位相比,我們的地位還不如那時的他們。我們僅僅做了本該做的事而已,從發展眼光看遠洋能力增強了,但算不上強大。歷史上強大的海軍總是在經過幾場惡戰并取得勝利后,才能談論崛起、強大與否的話題,不經交戰表面強大不是真正的崛起,不宜談論這個話題,北洋海軍就已成為這種話題的笑柄,而某些人因為一個大國海軍正常護航和剿滅幾個海上毛賊,就來談論強大、崛起恐怕徒惹外人譏笑。
陳詞濫調“威脅論”
如果把此次海軍出動看成是“中國威脅論”的證據,似乎有點張冠李戴了。即使將來中國海軍表面實力強盛、遠洋能力走得更遠,也未必一定要走西方國家近代殖民主義、海上霸權的舊路,因為西方國家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過程是在“霍布斯文化”背景下展開的,千百年來,世界的無序狀態導致國家之間在世界資源分配上的零和博弈關系,迫使“國家們”生活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中,根據霍布斯法則,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本質上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關系”。在這種生存環境中,一個大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必然加劇世界沖突而引發戰爭。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展開的,世界資源分配已按共同的“游戲規則”進入有序化階段,每一個國家的生存都嚴重依賴世界經濟體系,每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最終將殊途同歸同一個目標——維護世界經濟體系。經濟一體化將導致行政管理一體化,進而促成軍事管理一體化。如果歷史按這樣的方向前進著,即便有些大國懷有“霍布斯式的動機”,但歷史的發展法則也將迫使它們改變軍事力量的職能,服務于永久和平性質的基礎——世界經濟一體化體系。這點已在此次各國對付索馬里海盜的海軍聯合行動中露出端倪,同樣,歐共體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最終導致了歐洲長久和平體制的建立。在這樣的體制內,某個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不會被其他國家認為是對自己的威脅,相反有助于集體安全。某些西方國家是殖民主義的老手、海上霸權的“過來人”,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把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以及中國遠洋海軍的建設和派遣,總看成是自己的過去在今天的再現,未免有些小人之心了。
和海軍前出印度洋一樣,“中國威脅論”者對中國即將建造航空母艦更感到憂慮,似乎在雙雙印證中國軍事外交某種不祥信號。事實上,航母只是一種兵器,本身不代表侵略擴張,它的作戰功能是將有限制空權變成無限制空權,任何一個海洋國家的國防都需要這種能力。隨著中國經濟生存結構的轉型,為應付直接影響國計民生的國家海外利益以及“海上生命線”安全的不測之虞,中國遲早需要現代遠洋海軍的核心艦種——航空母艦。
事實上,中國早就需要自己的航母來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2004年4月24日,埃塞俄比亞的反政府武裝“歐加登民族解放陣線”血洗中國中原油田勘探營地,殺死中方人員、搶走全部車輛、搗毀全部勘探設備。最近又有非洲國家的反政府武裝揚言中國等外國公司不要到當地從事資源開發,否則后果自負。如果中國航母在亞丁灣和東非沿岸游弋,或經常“友好訪問”非洲,如果航母上的海軍航空兵精確打擊足以摧毀地面一切目標,如果“歐加登民族解放陣線”之類的土著武裝知道我們具有這樣的打擊能力,那他們還敢肆意踐踏中國的海外利益嗎?
歷史的教訓是:要維護海外動蕩地區的利益,一定要有強大的軍事存在,這樣沖突各方不會惹你,生怕你幫對手滅了自己。如果你是弱者,各方都隨時把你當作和對方沖突犧牲的籌碼。這就是索馬里海盜沒有搶過一艘美國貨輪,而我們的貨輪卻屢屢遭搶、中原石油勘探營地遭血洗的原因。當年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率大軍即將攻克武漢,英國一介商務領事出面阻止,一句話便讓陳玉成退兵,強大的英國在清王朝和太平天國的內耗中玩得游刃有余。我們不能因為居心叵測的“中國威脅論”者的無端猜疑而放棄航空母艦為核心的遠洋海軍建設,卻任憑同胞的生命財產和國家海外利益在外被肆意踐踏。
上述僅僅是和平時期,同樣,盡管我們這個世紀已露出永久和平的曙光,但誰也不能保證中國永遠不會遇到戰爭了,如果中國遭遇一場不以自己和平意志為轉移的戰爭,沒有航母為核心的遠洋海軍是不能奪取制海權的,因為現代制海權的爭奪是通過海上制空權爭奪來完成的。而奪取制海權一方一定能夠戰勝龜縮在陸上的所謂陸權國家。蒙哥馬利元帥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總結道:“歷史的重大教訓是,對方實行陸戰戰略是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根本上看,是一場爭奪海上航道控制權的斗爭。”因此,那些主張中國回歸陸權、放棄海權和航母、以免引火燒身的觀點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對國家國防建設的誤導和對子孫的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