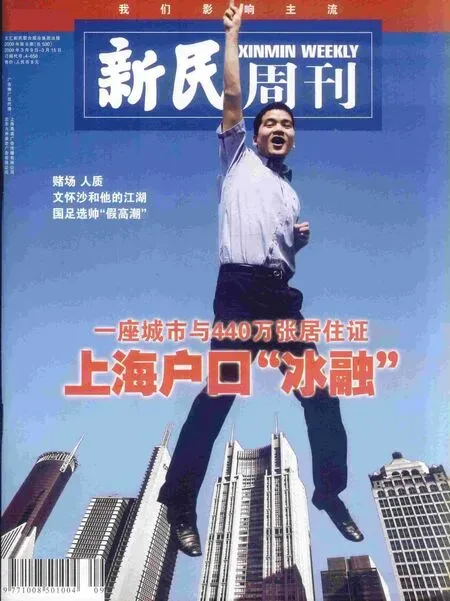佛斯特訪問尼克松
靈 子

歷史比電影來得無情。原以為這場對話是兩個失意者碰撞出的火花,原來不過是兩個聰明人的雙贏。
“我讓美國人民失望了。”在大大的特寫鏡頭里,尼克松布滿皺紋的臉顯得滄桑疲憊。他因水門事件被從總統的位置拉下馬,以總統的身份踐踏美國的憲法,卻從未為此公開道歉。直到這一刻。
使他說出這番話的是坐在面前的大衛·福斯特,英國電視節目的脫口秀主持人。沒人料到他能順利訪到尼克松。第一,尼克松好不容易被繼任的總統福特給予赦免,免掉上法庭的難堪,為何還要主動接受媒體的詰問?第二,即便尼克松想談,又哪里輪得到福斯特?美國大有如《60分鐘》的邁克·華萊士等等名記,而福斯特在美國名不見經傳,此前剛因收視率不濟被取消在紐約的節目,每周被迫于倫敦和澳大利亞間往返主持“驚險逃生”。
可機會偏偏砸在了福斯特頭上。尼克松正看中他的無名無勢,料想自己可占絕對上風,一來要借節目為自己澄清,渴盼重樹形象,甚至再次回到政治舞臺;二來趁機賺點零用——他借經紀人之口向福斯特索要采訪費60萬美元。
分為四期的電視節目里,尼克松在前三期占據絕對上風。這位曾與赫魯曉夫和毛澤東談判的高手毫不費力地應對一切質問,轉移話題、放大無關細節、拖延時間、著重講述自己的政績,三次的訪問如同垃圾時間一樣迅速被消耗掉了。
是什么讓他在第四天放棄抵御?在這最后一集節目里,尼克松不僅表達了自己的遺憾,還坦誠說出自己長期以來的信仰:“總統無論做什么都是合法的。”僅憑這兩句發自內心的表述,這個節目已成為經典,并成為后來諸多學者研究尼克松的可信資料。
為什么尼克松說出了心里話?誠然福斯特借助手之力,找到水門事件中被疏漏的證據,伺機以死硬問題伏擊,使對方措手不及。但這一切都源于尼克松此前深夜打來的電話。他抱怨、咆哮、喋喋不休,使福斯特得以窺見這個巨人背后脆弱的一面。事實上,他們都不過是落寞的失敗者。他們都為進入主流而拼命奮斗,得到的卻總是奚笑冷落,他們都曾經取得事業的輝煌,卻仍然甩不掉心底里隱隱的自卑。
尼克松也許是因為窺見這樣的相似而袒露心扉。他終于卸下盔甲,還原為一個普通男人。在結尾那個特寫里,他脆弱、無力、傷感,簡直要讓人原諒他所犯過的罪了。
只是電影始終是電影,它刻意削弱福斯特,成就了一個具有莫大魅力的尼克松。而歷史并沒有這樣打動人心。當時的民意測驗顯示,看過節目的美國觀眾,有69%認為尼克松仍然想要掩飾自己的過錯。
現實中尼克松從未打過那通泄露心思的電話,福斯特也沒有那么不堪一擊。事實上,他一直在采訪政治人物方面頗有心得。但不可否認的是,與尼克松的對談是福斯特事業的巔峰,它的唯一性與重要性為他今后的事業鋪平了道路。福斯特迅速登上《時代》與《新聞周刊》的封面,并憑此名聲陸續采訪了福特、吉米·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頓與小布什,名利雙收。
尼克松也不吃虧,不但拿到采訪費,還有電影中未提及的一項收益——那次電視訪談收入的20%分紅。要知道那期節目創下的收視率至今在美國政治新聞類節目中未被打破,僅福斯特本人就賺到100萬美元。
歷史比電影來得無情。原以為這場對話是兩個失意者碰撞出的火花,原來不過是兩個聰明人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