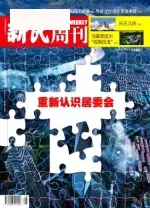龍應臺:時代怎樣“被記憶”
燕 舞
“法蘭克福書展表面上是在比成品,實際是在比哪一個社會有最豐沃的土壤,有最自由的空氣和獨立的精神。一個社會一旦具有這些品質(zhì),產(chǎn)品自然會好。”

“其實,我還想來北大講學一年呢,但不知道北大能不能像港大那樣提供條件給我。”10月下旬,當下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作家龍應臺接受筆者專訪時,如是表達了她最近的一個心愿。一個多小時的專訪結束后,她特意走到北京華僑大廈門口“呼吸一下新鮮空氣”;辨認著王府井大街上的行道樹到底是楊樹還是榆樹,借機體察“唐詩宋詞的中國”。
從2004年夏天開始,卸任臺北文化局局長的她到香港城市大學訪學一年,參觀港大教授公寓時看到的“一片海”讓她決意留下。港大5年,讓她發(fā)現(xiàn):“港大有一個非常新的狀況,研究生幾乎80%以上是大陸學生。”
專訪次日午后,“龍應臺《目送》新書見面會”在北京三聯(lián)韜奮圖書中心舉行。在穿插著演講、歐洲式誦讀和問答的兩個半小時見面會上,除了拒絕“你化妝嗎?怎么保持這么好的氣色?”一類的個別問題外,龍應臺基本上是知無不言。她再一次表達了她最近的心愿:“我確實希望有機會能到北京來長住一段時間,住半年或者一年。如果我有過在中國大陸真正的腳踩在泥土上的生活經(jīng)驗的話,我再來寫(一些題材)會不一樣,會更好。缺了這塊泥土上真正的生活經(jīng)驗,你就比較不容易知道這片土地上真正的痛之所在和情感。”
文化輸出的差距
1980年代初,旅美苦學9年的龍應臺在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后,回到臺灣執(zhí)教和寫作。1984年,她在《中國時報》撰寫“野火集”專欄,吶喊“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因?qū)顸h威權統(tǒng)治的猛烈抨擊和對公民意識的倡導而引起熱烈反響;次年,“野火集”結集出版,不到1個月內(nèi)再版24次,被詩人余光中譽為“龍卷風”。從1986年,起,她旅居歐洲共13年,其間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開設“臺灣文學”課程,并在歐洲報紙如《法蘭克福匯報》撰寫專欄。
龍應臺在法蘭克福住過11年,那時每年都會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今年也以臺灣出版商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了10月19日剛剛閉幕的第61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100多年才能輪到做主賓國的機會。它不同于汽車展等一般的商展,其實是思想展,各個國家借此展示自己最有潛力被外國買去的書。它是各個國家文化輸出的競賽,是思想競技的場所”,龍應臺很為中國是這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主賓國而高興,也很為中國圖書在裝幀設計等領域的微觀進步而欣慰。
但“中國在所謂大國崛起的趨勢里,相較于商業(yè)輸出,文化輸出這塊是比較落后的。中國作為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其實接受了一個刺激:在文化輸出上,與國際的差距那么大”,龍應臺也看到了中國出版在全球化態(tài)勢下需要奮起直追和錦上添花之處,“中國的展臺上有很多很多書,但這些書能被國際社會認可的比例是很低的。”
對于大陸官方近年大力倡導的“出版走出去”戰(zhàn)略,龍應臺認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首先,“輸出之前,你要去了解什么樣的書才能打入德文、英文等市場”,“這勢必要我們對英文世界、德文世界進行深入了解,而對文化的理解比對汽車、電冰箱市場的了解面臨的挑戰(zhàn)更多,是需要下功夫的”;其次,出版品乃至文化商品“無論在思想深度、對世界認知的廣度和文字藝術的高度上,(本身品質(zhì))都要好,這是一個競技的事情”,“一個社會的文字作品,不止文學,要達到最高境界,社會一定要給它最寬廣、刺激最大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法蘭克福書展表面上是在比成品,實際是在比哪一個社會有最豐沃的土壤,有最自由的空氣和獨立的精神。一個社會一旦具有這些品質(zhì),產(chǎn)品自然會好。”
這個時代怎樣“被記憶”
最近5年,除“一個月去一次臺灣清華大學講課”,龍應臺主要給港大學生授課,“我有時開對社會開放的課”,聽課的三分之一是當?shù)卣賳T,三分之一是律師和建筑師等專業(yè)人士。來聽“文化政策”的港府官員和公共文化藝術機構的主事者,顯然看重龍應臺1999年夏至2003年2月受馬英九之邀擔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長的經(jīng)驗。龍應臺不太愿意多談“公務員經(jīng)歷”,不過她表示:“當只是純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時候,我可以看到一個鐘表,看到兩個時針是怎么走的。當你有實際經(jīng)驗的時候,你就知道齒輪是怎么回事。”
回望那4年,龍應臺最敝帚自珍的是“打下了一個基礎”,“就是文化局能獨立行使職權,不是市長的化妝師,只對市民負責。它包含城市規(guī)劃、古跡保存、公共意識、城市的藝術教育和文化人才培育等。”
“政府的所有錢來自稅收,來自人民,所以要保證每一個人的文化權”,龍應臺在任上大張旗鼓地推行“庶民文化權”、“公民文化權”的概念,并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等主張:“所謂的文化,不是停留在裝飾著水晶燈的大歌劇院里上演的歌劇上,它是城市里的居民如擺路邊攤以糊口的老太婆的文化權,甚至包括坐牢的犯人都有文化權。城市的居民有權利追問官員:我有文化權,我和那些穿著華服去聽歌劇的人的文化權的差距在哪兒?”
“決策者一旦有了人文涵養(yǎng),他在修路時會為一棵400年的老樹轉個彎,會保護對歷史積淀有貢獻的人的老房子,會在最新潮的建筑里融進古代的建筑元素。”龍應臺主政臺北市文化局時,會組織專家就民間文化團體申請政府資助的項目進行科學評估,“我要看你的土壤好不好”,“我作為政府,會設法給你一個‘釣竿而不是直接給‘魚,但好多民間申請者只要錢,想直接得到‘魚。”糟糕的是,民選的政府官員為了拉攏選票,很可能迫于選民壓力而把政府資助劃撥給投自己票的選民和團體。
南京作家范泓寫作《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時,觸動他的就有一個細節(jié):2002年5月23日,龍應臺偕“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錢永祥與資深報人南方朔等會勘年久失修的雷震故居,“那天,在蒙蒙細雨之中,龍應臺手執(zhí)一本1956年10月適逢蔣介石七十壽辰出版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其中有雷震先生所寫一篇題為《壽總統(tǒng)蔣公》的社論……龍應臺女士動情地說:‘這篇社論正是雷震十年牢獄之災的關鍵點。”時隔7年,龍應臺回憶:“我在保存雷震、梁實秋等臺灣‘外省人的故居時,還會考慮是否保存臺灣本土文化名人的故居”,“決策者從下到上界定什么叫文化,什么值得保存,什么要拆掉,才是多元社會所需要的。如果民間聲音出不來或者得不到落實,這個多元社會就聽不到足夠多的人的聲音、意見。”
“當我想到北平的時候,我馬上想到梁實秋”,龍應臺認同“文化中國”的概念,她追問:“當代中國有這樣的人嗎”,“我們這個時代又會被人家怎么樣地記住?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建國60周年,這是一個該思考的問題。”
龍應臺現(xiàn)在最關注青年問題。
“兩顆子彈的事情(指2005年3月19日的‘陳水扁槍擊案,筆者注)發(fā)生之后,我們這些朋友們覺得,恐怕應該放棄任何對于政治人物的期待了,還是要回到原點,讓咱們直接在民間社會里面,尤其是面對年輕人做一點基本的事情。”
龍應臺注定了被誤讀和被期待。《孩子你慢慢來》本來與《野火集》是同期的作品,但陷入二元對立偏執(zhí)的讀者非要把《孩子你慢慢來》、《親愛的安德烈》和《目送》這個貌似“軟”的系列和“硬”的《野火集》生生對立起來。龍應臺哭笑不得,“白天罵政府”和“晚上回家給孩子喂奶”絲毫不矛盾。
有“刁鉆”的讀者提問,假設龍應臺那溫馴的次子菲利普是“同性戀”時怎么辦,龍應臺坦然作答:“跟他對我說‘媽,我是個左撇子一樣,沒有任何差別”,“比他跟我說‘媽,我吸毒這種問題好多了”,“我會跟他一起去同性戀的酒吧”。
在逗留北京的三天里,龍應臺竭力敞開自己,一點一滴地去感受胡同、平房和楊樹等構成的“心靈里面的唐詩宋詞的中國”;讀者見面會上,為了多聽聽字正腔圓的北京話,她請求提問的讀者盡量少寫紙條而多用口頭提問。面對海峽這邊的青年崇拜者,龍應臺的最大期待是:“挑戰(zhàn)自己,你們心中原來有的所有價值都是可以被挑戰(zhàn)的,那才是真正的年輕的中國人、下一代中國人最有志氣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