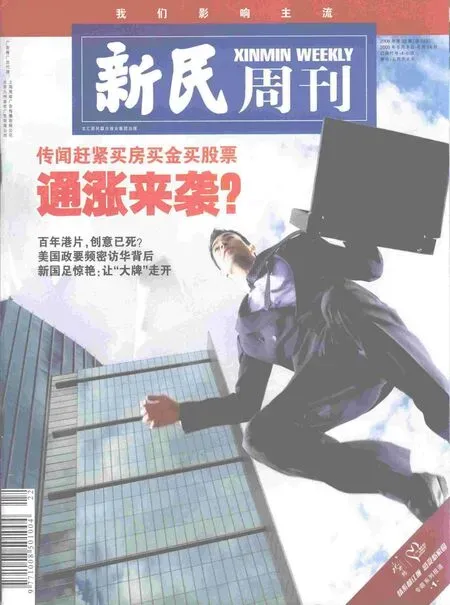物業稅:修正被扭曲的體制
馬紅漫

盡管價格是市場經濟一切問題的核心,但是有時候如果過于看重價格因素,卻有可能讓問題的本質被忽視。在房地產市場上,這一現象就顯得尤為突出。
近期,曾一度沉寂的物業稅再次成為焦點話題。
正是基于對房地產市場觀察的一般慣例,業界在物業稅再度被提及之時,首先想到的是房價將會受到什么影響。對此,普遍的觀點認為,開征物業稅有助于打擊投機性買家。從作用機理上講,物業稅是對房產保有階段征收的稅種,納稅金額隨著房產價值的漲跌而增加或減少。由此,物業稅增加了房產持有者的成本,把擁有房產的風險由一次性買入轉變為長期持有過程,這對囤積樓盤并進行投機炒作者而言是不小的打擊。征收物業稅后,房地產炒作者的投機收益將大幅縮水,部分投機者將會隨之離場,從而能夠擠壓市場泡沫的形成,最終倒逼房價回歸到理性的區域之中。而且依據國際慣例,物業稅當屬于地方稅種,其開征有利于地方政府擺脫對“賣地生財”的依賴,徹底根治地價高企的頑疾,割裂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的利益鏈條,進而能夠更加有效地遏制房價虛高的勢頭。
顯然,這樣的分析邏輯切中了當下畸高房價的要害,但物業稅的實質絕非僅僅是為了要打壓房價,而是圈定私人的財產法定地位,以及據此而需負擔的社會道義責任。
一個被征收了物業稅的房產,表明其擁有者獲得了權利與義務對等的法律地位。在權利上講,私人對于物業的法定權利經由“合法納稅”途徑被正式認可,由此可以享受排他性的支配權利,得到了法律認可與保護;而從義務角度看,私人擁有資產的多寡與納稅的高低直接掛鉤,并且在每個年度依照市價而調整,能夠體現占用社會資源的納稅公平性。
顯然,較之于單純基于房價高低變化的分析,物業稅的擬議以及征收,其實際的社會法律意義要大了許多。就以國內備受爭議的動拆遷問題為例,實施動拆遷的權利,與動拆遷的財務補償標準是拆遷引發爭議的核心。而物業稅的推出則能夠讓這兩個問題迎刃而解,它首先標明了納稅人擁有房產的權威法律地位,由此讓強拆強遷于法無據。此外,歷年來房產所繳納的物業稅高低,直接成為判斷拆遷補償標準的重要依據。換言之,物業升值越多,累積繳納稅款越高,理應獲得的拆遷補償也就隨之而增加,反之亦然。由此,個人的財產權因此在法律上獲得物權與財權雙方面的認可,這才是物業稅所帶來的真正社會影響,至于打擊房產交易投機以及對房價的影響倒在其次了。
在房地產市場上,類似的誤區還有很多,比如備受爭議的預售房制度也是一個典型例證。內地的預售房制度源自香港,但是這一體制卻與歐美絕大多數國家的現房銷售制度存在明顯不同。因此,取消預售房制度的呼聲也很高,而業界按照慣例不斷分析著該制度存廢對于房價高低的影響。誠然,預售房制度等于讓購房者為開發商提供了財務支持,一旦取消,必然會經由開發商資金壓力變化而引發房價的漲跌。但與物業稅一樣,業界的觀察也過于集中于房價,反而忽視了相關問題的實質。
預售房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房價,而在于資金財產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在房屋還遠沒有成形、產權證等法律憑證尚未落定之時,購房者首付款與銀行的貸款就被開發商納入囊中并投入使用。顯然,這并不符合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基本規則。一旦開發商資金鏈條出現斷裂,個人財產與銀行信貸資金都會出現巨大風險。正因此,對于預售房制度的修正,同樣是屬于制度性的正本清源之舉,這一點與房價的高低漲跌沒有太多的相關之處。只是近年來的房價飆漲,讓人們過于關注于此,反而忽視了房地產市場體制亂象的本源所在。
權利與義務的失衡問題才是房地產市場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恰因此,當下難得的市場平穩期,提供給調控部門一個極為珍貴的時間窗口,那就是去及時修正被扭曲的房地產市場體制,打開市場良性運行的體制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