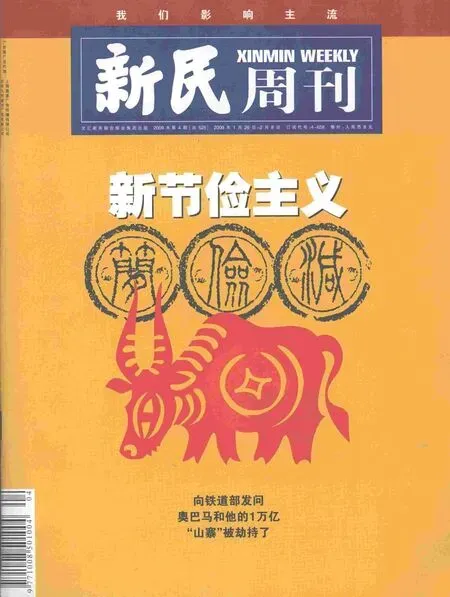中國內需結構轉型的三張通行證
童大煥
世界金融危機一來,中國國內實體經濟深受其害,人們這才發現,我們的現代化基礎是如此薄弱。我們寄希望于擴大農民的消費來刺激內需,并實現經濟轉型,但失業潮、農產品價格降低等一系列因素使農民自身難保。筆者十分贊成華生、羅小朋、張學軍、邊勇壯四位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在2008年12月27日《新京報》上撰文所持的觀點:農民工變市民是下一個30年發展的引擎。
縱觀全球,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村人口會超過10%。這是一個鐵律,中國內地也不可能既把農民摁在土地上又收獲現代化的甘甜果實。官方數字說,30年來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4.9%,城鎮人口已達5.9億。然而,很多學者卻認為,中國真實的城市化率實際僅有27%左右。如果大量農民無法順利轉化為市民,中國的現代化就是沙上建塔,所謂培育內需、實現經濟結構轉型等等也就只能成為空想和空話。
在此,我們有必要就三農問題多問幾個為什么,以便于理清下一步改革的思路和著眼點。
為什么內地一些城鄉接合部或東部地區的村主任選舉競爭總是相當激烈,甚至到了幾乎年年都有地方鬧出人命的地步,這可能算是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職位了。而那些偏遠地區的村干部照例是“請我都不做”,“空殼村”也并非少數。為什么同樣的基層自治組織,城市的業主委員會很少有人問津?為什么上訪、投訴、舉報事件中,以征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和干群矛盾越來越多?其中相當多的內因,無非是農民殘缺的土地和農房權利;其中相當多的秘密,出在地方掌權者或“集體”代表人擁有了本不該擁有的土地與農房支配權力。眾所周知,馬克思曾生動地描述過資本家對利潤的追逐。實際上,對暴利的追逐,從來不只是商人的專利。在我國一些地方,土地農轉非的過程中,其中的暴利又豈止是3倍?筆者2003年曾根據某地征地和出讓地價格進行一番比較,一出一進的最低差價是40倍,最高285倍!如今這么多年過去,相關方面的“利潤”更高了,因為征地價格基本未變,而出讓地早已經“地王”頻現。與此直接相關的另一方面,是農民作為個體卻往往不能自主自由地將自己的土地和農房轉化為進城創業的資本。
為什么農民工進城帶來了如此之多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葉敬忠及其26人組成的課題組,通過兩年時間的研究估算,留守兒童總數約2300萬人,留守老人總數約1800萬人,留守婦女總數約4700萬人(2008年12月20日《新京報》)。這個數字有可能被嚴重低估。根據農業部部長孫政才的公開說法,2007年農民工達到2.26億人。去年2月27日,全國婦聯發布《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說:“目前,我國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約1.3億人。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抽樣數據推斷,全國農村留守兒童(17周歲以下)約5800萬人,平均每四個農村兒童中就有一個多留守兒童。”這是根據1.3億農民工的估算數字,如果根據2.26億農民工來估算,數字還要更龐大。留守婦女、留守老人亦然。
為什么他們都被迫選擇了留守?對于留守兒童來說,戶籍壁壘、不能在當地參加高考,當然是主因之一。但是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呢?難道他們自甘自愿過一種長期沒有親情愛情的生活,只把自己當成掙活口的牲口和苦力?
不是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當下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條件極其惡劣,居住權利嚴重匱乏!工棚和集體宿舍就是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家!這種情況下,農民工的家庭生活怎么可能?更令人駭異的是,還有不少企業為了生產效率的需要,居然禁止員工外宿,農民工自己租房也不行!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許崇德憲法學發展基金評選出了2008年十大憲法事例,廣東法院判決企業禁止員工外宿違背憲法精神名列第三。你想不到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企業規定。
我認為,政府為農民工提供適宜家庭生活的廉租房應該從速提上議事日程了!由企業提供租房補貼,并且由企業開通工地到集中居住地的班車,應該成為改善農民工生存狀況的人權指標。如果這點做不到,應該允許貧民窟的存在。有家、有精神生活和社區生活的貧民窟,即使簡陋,是不是比工棚和集體宿舍的生活更為人道?
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城市化都會節約土地,唯獨我國卻完全相反?因為土地和農房制度僵化,因為農民工及其家庭的進城權利得不到保障,在城市沒有歸宿感,因此一有錢就回老家蓋房!城市越發展、農村外出打工者越多,回鄉蓋房、蓋大房子的也越多,農村房屋的空置率也越來越高。這是土地和住房的雙重浪費。
以此看來,土地和農房確權、農民工的城市住房權利、戶籍改革,乃是農民變市民、實現中國經濟向內需型結構轉型和中國現代化的三張必不可少的通行證。(作者系北京資深評論員,知名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