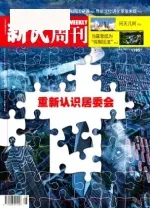另一個世界的圖像報告
劉國鵬
攝影家采取黑白攝影的風格,一方面旨在抵御普遍流行的彩色攝影的誘惑,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文獻式攝影后面的嚴肅意圖。
常識和眼睛告訴我們,攝影作品同被攝對象呈現一一對應的關系,這顯然不是個錯誤,卻并非事物的全部。攝影是對某一被攝體的反映,卻毫不被動;它是對被攝體的呈現,卻非遵循全然復制的方式。攝影毋寧說是在攝影師的精密控制下從某一特定角度入手對被攝對象的切割,攝影作品只可能是攝影師希望你所看到的被攝體的某一狀態、情緒或顏色變化。它注定是一個特定的觀察世界的方法,一種攝影家個人的哲學、觀念、看法或者意見。

《黑白布朗山》系列,是攝影家王藝忠歷時三年(1989-1991)在云南西雙版納布朗山所拍攝的人文攝影作品。居住在布朗山的數個少數民族和與世隔絕的環境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幅原始、蠻荒、貧窮和帶有某種異國情調的畫面。這些作品是對常人所難以涉足的一片神秘區域的重新界定。它們是經過揀選的生存狀態清單,是詳盡考察后的一份田野記錄,和一個個被嚴格控制、包裝的對象。
與滿足都市人的旅游和獵奇癖而言,這些照片在攝影的技術性控制,對被攝對象及其生存狀態的切入角度和特殊興趣方面,均遠遠超越了簡單的獵奇心理和庸俗的審美旨趣,從而反映出攝影家個人深刻的觀察,甚至某種意義上的人類學和社會學態度。因為,人類學考察的視野,諸如:“人類群體當中為何存在著變異和差別?”“原始時期的人類演化如何影響其社會組織和文化?”以及社會學的考察領域諸如人類社會的各種生活實態,和社會變遷的成因等也在此得到了某種精心釋放。
在王藝忠的作品中,人們看得到衣衫襤褸的幼童,袒胸露乳的婦女,滿布滄桑的老者面孔,承受生存重負的勞動場景,但是,這些統統被藝術家謹慎地罩上了一層神秘而又神圣的光環,從而巧妙地避免了對貧窮、苦難的廉價展示,和對原始、赤裸的人體的色情闡釋,在每一雙眼睛,每一座茅屋,每一隊畜群的背后,人們看到作品慷慨而又輕柔地推開了一道隱秘的大門,供我們的靈魂和情感出入。攝影家鏡頭所對準的那些個體和群體,被再加工為界乎攝影人像與版畫肖像之間的一種雙重風格的融合,他們貧窮而自足的面孔、身體和姿態從而成為一些奇特故事的線索和源頭。在此意義上,攝影是對某個特定時空交錯點上的被攝體的局限性呈現,但卻為我們提供了想象整幅時空坐標的畫筆和出發點,便于我們恣意涂抹和長途跋涉。王藝忠的作品,也在此超越了對生活在布朗山深處的特定族群的簡單同情和獵奇,從而提供給觀者一系列意味深長的態度和深層次的思考。“另一個世界”之謂,并非單純局限于攝影家所拍攝的地點的難以抵達與拍攝場景的罕見,還在于它是純然相異的一個生活世界,一個與我們共同享有生活的熱望,具備同樣的人性尊嚴,卻反差如此強烈的某一生活群體的陌生畫面。通過攝影家,這些獨特的群體忠實而本真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他們是無聲的。在此意義上,他們不僅僅是被動的被攝體,而是委托攝影家向外部或相異世界帶去其豐富而獨特的生活消息,這一無意識的委托也將攝影家轉化為“另一個世界”的獨特信使和翻譯家,為我們帶來斷續、模糊而又激動人心的信息和故事。
攝影家采取黑白攝影的風格,一方面旨在抵御普遍流行的彩色攝影的誘惑,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文獻式攝影后面的嚴肅意圖。此外,黑白還有一種獨有的超越時間流逝的特質,它同時是色彩的豐盈和極簡,是變化中的無變化,是無變化中的變化,從而抗拒任何時代和風格的變遷而努力接近永恒。
王藝忠的攝影展正在可當代藝術中心等著攝影愛好者前去品賞,并且我相信,他的畫面一定會被觀眾長久地烙進記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