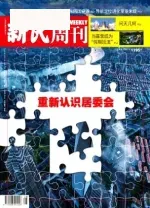追蹤中國公益律師
季天琴
在如今的中國,就有著這樣一群特殊的律師,他們通過發起具有超越個案意義的公益訴訟和公益上書等法律行動,以挑戰不合理的社會現象。

有人說,在中國公共利益受損得不到保護是因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路見不平的人多,拔刀相助的人少。反駁者卻說,我們并不缺高尚的人,但徒有拔刀之勇能解決什么問題?
在歐美等國,公益訴訟的主體是公益律師和公益法團體,公益訴訟至今仍保留了為弱勢人而戰的倫理規范。美國律師丹諾被譽為法律界的“老獅子”——他在民權運動的前夜為形形色色的被告做了無數次成功的辯護。作為律師,他對正義的熱愛、對弱勢群體的無比同情,都大大升華了律師的職業屬性,使律師不僅僅是一種謀生手段,而且成為改造社會、關注人類的崇高事業。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律師不再只激動于丹諾的高昂理想,而是開始以專業求職業。在如今的中國,就有著這樣一群特殊的律師,他們通過發起具有超越個案意義的公益訴訟和公益上書等法律行動,以挑戰不合理的法律、法規以及其他規范性法律。
這些就是公益律師。
律師制度的緩慢演進
“律師”概念開始植根于中國,是在清朝末年。1910年,清廷頒布《法院編制法》,開始從法律上確認律師活動的合法性。到30年代末期,全國律師已達3000人,并出現了一批著名律師,如施洋、史良、章士釗、蔣豪士、吳凱聲等,他們辯護過許多大案——陳獨秀案、廖承志案、“七君子”案等。
1954年,隨著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誕生,律師制度也開始建立。事隔幾年,很多律師被打成右派,律師制度隨之消亡。1979年,司法部恢復律師制度,各地陸續出現20多家“法律顧問處”,全國有200多人進入這些機構,這些人或在50年代曾經做過律師,或在“文革”期間做過政治教員。他們跟警察、法官一樣,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工資由政府發放。
1988年3月,中國律師制度作出重大改革,由純粹官辦改為“合作制”,改變了10年來律師事務所為官方壟斷的歷史。繼合作制之后,合伙制成為大陸律師所組織形式的又一突破。律師也從專政工具逐漸變成制約權力、維護正義的重要因素。
公益律師的群像崛起
法學家江平教授說:“律師興,法治興;法治興,國家興。”
在利益分化的年代,各種強勢組織漠視公民權利的現象層出不窮,法律程序成為維護公共利益和推動社會變革的強有力的推手。
1996年1月,福建省龍巖市的邱建東以公用電話亭未執行夜間長話收費半價規定而起訴郵電局,要求加倍索賠,索賠金額為1.2元。這場“一塊二”官司,拉開了中國公益訴訟的序幕。
2003年孫志剛事件,以許志永、滕彪、俞江為首的北大三博士和以賀衛方、盛洪等為首的五教授提起的民間立法上書開啟了中國違憲審查的先河,并促進了《收容遣送條例》的廢止,從而彰顯了法律人的公共關懷和正義訴求。
這一年,以東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師事務所的建立為標志,公益訴訟走到了分界點,出現了一批相對穩定的群體來運作公益訴訟案件。同年底,許志永等人在北京海淀區工商局注冊了一個“陽光憲道”的機構。“陽光憲道”被注銷后,重新注冊后更名“公盟”。
幫助黑磚窯受害人提起行政訴訟、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組建律師援助團并提起公益訴訟、為上訪的弱勢者提供援助……“公盟”這些注重公共利益層面的考量,即使失敗,也逐漸成為撬動民主進步的“杠桿”。
光環背后的現實
還有些響亮的名字——郭建梅,中國第一家女性法律援助公益性民間組織創始人;喬占祥,為春運票價上浮狀告鐵道部;周立太,為傷殘民工爭取權益……
除此,無論公益律師們頭頂怎樣的道德光環,都無法改變那些冷冰冰的社會現實——在中國為公共利益打官司的人,沒有幾個是凱旋的。他們除了耗費自己的精力和錢財,還得接受被駁回訴訟或者敗訴的宿命。
2009年7月14日,許志永主持下的“公盟”收到北京兩稅的處罰事項通知書,除要追繳稅款外,并擬按最高“刑”處以五倍罰款,共計142萬多元——這場風波根源上來自于“公盟”不尷不尬的“身份”。法律性質上,“北京公盟咨詢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民營企業;但實質上,它從事的一直都是公益活動。
對于公益律師而言,公益訴訟本身也充滿悖論——一方面,他們要堅持法治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他們卻不得不經常訴諸媒體這種法律之外的手段尋求合理的結果,因為結果總是證明,可以指望的總是媒體的報道而不是法院的審判。因此,公益律師們總是經常面臨著過分政治化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