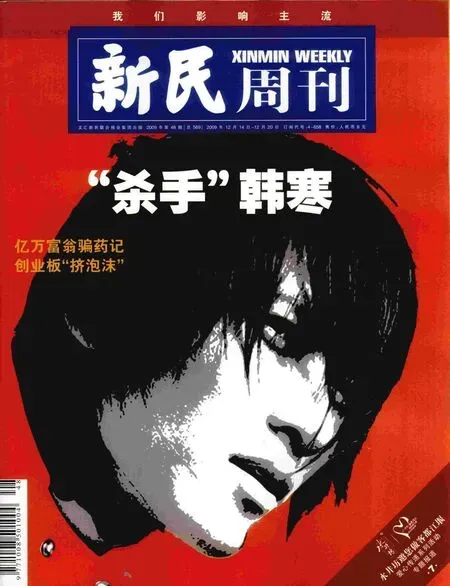拆遷條例怎么改?
葉 檀
我們應該學會以市場化、以法律的方式解決社會利益分配,以滿足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用傳統的官民邏輯來考慮現代社會的利益分配。
由于城市化進程中拆遷沖突集中爆發,拆遷條例是否該廢除,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12月7日,北京大學法學院5位教師學者通過特快專遞的形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建議立法機關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撤銷這一條例或由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向國務院提出書面審查意見,建議國務院對《條例》進行修改。5位學者的理由是,2001年11月1日開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拆遷條例》”),與《憲法》《物權法》《房地產管理法》中保護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動產的原則和具體規定存在抵觸,導致城市發展與私有財產權保護兩者間關系的扭曲。
如果我們把拆遷條例看作城市化進程中個人產權與公共產品之間的沖突,那么,這樣的沖突將長期存在。對于長期存在的利益糾紛必須有法律加以約束,不管這部法律稱作什么。
現在關鍵的問題不是《拆遷條例》該不該廢除,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
拆遷的公益性有必要接受民眾的質詢。按照《物權法》第42條,對政府征收公民個人的房屋和不動產采取了例外允許、嚴格限制的態度。該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問題在于許多動拆遷到底是為了公共利益,還是為了官員利益,還是為了權錢交易,之間的界限并不清楚。在界限不清的情況下,以底線衡量對方的做法是常規。因此,民眾在多數時候把拆遷視作地方政府渴求土地收入,甚至中飽私囊的產物。因此,將拆遷過程,拆遷后本地的規劃公諸于本市市民,符合多數人贊同原則,則可視為公共利益。
并不是民眾大多數時候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舍大家為小家——這樣做同樣符合經濟理性人規律,沒有違反法律——而是在大多數時候,拆遷成為利益最為豐厚的圈地戰。通過拆遷擴大或者建設城市,政府以極小的補償獲得土地收益與房地產稅費,而開發商獲得房價上漲溢價。
拆遷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補償安置標準,目前的補償標準毫無市場氣息,剝奪了拆遷戶獲得土地溢價的權利;而一些通過漫天要價僥幸獲得土地溢價的人,沒有成為建立案例法的有益鋪墊,反而成為拆遷市場毫無規范的活樣本。
地方政府成為主要的利益主體,是拆遷過程中的致命傷。在拆遷過程中,地方政府既是行政執法者,又是既得利益者,更是房地產市場的中介商,集各種身份于一體,此時經濟人的身份壓倒了政府的守夜人身份。
一些地方政府的補償標準八仙過海,標準彈性大到可笑的地步。聽著挺美,挺有章法,如果一些房地產評估機構完全是地方政府的橡皮泥,則所謂的市場化補償將成為無本之木。
標準再多,地方制訂的補償標準往往就低不就高,如“統拆統建的,按住宅房屋統拆統建標準支付拆遷補償款,但其原房補償款部分按1.2倍計算,不再另行安置和支付停業損失等其他補償”。正如被拆遷者所說,你牽走了一頭牛還給我一只雞,我不要,我要我的那頭牛。是牛還是雞,必須由中立的第三方機構來說了算,而不是由深陷利益中的拆遷者與被拆遷者說了算。
解決的辦法只有兩種,一是按照市場化的評估價格對被拆遷者進行貨幣補償,二是按照市場化的價格對被拆遷者進行實物補償。此時政府退出利益鏈至關重要,如此才能做到評估、補償的公正與公平。如果當地居民普遍反對拆遷,那么暫不拆遷天也塌不下來。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可能終止,也就是說大規模的動拆遷還將延續一段時間。我們應該學會以市場化、以法律的方式解決社會利益分配,以滿足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用傳統的官民邏輯來考慮現代社會的利益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