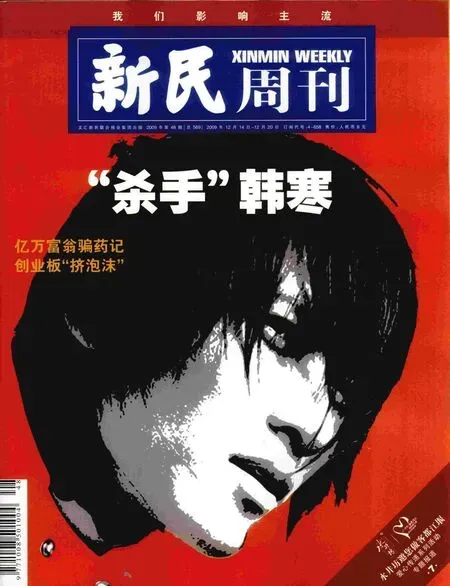作家是怎樣煉成的
嚴 鋒
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還是對的。一個對文學沒有愛,沒有天賦,沒有生活的人,上100堂哈佛的文學寫作課也沒有用。
最近,復旦大學中文系成為國內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面向全國招收文學方向的創意寫作藝術碩士(MFA)的單位。這在中國的中文系史上,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情,因為這個專業以培養作家為主要方向,與傳統中文系的理念完全不一樣。
就我個人而言,看到這一天的來臨,實在是悲喜交集,不能自已。我曾經是個狂熱的文學青年,狂熱到什么程度?1981年,我讀高中二年級,有一次老師在作文課上布置我們寫一篇小說,第二天交上去。這天我回到家里,一個晚上沒有睡覺,一口氣寫了三篇小說。
第一篇寫一個科大少年班的學生衣錦還鄉回母校,卻倍感失落寂寞,因為昔日的同窗都與他有了距離。第二篇寫“我”在菜市場與一個葛朗臺式的菜販子周旋,后來葛朗臺不慎失誤,多找給我錢,“我”回家發現后飽受道德的煎熬,最后良心發現去還錢,而葛朗臺已在失錢的痛苦中含恨死去。第三篇寫“文革”中大人失去自由,父親讓8歲的“我”去寄一封信。到了郵局門口,“我”發現信不見了,回家后謊稱信不慎掉進廁所里。造反派來抄家,在我書包里找到了那封信。原來此信是父親向黨中央揭發造反派的密件。父親因此獲罪身亡,留下“我”生活在無盡的悔恨之中。
寫到第三篇的時候,越寫越順手,已經欲罷不能,一顆心好似要破壁飛去。巴老說過:創作是一種燃燒。我非常理解他說的意思。他指的就是我那天晚上的那種狀態。要高考了,文理分班,我毫不猶豫地選擇文科班,懷著成為一位作家的夢想,來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
我清楚地記得1982年9月的那個下午,中文系新生開學典禮,系主任給我們講話。他說,你們當中肯定有很多人是因為想當作家才考中文系的吧,這是對中文系的一種誤認,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回到宿舍,班長翟寶海,和我一樣熱切的文學青年,一頭倒在床上嗚嗚大哭。我沒有哭,但也就把自己的夢想悄悄埋葬了。
慢慢也就知道類似“作家不是教出來的”、“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說法是怎么來的了。源頭就在魯迅。他認為,“創作并沒有什么秘訣,能夠交頭接耳,一句話就傳授給別一個的。”(《不應該那么寫》)多次表示“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答北斗雜志社問》)但魯迅的話確乎不能全信,因為他還有一句名言“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這些話全部加起來,中文系就可以關門了。
2004年,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想選一些課聽。拿到課程表,一眼看到有七門Creative Writing(文學寫作)的課程,突然就很想去聽,結果每一門課都人數爆滿,無法選上。其中又分初級、中級和高級三種級別,高級文學寫作課需要通過考試才能進去。
課沒上成,卻從此領略了哈佛學生對文學寫作的熱忱。其實美國的許多大學都開設文學寫作課,甚至有專門的文學寫作系和寫作學校,全美有350多所大學開設文學寫作的MFA項目。看來,他們是認為作家可以教出來的。旅美中國作家中最有名的兩位,哈金是波士頓大學文學寫作專業的畢業生;嚴歌苓是哥倫比亞學院文學寫作系的畢業生,拿到過正式的MFA文憑。
2008年,復旦中文系請嚴歌苓的老師、哥倫比亞學院文學寫作系的系主任舒爾茨教授夫婦前來給研究生授課。王安憶老師和我全程旁聽,終于領略了一回美式文學寫作課的滋味。第一課,舒爾茨教學生怎樣“聽”。他讓學生描述一個剛才聽到的聲音,不斷追問下去:那個聲音是什么顏色,什么形狀,什么質感,給人什么聯想?
這是文學嗎?聽著聽著,我突然有點明白了。舒爾茨教的是文學最物質化、最技術性的層面,就像我以前上吉他課時,老師讓我們每天做的手指體操,俗話說的“爬格子”。也像鋼琴課老師讓我們彈的“哈農”,極其枯燥單調乏味的手指練習。這些本身毫無藝術性可言的練習曲,卻是通向藝術自由的必經之路。
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還是對的。一個對文學沒有愛,沒有天賦,沒有生活的人,上100堂哈佛的文學寫作課也沒有用。但是,像我這樣的曾經的文學青年,如果有魯迅或王安憶當面批改作品,有舒爾茨每天都在一旁拎著耳朵不斷追問“你聽到了什么”,最起碼我們的文學夢可以做得更長久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