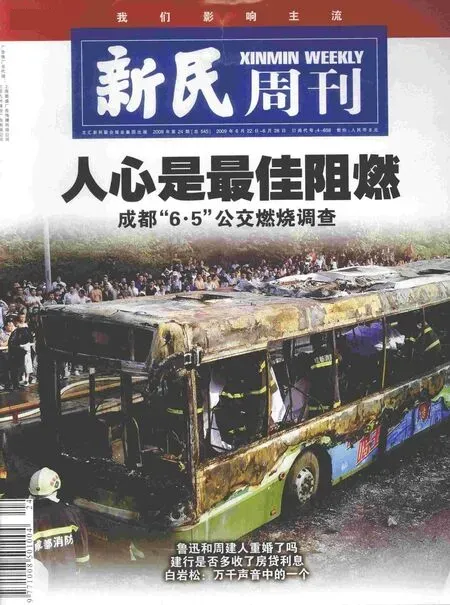白巖松:萬千聲音中的一個
王 倩

整個社會要有一種包容。不能因為有不對的聲音,就連對的聲音都不能說了。不對的聲音,也是眾多聲音中的一個。
白巖松被一群娛樂記者圍住了,第二天就是《新聞聯播》主持人羅京的出殯日,年輕的采訪者們以各種方式,或直接或迂回地希望他對此多說點“花絮”什么的。在表達了傷痛之情后,白巖松嚴詞拒絕了此類問題。
“他真嚴肅”,不太習慣的記者們私下嘀咕著。這就是白巖松的公眾形象,連同他的眼鏡和眉毛,一起成為了這位中央電視臺著名新聞評論員的標志。
私下里,坐在對面的白巖松沒戴眼鏡,穿著簡單的Kappa運動T恤,電視機里在“無聲”地播放著斗牛大賽。這也是他的習慣之一,走到哪兒都要看看體育頻道。前一天他剛剛在“2009華語主持高峰論壇”的演講上提出了12個字:“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而我好奇的是,和電視新聞為伍的這16年里,他真的一直如屏幕上那般自信嗎?嚴肅之下,是否有過累了的時候呢?
中國怎么說
《新民周刊》:和楊瀾這樣頻繁和國外嘉賓們對話的主持人不同,像你這樣的央視新聞主持人和評論員,也需要去考慮在全球電視業界的影響力嗎?
白巖松:這是中國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誰也無法回避的問題,所有的媒體人都關心的問題。要問中央電視臺什么時候成為國際大臺,十幾年前我的答案是等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現在中國正走在通往世界大國的路上,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別人都會更加關注你的聲音。通過媒體的變化,來看中國國內的變化;通過媒體的聲音,來看大事發生時中國怎么說,所以你逃避不掉的,因為中國到了這個分量。
《新民周刊》:什么時候慢慢感覺到了這個分量?
白巖松:十幾年前,大家只是提出“中央電視臺什么時候能成為國際大臺”這樣的問題,但僅僅是提出問題,沒有人會真的關心。但從這兩年開始,你會發現你回避得掉嗎?西藏事件逼著你思考,中國該如何去和世界溝通和交流,你怎么發出自己的聲音;奧運會了,全球4萬個注冊和非注冊記者像顯微鏡一樣地在報道中國;汶川大地震時,大家都在關心你在媒體報道上的開放和透明。中國GDP已經是世界第三,隔幾年就會變成世界第二,別人當然要關注這么大分量的國家。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媒體人會提前預知到這個。
《新民周刊》: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發生時,你基于怎樣的原則來發表你的評價呢?
白巖松:基于新聞準則。總有人問你站在哪兒,好像要站隊似的,你站在國家、政府、國內民眾和國外的哪一邊呢?不,我站在新聞立場。就像日常生活里面對很多事情,別人也會問我,你站在政府立場還是百姓立場呢?我站在事情的對錯和方向立場上。有些事情,你站在政府立場上不一定對,站在公眾立場上也不一定對,很多時候站在一種情緒的立場上時更需要理性,而且可能會有很多公眾罵你。
《新民周刊》:新聞要求客觀。但楊瀾也說了,現實情況可能是附庸一種情緒,要比探究事實容易得多,也更容易得到短期銷售量和收視率上的回報。
白巖松:事實擺在那兒,站在不同角度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這的確是可怕的地方。不過有一點不用擔心,新聞的客觀不是哪一家新聞媒體的客觀造成的,而是由開放和透明導致的所有人都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去關注它,最后呈現出的結果才是最接近客觀和事實本身的。
總會有不同的媒體,站在不同的角度和準則,選擇了事實的不同截面。怕的就是不公開和不透明,有的新聞事實只能允許少數的媒體擁有報道的權利,我倒擔心它的不客觀。即使它做得對,我同樣擔心,因為這種壟斷中蘊藏著一種不客觀。所有的媒體都擁有報道的權利,那才會接近客觀。
捍衛常識
《新民周刊》:我們的社會正在巨變,你作為新聞人的心態是怎樣的?
白巖松:挑戰更大。十幾年前我們在《東方時空》開始電視改革,更多的是回到新聞應該的立場上。一點都不該表揚,沒多做什么,只是新聞就該那么做,關注人,說人話,像個人。通過十幾年時間,我們做到了,而且新聞監督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現在社會變革到了新的階段,中國將要拉開的不是某個局部的變革,而是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化,和諧社會是一個理念,另外還包括民主進程、社會多元化的聲音和百姓的權利等等,中國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么徹底的變革。作為新聞人,不能再簡單地說新聞該怎么做,所以我提出了“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這是對我自己說的。如果別人愿意,也可以聽聽。
《新民周刊》:捍衛常識,你說要強調1+1=2,因為當1+1=3會獲得利益的時候,就會等于3了。什么時候意識到1+1可能不等于2了呢?
白巖松:我每天都能遇到。身邊有無數的話語,這些話語都以真理的姿態出現,可能相當部分都是偽真理,但你都得聽啊,但聽完后你不能被偽常識所迷惑。
誰都知道1+1=2,你以為“文革”時人們不知道有些事是錯的?知道,但明哲保身,所以大家走到了1+1=3的道路上。
《新民周刊》:如何從利益中擺脫出來?
白巖松:我不知道,但起碼我不會那么做。看你如何去看待利益?先不要說責任這樣的大詞,就說《道德經》里的一句話“無私為大私”,哪怕你想要得到更多,先要有一顆無私的心。
真正可怕的是小利益,但為了小利益,只要扭曲過自己一次,你可能就欲罷不能。你也許會得到一些表面的利益,肯定會失去長遠的利益,這是稍微清醒一點的人都能看到的,難嗎?捍衛常識不難,只要擁有勇氣和良心,一般人都能做到。
《新民周刊》:但人非圣賢,不可能永遠不出錯。
白巖松:出錯,和為利益而故意出錯,是兩回事。人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我天天做新聞直播,我的話語量是中國主持人中最大的,我也可能出錯啊。但這種出錯可能是因為自己的知識積累不夠,或者你當時只看到了一二三四的事實,而五和六要到后天才能看到的。當然這種出錯,在我的職業生涯里并不多。我時刻做好了出錯的準備,在河邊濕鞋是正常的,否則就不要去河邊了,對我來說這不是問題。
《新民周刊》:當年和你一起奮斗的那群臺前幕后的新聞人,如今似乎各奔東西,為什么你還在那兒?
白巖松:為什么我堅持下來?起碼到現在為止,這是我認為的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非常好使的方法,或者說崗位。我也不知道五年后會怎樣,起碼我現在還喜歡它,在這場接力賽中我正拿著這一棒在奔跑。跑好它。
《新民周刊》:你在2000年前后主持了大量的大型節目直播,然后進入新聞頻道擔任新聞評論員。是到了這個火候了嗎?
白巖松:十幾年前《東方時空》創辦時,創辦人孫玉勝(現中央電視臺副臺長)非常明確地說過,我們的主持人將來的發展方向是記者—好記者—主持人—好主持人—新聞評論員。當時他在臺上說,我在臺下聽得非常清楚。也許我早了點,40歲剛過就當上了新聞觀察員。但是從電視改革的角度來說,晚了點。
不怕越位
《新民周刊》:在你的背后,有多少的幕后力量呢?
白巖松:《新聞1+1》是個非常小的團隊,十多個人應付每天半小時的新聞直播。小型化是將來的必然,一個大耗能的電視操作模式結束了。
《新民周刊》:別人給你撰稿嗎?
白巖松:在過去十幾年,就念過一兩次別人寫的稿子吧。我的稿子都是我自己寫的,這不是大話,我到現在還不會用電腦。《新聞1+1》是直播,我從來不會準備太多的稿子。《新聞周刊》是非常嚴謹的周播評論,我會在家里先寫下來,通過電話錄出聲音,由速記打印成文字,晚上再錄。先錄下來,是為了讓編輯知道我要說什么,才能更好地編輯畫面,以免信息重復。
《新民周刊》:錄一期45分鐘的《新聞周刊》,你寫稿需要多長時間呢?
白巖松:兩個小時吧。但為了寫,我要看很多東西。從2003年(當時叫《中國周刊》)到現在,不是我錄的節目也就五六次。我大部分的星期五都會在北京,這本身就是無數利益的放棄。
《新民周刊》:有領導在你的直播現場嗎?
白巖松:不會。我直播時,現場只有制片人,負責技術方面的問題,沒有領導。如果不放心,就不要讓我做。放心的話,那大家彼此都明白,要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門開了,我不會讓它再關上的。難道做了十幾年的新聞主持人,達不到和領導一樣的新聞判斷能力嗎?如果連這個自信都沒有的話,就不要做了。
《新民周刊》:那你會不會為了讓這扇門永遠開著,就站得離門遠點呢?
白巖松:我這樣做了嗎?我的節目每天都在播,我是不是站在前沿的,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一個節目怕越位,和自己的后衛站在一起,這樣的節目早被淘汰了。我絕不會因為怕越位而失去前行的勇氣,我一直在說要貼著最后一名后衛站著。
《新民周刊》:趙忠祥說,新聞評論最重要的是預報,說準明天會發生什么。你怎么看這個說法,預報重要嗎?
白巖松:不重要,思想也不重要。在一個紛繁復雜的時代做新聞評論員,最需要的是勇氣、敏感和敏銳,還有預判和方向。總有很多人說,做新聞評論員需要思想,這是個誤讀。思想就那么多,我不是寫學術論文。比如周一我在節目里提出一個明確的看法,今后的高考能否改在每年6月的第一個周末。今年的高考第一天是周末,和第二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社會也付出了極大的成本。這需要思想嗎,只是需要有人說出來。
《新民周刊》:現在很多電視臺強調雙語主持人。你覺得外語能力對于主持人來說是關鍵嗎?
白巖松:有更好,沒有也不是大問題。我上次在耶魯演講時用的是中文,即使我英文再好,我有足夠的能力做英文演講,我肯定還是用中文演講。當然耶魯方面考慮得也很細,他們給我請的翻譯是美國人,他以聽眾最能理解的方式來翻譯。如果是來自中國的翻譯,對我的理解極其準確,但是翻譯后不一定。我是學俄語的,現在也在學習英語,曾經花了一年從ABC開始學起,現在應付日常對話已經沒問題,未來肯定還要繼續深化。
《新民周刊》:當時你在美國制作了《巖松看美國》,還是你一貫關注細節的風格,但我知道出發前很多同行都在期待著你能接觸到美國的大人物們。
白巖松:沒有細節,就沒有節目。意識形態中任何的偉大,都是由偉大的細節構成的。我可以選擇很多熱門選題,但到了我這樣的年齡,我不會選擇那些表面很熱鬧、一兩期收視率很高但過后就被忘了的節目。很多人問我如何看待收視率,我說,我心目中最高的收視率是中國的鄉村里能開出一輛校車,無家可歸者也可以在公共圖書館里自由穿行而不遭受歧視。
接受表揚,也接受批評
《新民周刊》:你過了為得獎開心的年齡,你也過了要收視率證明自己的年齡。十幾年前你絕對不是這樣想的吧?
白巖松:那當然,過去幾年在我身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現在我不會為收視率而去做什么,但我的節目收視率從來都不低,上兩周整個頻道的最高收視率都是我的《新聞周刊》;我不會總去說一些人們覺得好聽順耳的話,有些事情是要有勇氣挨罵的;不能再想著要有多大多大的影響力,我不過是萬千聲音中的一個;關于獎項,我拿到了中國新聞人所能拿的所有的獎,希望有一天我能退出所有的獎項。
《新民周刊》:你這份工作隨時隨地要面對批評,當然有時可能是極其夸張的誤解,你怎么反應?
白巖松:我能接受很多過度的表揚,為什么就不接受批評呢?你以為給我的表揚都正常?我1989年畢業,天然對民主會有自己的思考,你可以不同意別人說話的內容,但是要維護別人說話的權利。讓別人說吧,很正常,哪怕不對的聲音。他可能今天罵你,過段時間可能就會覺得你是對的,要有一段過程。
人該如何面對批評?我也一樣,沒有道理,我不會生氣;有道理,那我就要慢慢去改,而不是去責罵批評者。整個社會都該給批評者更寬松的余地,將來的新聞評論會越來越多,有對的也有不對的,整個社會要有一種包容。不能因為有不對的聲音,就連對的聲音都不能說了。不對的聲音,也是眾多聲音中的一個。
《新民周刊》:繼續往前走,最大的動力是?
白巖松:往前走,最大的動力就是好奇。別想那么多,把眼前和未來短期的事情做好,保持永遠的好奇。最佳的狀態應該是“我去意已絕,觀眾戀戀不舍”,千萬別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