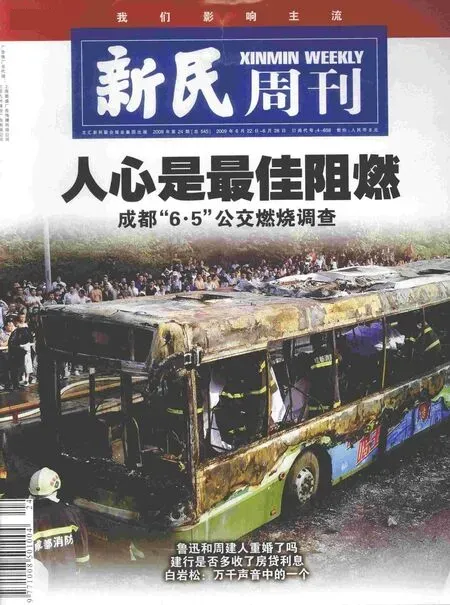向戲曲致敬的心靈雞湯
周晏珵 王 倩

影片甚至可看作一部“妙用虛實、出入古今”的先鋒藝術片,蘊含導演深深的個人創作痕跡,充分展現了現代電影人對中國京劇藝術的理解。
戲曲電影恐怕稱得上是中國老百姓最熟悉的陌生人。當年樣板戲、黃梅戲、越劇電影熱潮看似不復,今日一員猛將闖入眼球。電影《廉吏于成龍》被寄予厚望,視為中國戲曲電影探索之路上的又一塊里程碑。
戲曲電影卷土重來
戲曲電影曾在中國電影史中占據了很重要的篇章。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老板任慶泰靈感乍現,決定拍攝中國人自己的電影。于是幾個《定軍山》的片斷鏡頭引來眼球無數,“伶界大王”譚鑫培成了當年的天皇巨星,“中國第一部電影”的封號就這么落在了戲曲電影頭上。之后的一個世紀里,以京劇為主兼及各地方戲種的戲曲電影相繼出現,戲曲和電影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藝術語言開始不斷地交融和磨合。
樣板戲電影則讓京劇在上世紀中后期得以“另類”普及,許多經典唱段被傳唱不已,樣板戲在那個時代的影響力證明了電影手法在推廣戲曲藝術方面的重要性。中國電影在多個時間段里都有過非常杰出的戲曲電影,比如黃梅戲電影《天仙配》、越劇電影《梁祝》和《紅樓夢》,80年代全國超過7億人觀看了京劇電影《白蛇傳》,在《侏羅紀公園》等好萊塢科幻大片進入中國前,它就是我們自己的魔幻大片。
80年代末開始,商業大片蜂擁而至,把中國電影市場塞了個滿滿當當。面對競爭劣勢,戲曲電影偃旗息鼓。但是戲曲本身還在為拉攏市場做著不斷的嘗試,京昆繼續領跑舞臺,新劇不斷出爐。尤其是上海京劇院的新編歷史劇《廉吏于成龍》,上演7年蜚聲全國。于是有著近60年戲曲電影創作歷史的上海電影制片廠,與上海京劇院合作,將名噪一時的京劇《廉吏于成龍》搬上了電影銀幕。戲曲電影卷土重來。
6月11日電影《廉吏于成龍》在上海大光明電影院進行了全國首映,上千名觀眾在電影里感受到了劇組對京劇和電影這兩門淵源極深的藝術的致敬。青年導演鄭大圣力求讓沒有看戲經驗的觀眾不僅看懂電影,還要覺得有趣。影片中,康王爺的斗篷在鏡頭前四下翻飛,他拍桌瞪眼的時候,你仿佛能嗅到一點港產周氏喜劇電影的味道。福州臬臺于成龍被稱作廉吏,卻并沒有像以往的清官角色那樣頑固木訥,與康王斗酒的時候,他在眼角眉梢流露出了小小的喜酒性情。面對離別十幾年的妻子,他差點丟下三千臨刑百姓告老還鄉。
“你去劇場看戲,覺得好看,一定是因為這出戲里有打動你的地方,你和戲之間有著真正的交流,而不是因為某個臉譜或某個程式化的動作。”鄭大圣始終堅持自己創作的初衷,任何故事,不管是京劇還是電影,不管說的是哪個朝代,都是現代人說給現代人聽的。新編歷史戲《廉吏于成龍》在舞臺上精磨了7年,引起了強大的警世反響,“對所有關心現實的朋友來說,這是一個對現實有需求的故事”。
為尊重京劇特有的表演方式,導演鄭大圣先精讀演員們在戲劇舞臺上的表演,然后再來設計電影中的細節。當然電影免不了要對舞臺上的京劇進行調整,攝影棚里,不同于面對上千觀眾的劇場,只是對著攝影機在表演,肯定也會有新的設計。“幸運的是我能隨時隨地地向兩位表演大家來要意見。”這部電影打破了許多原先戲曲電影的俗塵框架,尚長榮對于導演的藝術創作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不斷鼓勵大家勇敢嘗試,不要墨守成規,別讓舞臺把鏡頭框死了。戲曲藝術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只有不斷打磨,才能永葆戲曲具有生命力”。
原劇主演尚長榮和關棟天繼續在電影中出演于成龍和康王爺,雖已對細節駕輕就熟,依然不敢大意。“沒有自滿,不敢驕傲”,談及此次拍攝,尚長榮表示也曾心懷顧慮。多年前他表演的京劇《曹操與楊修》被電視臺拍過,在看樣片時發現“舞臺被縮小了,表演被淡化了。不行,我(在表演時)需要極力的夸張。”這回拍電影,舞臺卻被放大無數倍,于是尚長榮在攝影棚的兩個多月里,總在告誡自己,千萬要注意度,別太夸張。
是“穿幫”,還是嘗試
鄭大圣是中國戲劇大師黃佐臨的外孫,《人·鬼·情》導演黃蜀芹的兒子。最初接到上影集團的拍攝任務時,鄭大圣還很驚訝,現在還能拍戲曲電影?拍戲曲片,可算是電影人眼中的雞肋。不知從何時起出現了一種說法,戲曲和電影之間好像有著不相容的鴻溝。

影片開機前,鄭大圣也有和很多人類似的這種焦慮,等到進入拍攝狀態時,他才慢慢發現二者之間并沒有那么不可調和的對峙和矛盾。“大家以前習慣中就認為,電影的實和戲曲的虛無法調和,我也一度覺得這個問題難解。其實壓根不存在人們以為的這種矛盾,差別只是在技術層面。我們這次要做的,就是在前輩們都探索過的各種可能性之外,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過去的戲曲電影無非是舞臺紀錄片和實景拍攝兩種,后者甚至真實到連騎馬上轎都用現實手法來演繹,這都大大削弱了戲曲本身的表現力。電影《廉吏于成龍》摒棄了一切皆寫實的做法,還原了京劇中最重要的寫意手法,比如比酒時的“杯中無酒”、探監時的“獄中無人”都給了演員極大的發揮空間。
導演也沒有給觀眾一把能以生活為參照的尺子,“實景-虛景-實景的轉換”讓觀眾置身虛擬與真實之間,很大程度上平衡了現實與歷史的落差。片中的許多場景被白色電影條屏取代,樹葉和人像的倒影隱約略見皮影戲的痕跡,亦實亦虛,給人以美感和極大的遐想空間。攝影棚、燈光等一些建筑部件首次直接暴露在鏡頭中。
在表現主人公的內心獨白的唱段時,樂師人影綽綽,琴聲千回百轉。京劇舞臺上最隱秘的琴師也被請到了銀幕前,以往樣板戲中大型樂隊的全程伴奏形式幾乎不見蹤影,而是盡可能地突出了京胡在京劇樂隊中的靈魂地位,還原戲曲本身所具有的韻味。
可這樣一來,不等于鏡頭“穿幫”了么?!鄭大圣強調這是自覺的嘗試,“因為我們需要一種假定性的情境,使得京劇能展開它所有的寫意和美感。”鄭大圣暫時也說不清這樣的嘗試是否會被大眾接受,“試試看吧。至少上海京劇院那邊挺喜歡的”。
目前看來,“穿幫”的運用廣受贊譽,不僅加強了京劇的特色,也將整部影片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劇中人物從歷史時空中被帶入電影,又以京劇的方式表現情節,攝影棚的故意暴露顛覆了傳統拍攝中最為人詬病的冗長戲曲模式,讓人物得以從歷史走回現實。
影片甚至可看作一部“妙用虛實、出入古今”的先鋒藝術片,蘊含導演深深的個人創作痕跡,充分展現了現代電影人對中國京劇藝術的理解。燈光琴師的藝術空間和人物再現的歷史年代相結合,在畫面構圖、人物特寫、情景調度和外景隱喻上都讓人耳目一新。
同時《廉吏于成龍》在內容上也稱得上是一盅心靈雞湯,勸當官者非我之有莫伸手。有人問,在公務員的財產申報制度遲遲不能建立的時代,我們極力塑造一個古代清官的道德形象,是否有點自欺欺人呢?戲劇評論家龔和德在研討會上說,“文藝不可能解決體制的缺陷,我們不幻想貪官污吏看了戲就會轉變,但好的戲能夠表達人民的愿望。”雖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