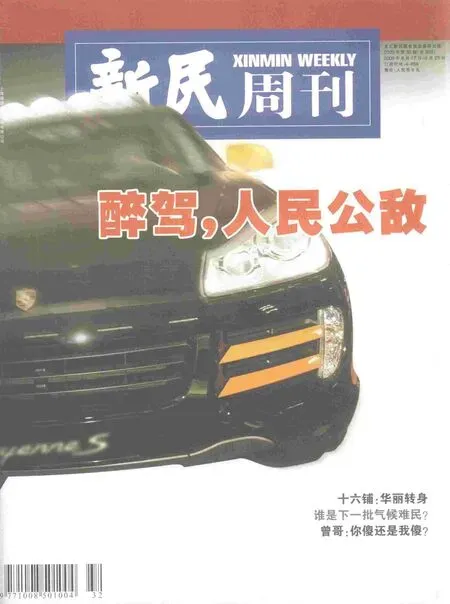被揪的“辮子”
邊 芹
自歐洲人做了主子,寬廣的星球,被擠壓成棧道,而他們似乎看不見自己綁架他人的獨木橋。這架從來沒有卸掉一個零件的龐大手術臺一面切割,一面呼叫著保全尸首,我時常禁不住要用這樣尖利的眼睛去看西方環保主義者。
兩只母雞

兩只母雞是李鴻章抵達首日傳媒炒作的“大菜”,凡是可以抓來證明中國人“卑瑣”的細節,一百多年來都被點滴不漏地篩選,成為傳媒“熱炒”的佐料。如此搭建的“圍墻”果然安然無恙地穿越了世紀。蜂巢的哨兵人人知道怎么選料。而蜂巢從無哨兵把守的中國人,一點都不懂得掩藏,常常是拱手奉獻。就像兩個人的舞臺,一個機關算盡,一個渾然不覺;戴著無塵手套的一方,細心挑選著投向對方的石塊,然后溫雅地遞上白凈的手,等待著對方的親吻。不幸坐在舞臺下的我,不知向哪里奔逃。
各報記者大發西式想象,說母雞是李鴻章的護身寶,神圣得很,因為一路都有專人看護。這也是做官做到以為全世界都一個行事法則,要吃新鮮雞蛋,手下人也不該馬屁拍到給他帶兩只活母雞,好像環游西半球是沙漠探險。在這類小事上不擅遮掩生存本能,使中國上層總有一條“辮子”揪在刁民手里,而其實以西方標準他們善得近乎癡傻。據說隨行那么多行李里連大米都帶了,因為不吃西餐。但也有一種說法,說他有意拒吃西餐。從自帶下蛋雞和大米可以推斷,洋務運動的主將李鴻章在西人眼里也還沒有摘凈“遠東鄉巴佬”的標簽。行為表面的雅與不雅,在貴族與小資接力“雕琢”過的西方社會,是“利”之外頭等重要的事,人群間所有不成文的規矩都是以此為起點的。這桿標尺劃界之深遠,以及它引起的“西方”與剩下的世界的對立,自身未被西方文明浸透的人往往看不到。時常是以為抓到根本的人,連皮毛都沒有摸到,如此循環往復。這個世界只在一定的切面自由翻轉,超出的部分,不是滯留在上就是捆綁在下。
這個文明遮羞的錦被是“cultiverlessignes”,這句法文翻譯起來找不到現成中文,“cultiver”是“栽種”、“培養”的意思,“signes”是“跡象”、“信號”的意思,解釋起來,就是“精心設計和培養外在信號”。這句話是打開城堡宮殿的鑰匙。在劃分“同類”與“非同類”時,此為利益之外的主要標尺。所謂界外的“小孩民族”,都是缺乏這一意識的,在他們眼里便幾同蟲豸。“精心設計和培養外在信號”用在個人身上,就是盡可能掩飾生存本能,好像房子要裝飾到看不見下水道、電線。外在信號與中國人可以解釋為虛榮心的面子完全不同,它是對立于生存本能而存在的。中華文明沒有將生存本能與外在信號截然對立的傳統,也就看不見兩者之間有你無他的界限。對生存本能的劃分,西人的精細和轉彎,讓我明白每一種文明為自己編織的繩結,直與彎,虛與實,都只在某個點上才找得到答案。比如馬桶和浴缸,有條件的人家絕不放在一起,因為馬桶在生存本能的界內,浴缸沒被劃入。再如痛哭與裸露,前者與尊嚴掛鉤,屬于生存本能的一種,故眾人面前切勿放聲,而后者則全不在此列。看到這里,讀者已經明白“母雞”在界的哪一邊。這條界中國人是不設的,很多事都能從這條界之有無找到源頭。我經常自問:中國人作為整體是否學得會“精心設計和培養外在信號”?我每看到可馴化的人和不可馴化的人朝著相反的方向聚集,然后站在界河的兩邊陌生人似地對望著,便驚問自己往哪里去?
“大商店”老佛爺
拉法耶特街走到盡頭,接近歌劇院的時候,錢勢的影子一路都在放大。先是銀行一家接一家,隨后便是老佛爺和春天百貨商店的總店。馬車經過拉法耶特街與直通歌劇院的阿雷維街的拐角時,李鴻章應該看到1893年剛剛建成的老佛爺大商店。他大概絕想不到,一百年后,店已開到北京和上海,而巴黎的總店盈門的也是中國人。你只在一兩個這樣的細節上看到時間退潮后已經琢刻完成的海岸,它難以更改的連接和斷裂,它的深陷和凸顯。
我在拉法耶特街遠遠就看到老佛爺占了地平線半個夜空的彩燈。它的原名直譯應為“拉法耶特廊”,因為它就在拉法耶特街和奧斯曼大街交會的地方。19世紀是西歐建起家底的一百年,工業革命的第一階段在1875年左右已經完成。新的發展因素:海外擴張、石油、橡膠、鋼鐵和其他稀有金屬、電、渦輪機和發動機等等,使西歐這些彈丸小國迅速向帝國發展。而新帝國是不放過老帝國的,奧斯曼帝國就在這個世紀被逐漸肢解完畢,只剩下現今的土耳其;接下來又肢解了奧匈帝國,讓單一民族的小國寡民散落了一地;中華帝國則是從那會兒一直“啃”到今天。分而治之,一直是“新千年帝國”的秘密武器。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西歐本土的社會面貌也發生了巨變:人口增長(海外征服使多余的人口占領了其他大陸)、銀行存款劇增(主要得自文化和實業資產階級人數的激增)、交通迅猛發展(覆蓋全國的鐵路建設和遠洋汽輪駛往各大洲在1830到1876年間基本完成)、大規模城市改建(奧斯曼男爵使巴黎城徹底脫出了中世紀古城的面貌)、現代輿論——報紙——的誕生以及隨之而來的廣告業(金融資本布設的最有效的馬前卒)……這一系列的變化匯總到一起,“大商店”從1855年起,在新興的資本大都市巴黎應運而生,風卷殘云般摧毀了已綿延了不知多少世紀的小本買賣。而其中第一家大商店就是李鴻章過幾天會去參觀的羅浮宮商場。
站在拉法耶特街與奧斯曼大街的交叉路口,望著可以遮避一切的繁榮燈火,想到一個世紀以后以同樣的勢頭摧毀“大商店”的“大超市”,事情只在事后被掂量,而且永遠似曾相似。我大概能體察幾分19世紀末新貴暴富的心態,這種事情以同樣的面目或遲或早地會讓不同的眼睛看到。今天世界的煙花,歐洲早在19世紀就點上了雷管。19世紀被很多人稱為“愚蠢的世紀”、“心靈生病的世紀”、“掠奪者的世紀”,雨果發出悲鳴,左拉開始解剖,但所有的貶義詞都未能阻擋失敗者不遺余力的模仿。自歐洲人做了主子,寬廣的星球,被擠壓成棧道,而他們似乎看不見自己綁架他人的獨木橋。這架從來沒有卸掉一個零件的龐大手術臺一面切割,一面呼叫著保全尸首,我時常禁不住要用這樣尖利的眼睛去看西方環保主義者。
金融丑聞
李鴻章抵達巴黎前的那幾年,社會經濟這匹快馬,是在資本的溫床上奔跑的,溫床之下是拆都拆不斷的食物鏈。1893年3月揭出的巴拿馬運河丑聞,讓八萬多運河公債認購人傾家蕩產不說,還把一批政治家、新聞記者拖下了水。這條旨在將大西洋和太平洋連通起來的運河,因為一開始就設計錯誤,卷裹了遠遠超出預算的資金,工程承建人費爾迪南·德·萊塞普為了不致破產,買通政客和新聞記者,向公眾隱瞞真相,繼續發行債券。金融資本的詐騙式運作,在胚胎里已經孕育,且從未因一次敗露而停止,堵上一個洞,再去打另一個洞,鼴鼠一般。人們往往是在被褫奪之后,才意識到自己是下一個受害者。在這張溫床上的西方近現代史也沒有多少誠實可言,詐騙方式從這個體制的起源,油點式地漫延到社會各個領域。左拉在小說《金錢》中對19世紀的貪污受賄有精確的描述。事情最終敗露后,不光公共建設部部長被判刑五年,連設計和建造埃菲爾鐵塔的古斯塔夫·埃菲爾都差一點被送進監獄。今天千里萬里來“瞻仰”這座“現代神話”之塔的人,在埃菲爾銅像前已看不到這一切,資本的神奇在于它抹去自身丑陋的驚人效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為那些認購債券的中小資產階級出了氣,因黃熱病和工程事故死在運河工地的無數中國苦力,則沒有人提到一筆。時隔一百多年,應該有人去那個運河邊為這些無語的鬼魂立一塊碑。
巴拿馬丑聞被稱為“世紀丑聞”,足見那個時代金錢將社會上層捆綁在一起還沒有編織完“合法”的網罩,下面的世紀則一次比一次“聰明”。而且因為這樁丑聞涉及到兩個猶太裔操作手,反猶與反資本主義一路捆綁在一起,成了19世紀的風景。這些被金融資本趕鴨上架的國家,在與傳統割斷臍帶的陣痛中,一步一個血印,但無不被精巧地掩蓋。如今只看這個國家放在圖書館書架上的書,只能看到這場爭斗勝利者一方的證詞。不用一兵一卒的“占領”過程,時常讓腦筋狹窄的土著壓抑和不平,族群間的明爭暗斗一直持續到二戰撕臉。兩個撕打了幾個世紀的陣營,從臺上打到臺下,讓我這個異鄉人時常如墜云霧。我最驚心動魄的發現是青史無言,最初我以為跨度至多半個世紀,越往深探越是霧障重重。若聽如今被封嘴的鬼魂的說詞,早在路易十六被砍頭前,征服高盧文明的手就已經伸進來了。但正史上一個字沒有。華夏民族可以接受現實沒有真實可言,但尚未被扭曲到接受歷史沒有真相只有強權。來自遠東的我,多少看到了一些文明城堡被攻占的細節,以及過去幾千年被高山大洋護于一隅的我們近代兩百年殊途同歸的命運。有一天我們的歷史是不是也將遭逢真事隱假語存的暗算?
理想主義反抗者

裂紋之下是一些絕望的反抗者,但征服者總能將反抗者分在南轅北轍的派別里,在這條你死我活的分裂線上,掠盡風光的其實是“背叛者”。正義的殘存是加入“狼俱樂部”的主要障礙。靠剿滅正義與善征服異文明,讓人看見已經慘不忍睹,如果失敗者還要背著永世的罪名,則清醒者只有地獄可以遁逃。
而暴力就成了“分而治之”這盤菜的調味料。1893年12月9日,眾議院被炸,造成眾多議員受傷。投擲炸彈的是奧古斯特·瓦揚,兩個月后,他被送上斷頭臺。為這類人早已準備好了名詞:“左翼安那其分子”。欲使一個社會的零星反抗者醞釀不出一場革命,要學會選擇名詞的精細。據說他這是為1892年被砍頭的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拉瓦紹爾復仇。拉瓦紹爾也因為搞了四起爆炸被送上斷頭臺,他在法庭上說了一句話:“這個社會在腐爛。”
這是19世紀資本洪水下的呼號,你從呼號之凄厲和嘶喊者被人遺忘的速度,大略可以體察時代轉彎之急速。祭祀兒還從來沒有這么快地被拋棄過,背叛者還從來沒有這么堂皇地與正義為伍,今天的世界是在快速“腐朽”中誕生的,為此小資們承擔了解開傳統社會道德繩結的使命。光華萬丈的“人本”為大盜掃清了圍墻和阻力。我曾一度以為這個包裹著精美綢緞的國家,埋掉二戰的傷痛,便是被歷史特別垂顧、光滑無痕的土地,及至觸碰19世紀,才摸到這個民族曠日持久的壓抑,以及屠刀下的馴服。
很快,1894年6月24日,又有一名“安那其分子”鋌而走險,為回應政府“嚴打”無政府主義者的措施,加西里奧在里昂暗殺了法國總統薩迪·卡諾。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李鴻章應總統之邀參加國慶閱兵的那天,又有人向總統開槍。
19世紀被送上斷頭臺的人,除了刑事犯,就是理想主義者。總要有一個世紀的“合法”屠戮,才能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道路上掃清障礙。所以李鴻章到來的前一天,《費加羅報》有一篇雜議上說他來得不巧,看不到斷頭臺了。因為夏天上層社會都去外省度假,巴黎的行政和執法就有一個停滯,要等到9月,才能觀賞到巴黎人最喜歡觀看的節目:砍頭。總不能讓遠道而來的客人等到那時候吧。何況這位撰稿人懷疑李鴻章會把法式斷頭臺引進中國,因為早李鴻章而來的駐法公使陳季同先生,對斷頭臺這玩藝很好奇,曾特意跑到法國19世紀最出名的屠夫戴布雷行刑處觀摩,最后得出結論:
“這玩藝拿到我們那兒割起來就不一定這么方便。”
“為什么?”
“因為我們有辮子。”
在轉上阿雷維街走向19世紀大工業藝術的杰作歌劇院的那幾分鐘里,我忽然問自己:生不逢時是一個人的錯位還是整個時代的脫軌?來的時候,燈一盞接一盞地滅,背后拖帶著一百年都甩不掉的陰影。可以從這個孔穴去透視李鴻章嗎?我90年代初,也是在初次走到這地方的那幾分鐘里,感到了背后深長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