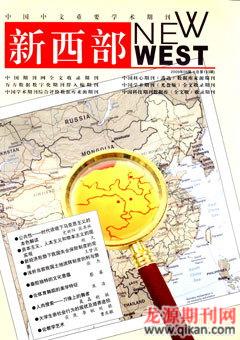圖里描述翻譯學研究述評
張建青 岳靖凡
(1.浙江工業大學浙江杭州310024;2.西安工業大學陜西西安710032 )
摘要圖里倡導的描述翻譯學目的是建立實證的科學翻譯學,其研究以譯文為導向,通過對翻譯規范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兩大嘗試性翻譯規律。其理論擴展了翻譯研究的范圍,有助于人們全面系統研究翻譯,大大促進了翻譯研究學科地位的確立。國內外對其理論也有質疑與批評,但其中有些顯然未能理解圖里理論的初衷和特點,實為“苛求”之論。
關鍵詞圖里;描述翻譯學;規范
圖里是描述翻譯學的領軍人物,《描述翻譯學及其他》則為其理論的總結和升華。
一、描述翻譯學的特點
首先,描述翻譯學的目的是建立實證的科學翻譯學。圖里指出:“尋求普遍規律是任何學科的不變目標和首要追求,沒有它們,則任何的所謂理論和科學活動都不可信”。他認為一門實證學科如果沒有一個描述性分支就不能稱其為完整和(相對)獨立的學科。
另外,其研究的出發點為多元系統文化理論。描述翻譯研究以譯文為導向,最重要的是將翻譯置于譯入語文化的社會和文學系統之中,正是這一系統中的位置最終決定了譯者的翻譯策略。科學的翻譯研究方法“應當是描述性和系統性的;應該重目的和功能;應當研究影響譯文產生的接受的規范(norm)和限制(constraint),研究翻譯與其他文本處理之間的關系,研究翻譯在某一特定文學中的地位與作用,研究在不同文學之間相互影響種翻譯的地位與作用。”描述翻譯學構建的方法論可歸納為三個步驟:
一是把文本置于譯入語文化系統內,檢驗其重要性和可接受性;
二是比較源語文本與譯入語文本,辨識譯入語文本偏離源語文本的動因,從而抽象概括出翻譯行為規范;
三是把所概括的規范確立為規約未來翻譯行為的規律。利用前兩步對文本進行多次檢驗和比較,使析出的規范在類屬、時間、作者等方面不斷豐富,為探索訂立影響翻譯行為的普遍性規律提供依據。這些規律便是圖里描述翻譯學孜孜以求的的一般理論形態。
二、主要理論
1、翻譯行為規范
“規范(norm)”是一個社會學術語,主要指一個社會或文化里某些“約定俗成”、有著相當普遍認可性的行為、道德以至觀念上的標準。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一般認為它反應了社會文化中人們共享的普遍價值觀念。在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中就曾提及“規范”,圖里則把它運用于翻譯研究,通過系統化,使之發展成為自己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認為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講,翻譯乃多種類型與各種程度制約(constraints)的產物。規范即為制約(constraints)。圖里認為,翻譯行為是一種受規范規約的活動,規范指社會文化對翻譯行為的制約。就約束力而言,處于極端一頭的社會文化制約的可稱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較為絕對的規則(rules),另一端則是純粹的個體癖好 (idiosyncrasies)。規范則呈梯度分布在規則和個體癖好之間,在約束力上介乎二者之間。從規范的角度看規則和個體癖好,前者是“(更為)客觀的”規范,后者則是“(更為)主觀的”也即“更少客觀性”的規范。可見,這一概念在其理論體系中舉足輕重。
圖里挪用規范這一概念指稱譯者翻譯時面對的種種制約,這些制約主要來自于譯入語社會及文化,卻直接影響譯者的翻譯決定。他引入規范的目的在于通過個案分析為翻譯行為確立某種統計學意義上的普遍規律。他之所以將規范作為核心概念,一是因為規范是建立和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因素,也是解釋包括翻譯活動在內的社會活動的關鍵因素;二是確立規范可為建立影響翻譯行為的規律提供依據。這些規律源自大量的文本描述研究,可以推演升華成為翻譯學理論的構建要素。
圖里提出了過程中體現的三種翻譯規范:初始規范(initial norm)、預備規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規范(operational norms)。初始規范指譯者首先須在源語文本規范與譯入語文化規范之間做出的基本選擇。預備規范在翻譯行為未開始之前就已發揮作用,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翻譯政策,二為翻譯的直接性;前者考慮的是選擇什么作品來翻譯,后者指通過源語翻譯其他語言的容忍度。操作規范則支配著翻譯過程中所作的各種決定,可以分為結構規范和語篇語言規范。三種規范中,初始規范對其他兩種規范具有統攝作用;操作規范具有形而下特征,是初始規范在翻譯過程中的明晰化。
研究翻譯規范有兩種主要資料來源:一為語篇材料,即譯文和分析性的譯文目錄。二為語篇外材料,指半理論的批評文章,如規范性的翻譯理論或觀點,譯者、編輯、出版者或者其他與翻譯有關的人或私下的說明、對個別譯本的評論等。
2、兩大翻譯規律
“由描述翻譯規范出發揭示翻譯規律正是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的特征。”而翻譯學在建立規律方面還缺乏自覺,翻譯學(Translation Studies)成為一門科學的學科的希望和出路就在于確立翻譯規律。因此,探討翻譯規律正是圖里理論的落腳點和自然歸宿。圖里為此提出了兩大嘗試性翻譯規律:
其一為譯文漸進標準化規律(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也可稱為文本功能轉化律(the law of the conversion of textemes to repertoremes)。就最一般的情況而言,它指的是源語文本往往在翻譯中被轉化進入符合譯入語文化系統的形式符號庫。從另一角度看,它又指在翻譯中,譯者更愿意擇取譯入語文化形式庫中的慣常用法替代源語,源語文本中展示的文本關系常常被整合、忽略乃至全然漠視。
圖里的研究表明:譯者將原文中新奇陌生的文本置換成符合譯入語讀者閱讀習慣和審美期待的內容與形式,其結果便是譯文的標準化程度(即在適應譯入語文化規范方面)提高了。這么做有多方面原因,主要讓譯入語讀者易于接受譯文。
其二為源語干預規律(the law of interference)。就最一般的形式而言,可以將這一規律視為翻譯中源語文本的各種構成要素趨向語在譯文得以傳遞;這種傳遞既可能為正傳遞,也可能為負傳遞。也即在翻譯時,源語的某些文本結構(例如詞匯特征、句法特征等)會轉移到譯文中。該規律表明,源語文本對譯語文本產生某種“默認”(default)作用。圖里特地指出:從譯入語系統的角度來看,對源語干預的容忍程度受制于語言和文化的相對聲望,以及與后者的權力關系。人們對從強勢語言或文化譯入的作品容忍度較高,在譯入語語言文化處于弱勢的情況之下尤其如此。而且,就語言和語篇層次而言,即使是對同一文本的干擾和容忍亦未必一樣。完全沒有必要對源語的干預太過憂慮,因為“所有的文化,無論處于哪個發展階段,都不得不接受干預,對此發動戰爭沒有任何意義。”
三、主要貢獻
一是大大促進了翻譯研究學科地位的確立。我們知道,其實霍姆斯早在1972年就提出應把翻譯學建設為一門經驗性實證性學科,并寄希望于描述翻譯學的發展。而圖里研究成果豐富,通過眾多實際個案分析,掌握了大量實證材料,證明了翻譯的重大作用和影響;并且由于其研究力求客觀,呈現出一般實證科學的特點。這樣,學界終于廣泛認可了翻譯研究的價值,翻譯學得以確立。
二是擴展了翻譯研究的范圍,有助于人們全面系統地研究翻譯。“翻譯”的涵義在描述翻譯學中得以空前擴大,以前處于邊緣位置的很多翻譯現象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以前,人們一般認為只有與原文完全對等的文本才可以稱為翻譯,而將現實中的其它翻譯行為加以貶斥。圖里認為:只要是在譯入語文化中以翻譯面貌出現或譯入語讀者認視之為翻譯的一切文本都應稱為翻譯。這樣一來,為眾多原來處于邊緣位置的翻譯現象,如轉譯/重譯和偽譯都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內容。
由于描述性翻譯研究關注更加廣闊的譯入語社會文化,探討翻譯與譯入語文化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這樣,就能更為系統和全面地研究翻譯,從而對實際存在的翻譯現象做出更加合理與準確的解釋。對此,我國翻譯理論家也有極高評價。
四、有關質疑與批評
首先國外論者如曼迪指出:圖里的“規范”太多,含義模糊,而且這些規范具有施為傾向和規約功能,有悖于描述性分析的初衷。此外,從個案分析中概括出的“規律”,似乎只是翻譯行為的一些慣常信念,乃至是無須證明的信念,且這些準科學的抽象規律在何種程度上可應用于翻譯實踐也頗遭爭議。再如有學者就價值中立對社會價值取向遮蔽方面提出質疑。斯內爾-霍恩比(Snell-Hornby)曾婉轉批評圖里堅持的所謂中立客觀立場,認為其成就與不足都與其刻意回避價值判斷不無關系。韋努蒂則斷言:翻譯研究永遠都不可能僅僅是描述性的。
我國研究者也提出,圖里為使描述翻譯學成為一門無涉價值、可以實證的科學,采用了簡化和分離范式構建其理論模型,實質上體現了對科學方法論至上的工具理性的推崇,付出了犧牲主體性等人文因素的代價。它有三大不足:一是片面強調研究者的客觀中立,過于避免價值判斷。二是脫離翻譯實踐,過度提倡將不利于翻譯事業的健康發展。對于人們認識具體譯作的優劣并無幫助,過度提倡必將不利于總體翻譯質量的提高,甚至對翻譯實踐產生負面影響。三是對譯者的創造性不夠重視。
上述看法,如從圖里研究的出發點和目的看其描述翻譯研究,則對其批評雖各有道理,卻也多有強求之嫌。因為圖里描述翻譯研究強調“價值中立、客觀性、實證性”(而實際研究中并未將之推向極端!),其目的恰是為凸顯翻譯研究的科學屬性,以提高翻譯研究的地位。而其通過描述分析譯文探尋翻譯行為“規范”和“規律”恰是為了認識“現實中的翻譯是怎樣,為何這樣”,合理預測和解釋“將來的翻譯趨向”,并非要指導具體翻譯實踐即“如何翻譯”。由于以描述文本為中心,自然對譯者談論較少,但圖里并未忽略譯者作用,其書中有關論述可以證明。只是談論不多,但主要卻是由其研究的重心乃翻譯行為“規范”與“規律”使然。至于認為提倡描述翻譯學會縱容誤導糟糕的惡劣譯文出現,則更是不合邏輯。因為導致劣質譯文出現的原因很多,與描述翻譯學恰恰關系不大,且根本無直接因果關系。如此批判描述翻譯學,恰恰找錯了靶子,是“歪打”,而非“正著”!說重一點乃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參考文獻
[1][2][4][5][6][7][8][9][10][11][12][13][14]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第259,1,36-39,54-55,55,56,259,56-59,65,259,268,269,275.
[3]Hermans,Theo 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C].London&Sydney:Croom Helm.1985.11.
[15]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3.
[16]張思潔.描述翻譯學中的工具理性反思[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7):63-65.
[17]韓子滿、劉芳.描述翻譯研究的成就與不足[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111-116.
[18]潘文國.當代西方的翻譯學研究[A].楊自儉.譯學新探[C].青島:青島出版社,2002.
作者簡介
張建青(1970-),山東人,浙江工業大學講師,文學博士.
岳靖凡,西安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