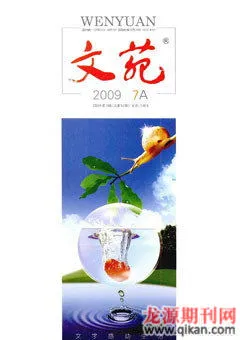青春留白
許 佳
我至今記得,高考的那一天——高考的時候。
晃眼的太陽底下,我們大家站在考場的外面,在我們的周圍,還有很多很多的人,還有張先生在跑來跑去。A他們一幫直升的人來送我們。他們站在我們面前,笑嘻嘻的,祝我們考試成功,還說著笑話。我站在那里,望著A。他的樣子還是和三天以前在瑞金路上一樣,可是現(xiàn)在卻令我忐忑起來。三天以前,瑞金路金色和藍色的黃昏里面,他氣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對我微笑,摸我的頭,拍拍我的面頰,把我抱在懷里——我好像完成使命了,可以就這樣待在瑞金路的水底,咕嘟咕嘟地讓水泡往天空冒上去,然后,靜悄悄地,不說話,什么話也不說。
我腦子里老是這幅圖景:太陽升起來了,熱還高高地盤踞在天上,沒有徹底地散發(fā)開來。細密的小汗粒滲到皮膚表面,變成薄薄一層,頭頂上雪亮雪亮的陽光,像毛毛雨一樣,飄飄灑灑。身后的考場,玻璃亮晶晶的,什么都很清晰。我們大家站在門外,送考的人和我們輪番握手,一個一個地輪過來。我們笑著,手臂交錯著……
A走過來,握著我的手,笑瞇瞇地說:“好了,給你復習了三個月。三天高考結(jié)束后,我就可以永遠也不要看到你了。”
我高高興興地對他咧開嘴笑,說:“是啊是啊!”
我們長久地交換著目光,好像真的在為永遠也不再見面這件事而由衷高興著。
顧湘是我的朋友。我進華東師大的時候她在上戲,現(xiàn)在我依然在華東師大,而她在莫斯科學習廣告。我是一個文風曉暢的作者,而她則憂郁、黏稠、優(yōu)美。我慷慨地把這些贊揚普魯斯特的言辭獻給了她,因為就像任何人都會艷羨自己沒有的東西一樣,我也艷羨她。
我們都已經(jīng)不是當年那個懷揣處女作的小女孩兒了,寫小說是我們在世間熟悉的不多幾個技能之一,如果寫不出小說,就幾乎像被掠奪了一半的靈魂那樣——不錯,這是值得認真恐慌一番的。
俄國的夏天來到了,我按圖索驥,回憶屠格涅夫的小說片段,關(guān)于樹林、花園、天空。在這中間,我要強硬地插進一個莫斯科大市場的畫面——這是顧湘向我描述的,她打零工的地方。她打的零工不錯,一切順利,然而卻令她很痛苦。她說,其實不適合工作不是我們的天才,而是我們的缺陷——為什么別人都能做,偏偏我們就不能做?可見是缺陷。
吳虹飛說:“每一位天才總要到長大之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平庸和夢想的艱難。”此話甚真,不由讓我將她引為知己,盡管并未見過她一面。我們已經(jīng)不是當年的十七歲天才少女,沒人再原諒我們疏懶,有時則有人懷疑我們狡猾。近日讀到E.B.懷特的一段話,喜不自勝,覺得再也沒誰能如此精煉地概括我生而為人的一切苦惱了,所以就拿來放在結(jié)尾。
“如果這個世界僅僅是勾人的,那就不用費神了。如果它僅僅是挑戰(zhàn)性的,那也問題不大。糟糕的是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會被改良世界的欲望和享受世界的欲望搞得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