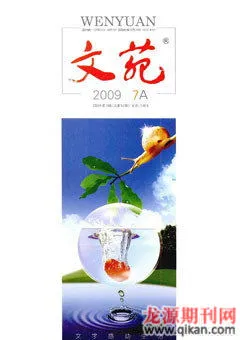棉花五條
肖復興
胡同常能給我意外的收獲,它無論長短,都像是緩緩展開的一盤電影膠片,總會有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景物,或根本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現,就像電影里突然出現節外生枝的跌宕,出現萍水相逢的驚喜,讓我有一種隱隱的期待,像有了懸念似的。每一次去胡同出門之前,心里總要想,這一回,能夠碰上誰?
在棉花胡同五條的西口,我見到的第一個人,是一位小腳老太太,我只是向她打聽路,沒有想到她老人家就是胡同為我今天上演的電影的主角。她長得身材苗條,眉清目秀,雖說滿嘴只剩下一顆門牙,但仍然能夠想象得出年輕時候一定是個美人坯子。
老太太很健談,我是問她您是住這兒的老街坊嗎?引起她的話茬子開了閘門的,她告訴我他們家住在這里一百多年了,四輩人都住在這兒。她伸出干蔥似的瘦削的四根手指,然后指著五條靠南把口的一個小商店說,我們爺爺原來就是在這兒開的一家油鹽店的鋪子,叫泰昌號。我們家一直就住在棉花胡同24號。我看出來了,泰昌號和24號原來是連在一起的,前店后院,一家子連做買賣帶過日子,是那時的小戶卻殷實人家。
她指著五條路口把北的一個房門告訴我:這里原來是一個麻刀鋪,開鋪子的是一個羅鍋,他有兩個老婆。說起這一帶來,老太太如數家珍。我繼續請她給我講古,她對我說,棉花胡同一共有九條,現在頭條和上二條都拆了,其余的幾條還在。早先年間說:人不辭路,虎不辭仙,唱戲的不離百順韓家潭,說是唱戲的名角住在百順胡同的和韓家胡同的多,其實,住在這兒的也不少。說著,她向我例數頭條住過貫大元,三條住過于連全,六條住過趙桐山,七條住過裘盛戎、李少春,八條住過金少山,還住過馬福祿,我們五條住過葉盛蘭。別說我們旁邊的山西街還住過茍慧生,椿樹胡同還住過余叔巖和尚小云呢。你說多不多吧?
看老太太說起他們,像說自己的親戚那般的親切,真有些為她為這些都已經逝去的老藝人,也為這些條胡同感到欣慰。一條胡同,正是因為有了這樣活生生的人才有了生命的氣息,更何況,這是些富有藝術生命的氣息。即使歲月變遷,這些名人故居已經是人去樓空,卻一樣是小巷長憶,細雨夢回,空氣中都還蕩漾著他們唱腔的韻律。
如果不是后來走來一個小伙子,老太太不會走。小伙子對我說,你別聽她瞎講,她老了,腦子都糊涂了。老太太不樂意了,反問小伙子,我腦子怎么糊涂了,哪兒說的不對了?等聽完小伙子的白話之后,老太太早不見了。我一人從五條西口走到東口,見到好多老宅門都像是葉盛蘭家,不知道哪一家確實。心里有些埋怨那個小伙子,莽撞得把老太太氣走了。折回西口,走到24號院,希望老太太在那兒。還真在院子里,好像有意在等著我似的。我問老太太葉盛蘭住在幾號啊?我沒找到。老太太走出院子,對我說我帶你去。我要攙扶她,她甩開我的手說沒事,我身子骨好著呢。我問她您多大年紀啦?八十整,說完,她自己先笑了。哪兒像八十的老人?踩著小腳,像踩著輕松的點兒,她領我一直快步走到東口(一路上還指點著那些老宅門,其中一個是當時名醫魏龍驤的老宅,魏是京戲票友,許多住在附近的京劇名角都到這里來看過病,曾聯合送他一幅“仁術可風”的匾),指著路北7號院告訴我這就是葉盛蘭的家。
院門很古樸,紅漆斑駁脫落,但門簪、門墩都還在,高臺階和房檐下的垂花木欞也都還在。我走進院子,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雖東廂房前蓋出新的小房,院子的基本面貌未變。我走出來問老太太進門的地方原來是不是有個影壁啊?她說我記不清了,我還是原來查衛生的時候到他們院子里來過,這一眨眼都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
想起放翁的詩:“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葉盛蘭活著的話,今年90歲,比老太太大10歲,心情大概和老太太是一樣的。
往回走,走到一個小胡同口,老太太對我說,你從這兒穿過去就到山西街,茍慧生的老宅子就在那兒。我想把老太太送回家,剛走幾步,老太太擺擺手,趁天沒黑,你快去吧。多么好的老太太,讓我想起自己的母親,心里很感動,臨別的時候問您貴姓?她說姓尚,我說那您和尚小云一個姓啊!她立刻開心地樂起來,笑開了只剩下一顆門牙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