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西方看純中國
劉婉媛 于曉東
劍橋大學出版社將首度出版由中國本土作者撰寫的中國書籍,而對于中國而言,這是中國圖書“走出去”戰略的重大突破
對于幾乎全世界的學者而言,劍橋大學出版社無疑是學術生涯中的一個符號——無人不曾在學術殿堂中享用過它所奉獻的精神食糧;同時,學者無人不將它視為著作等身、流芳百世的重要載體。
“流芳百世”之說并不夸張——從1534年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圣旨中誕生至今,以學術和教育為主旨的劍橋出版社已經走過了475年。四個多世紀的出版史伴隨著牛頓、達爾文、羅素、愛因斯坦等等如雷貫耳的名字,給全世界留下無數世人景仰的鴻篇巨著。
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中國為主題的著作,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和鬼才李約瑟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但是,這兩套叢書的所有內容,均為西方學者所撰寫。
2009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年”。今年,劍橋出版社決定引進《人文中國系列叢書》。這套分為三輯共30冊的叢書,涵蓋“中國哲學思想”“中國民間美術”“中國傳統醫藥”等等中國傳統文化和民俗的內容——這是劍橋大學出版社首次出版由中國本土人士撰寫的書籍。
除此以外,劍橋大學還把今年的生日慶典搬到了北京舉行,并帶來了全球總裁,全球財務總監,亞太、美洲、歐洲三大地區總裁等等幾乎囊括所有高層要員的豪華慶生陣容。在慶典上,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只有十幾年歷史的年輕出版社——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正式簽署了《人文中國系列叢書》的版權協議。
此次合作是“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重要內容之一。三年前,國務院新聞辦和新聞出版總署聯手推出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具體措施包括圖書出口,與國外出版社合作出版,邀請國外知名作家學者撰寫中國主題的著作等等。
“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給中外出版機構合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強烈的政府背景也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關注。“教育西方”(Educating the West)——英文報紙《中國日報》5月26日發表的關于中國圖書“走出去”的文章標題——無疑又抽打了西方讀者的神經。
此次納入劍橋大學出版社視線的《人文中國系列叢書》的內容,是西方社會早已接受并熟悉的中華傳統文明,意識形態的分歧在此無跡可尋。但無論如何,一個象牙塔頂尖上的西方出版社與中國的首度重要合作依然令人矚目。
5月19日,劍橋大學出版社總裁史蒂芬?伯恩(Stephen Bourne)在北京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我們是一只拿來做實驗的小白鼠”
中國新聞周刊:劍橋出版社為什么選擇出版《人文中國系列叢書》?在這個合作的過程中,一開始是誰先邁出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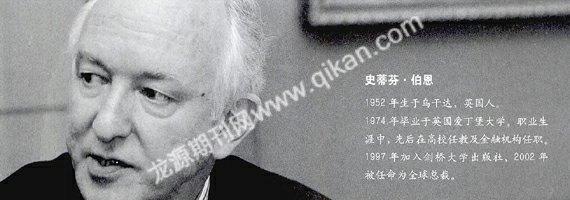
伯恩:中國的發展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和想象。而對于中國,人們最感興趣的莫過于文化和歷史。此外,中國出版社的同行也在探討可能在國外出版的書籍,顯然他們也認為傳統文化系列可能更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興趣。
至于誰先邁出第一步,真實的答案是:不是中國政府,或者是中國圖書對外推廣部門。其實,十幾年前就有一個中國的出版社找到我們,建議出版一些書,但當時我們認為那些書水平不夠。后來,中國政府部門跟我們說,“我們可以提供協助,包括資金支持。”由此促成了后來的合作。
除了文化系列以外,我們正在和中國的出版社商談歷史方面的圖書出版。這些歷史書是以中國的角度來詮釋歷史,和西方的角度不一樣。等我們合作雙方彼此之間更熟悉之后,我們可能會去尋找別的話題,有可能是數學、物理、法律方面的書籍,也可能是社會、政治方面的著作。將來,我們出版的中國書籍會更偏重于學術方面,畢竟我們是一個學術出版社。
我們的讀者,尤其是美國讀者更偏好于本國作者撰寫的書籍。比如,美國讀者所看的關于中國歷史的書籍,絕大多數是由美國人寫的。所以,我們想給他們提供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比如,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歷史。我們希望能給讀者尤其是學者們在學術研究上提供幫助,向他們呈現歷史、政治等方面的各種資料,讓他們從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結論和觀點。但是,如何去實現這一點,我們現在也還沒搞楚,沒有先例可循。所以說,我們就是一只拿來做實驗的小白鼠。我想,要說服西方的學者們去看這些從不同角度詮釋的歷史書籍,估計會很費勁,但我們已經做好付出種種努力的準備。
中國新聞周刊:會不會擔心由此引來質疑?
伯恩:不會。只有出版“壞書”才會讓我們擔心。所謂的壞書,是指內容糟糕,寫作也糟糕。如果我們覺得某一本書的寫法不對或者不適合西方人的閱讀習慣,我們會和中國出版社或者作者商量,建議他們補充素材或者重新組織文章結構,但我們不會改變書的內容。
中國作者的寫法和西方的寫法確實是有差別。劍橋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書,至少會有兩個相關領域的專家的評價,這些評價和建議都會反饋給作者。我們出版中國書籍也會采用這種方式。但除此以外,中國的出版社也應該有意識地幫助作者了解西方的標準和市場要求。我曾向中國圖書對外推廣部門建議,他們應該對編輯進行培訓,讓他們更了解西方讀者的閱讀偏好以及市場的選題需求和標準。我還建議采取中西方作者合作的方式。比如,中國作者“王先生”不為西方所知,他的書在西方就很難賣得出去,但如果這本書是王先生和詹金斯(英國著名學者)聯合撰寫,西方人就容易接受——這是向西方介紹中國作者的一個捷徑。
發掘、出版有吸引力的書籍在哪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基本上我們拿到的出版建議草案,十個當中只有一個能被選中出版。
“不要刻意制造爭議,不要無端出言不遜”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和中國的合作,劍橋出版社有什么打算和規劃?
伯恩:我們與中國的合作將是長期的。我們不僅會和中國出版界合作出版中國書籍,還會通過這種合作關系去尋找、培養一些能在西方發表作品的中國作者。我們和中國圖書推廣計劃部門還討論另一種合作的可能性:請熟知中國的西方學者撰寫更多關于中國的書籍。
我們也想通過與中國政府及出版機構的合作,在中國出版市場占得先機和有利地位。這種合作是雙向的,就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樣,如果僅限于單向,這種關系就不會長久。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西方人士擔心,你們和中國政府的合作會影響你們的出版立場,你對此如何回應?
伯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始終保持著學者式的立場,也就是說,我們努力呈現平衡的觀點。與此同時,我們不會刻意地去尋找、發掘所謂的爭議。我和我的繼任者們不會一方面保持與中國官方良好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還刻意出書指責中國政府。我們的一些作者在談及中國政治的時候,有時會有批評中國政府,但中國政府隨時都可以說“我們還沒準備好在中國出版這本書”。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刻意地去制造爭議,不要無端地出言不遜,也不要試圖在中國出版一些中國政府還沒準備好接受的書籍。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出版業正逐步開放,你們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的機會?
伯恩:目前,我們在中國的主要業務是與當地出版社合作出版英語教材,我們和外研社、新東方等有很好的合作關系。與我們在美國的業務相比,中國市場的業務只有其十分之一,但這個市場的需求在迅速增長。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我們在中國的業務會增至全球第二位,僅次于我們在美國的業務。
我們過去出版的關于中國的書籍,都是由西方作者或者是海外的中國人撰寫的,這一點和我們在印度的情況很類似。但是,我們在印度的經營模式是不一樣的。在印度,我們收購了一家本地的出版公司(這在中國還不允許)并將其更名為“印度劍橋大學出版社”。我們在印度市場的出版發行,或者在國際上出版發行印度作者撰寫的書籍,都通過這個公司進行。但在中國,我們距離這一目標還很遠。我們當然希望,15年或者20年以后我們可以在中國建立起類似于我們在印度的經營模式。至于何時外國出版機構能進入中國,那要看中國政府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