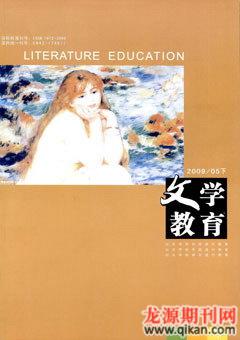《臨江仙》詞意分析
王文娟
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河南洛陽人。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詩人。他的詞作以清婉秀麗為主要特色。陳與義于紹興五年(1135年)前后退居湖州青墩鎮壽圣院僧舍,本詞大約寫于此時。這是一首名作,上片追憶二十多年前在洛陽故鄉度過的豪暢歡樂的生活,歷歷如見情景,如聞聲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是廣為傳誦的名句,意境極美。風格爽利。劉熙載說此二句“因仰承‘憶昔,俯注‘一夢,故……不覺豪酣轉成悵悒,所謂好在句外者”(《藝概》)。過片轉言今情,“二十余年”二句寓無限國事滄桑、身世飄零之慨,用筆空靈,內涵豐富。北宋覆亡后。作者曾“避亂襄、漢,轉湖、湘,逾嶺嶠”,歷盡艱辛,這里抒寫真情實感、痛定之痛,動魄驚心。末三句宕開一筆,故作曠達語,而覺嘆惋之意裊裊不絕。胡仔說“清婉奇麗,簡齋惟此詞為最優”(《苕溪漁隱叢話》)。張炎稱此詞“真是自然而然”(《詞源》),彭孫通云:“詞經自然為宗,但自然不從追遂中來,亦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仍歸平淡。”他稱此詞“杏花”二句,“自然而然者也”(《金粟詞話》)。
通首詞中,沒有一個華麗詞藻,沒有一處用典,更無艱澀陰晦之詞,簡直如一幅白描山水畫。雖句句平白清晰,完全出自自然,但又不失之于平直,而給人一種清新之感。
開首“憶昔”二字,引起題中所云“憶洛中舊游”,回憶在洛陽時與友好宴游之情。“午橋橋上飲”,已極有情致而愉悅人心,加上“坐中多是豪英”,則更見其游之樂,益發使人憶念。“長溝流月去無聲”,描寫當時宴飲的環境。皎潔、幽雅的月夜,橋下流水載著月波悠然而去,富于詩情畫意。其更動人之處,是上片結句:“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平白至極,又自然至極,堪稱名句,讀之使人倍感親切,似親眼看到一群青年“豪英”在月明花好的杏樹叢中,觀月賞花,吹笛賦詩,一直玩到天明,充滿了歡樂及風流倜儻的情調。對于這樣的“舊游”,怎能不追憶呢?
下片從憶舊游回到眼前,即“夜登小閣”。既憶舊游,則必于眼下情景有感,古人憶昔之作,每多如此。作者這里抒發的是一種深沉的家國之感和身世之感,悵悒的懷鄉之情和深刻的愛國之忱交織在一起。這種情懷,當然與當時社會政治的動亂和個人生活環境的變遷有關。試想,二十多年前,金人南犯,汴洛失守,國破家亡,作者憂國憂民,又挽瀾無力,怎能不感慨萬千呢?正如他在《夜賦》一詩中所說:“腐儒憂平世,況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發滿頭生。”避亂異鄉,有家難歸,憶及舊日與故鄉友好暢游之歡,今舊友星散,故國未復,其心苦楚可知,所以感慨道:“二十余年如一夢”。這一句,不但以時間概念將舊游與現狀聯系起來,使下闋自然地承接上闋,而且以“如一夢”使氣氛驟變,只數字便給人以情調已非之感。避亂以來,“倚杖東南觀百變,傷心云霧隔三川”(《春夜感懷寄席大光》)。“殊俗問津言語異,長年為客路歧難”(《舟行遣興》),“風霜侵游子”(《巴蜀書事》),“無夢到功名”(《道中寒食》),這里“如一夢”。便概括了家國、身世之感。緊接著道出:“此身雖在堪驚!”幾多感慨,幾多悵悒,盡在其中。此兩句是全詞的主題所在。感念故國淪亡,長期不見恢復,語極沉痛,頓使此詞分量增加許多。目前政府偏安江南,國家景況已非疇昔,那么現在夜登小閣,當然不會有舊日夜飲午橋時的興致了,兩相比較,倍覺感傷!“登小閣”前冠一“閑”字,則更見其救國無門、生活無聊之情。悒郁之時,獨自登小閣,幸而看到的卻是晴天,暗示此時南宋政府已以杭州為都城,改名臨安,國家轉危為安,前途已有希望。從這里可看到赤心愛國的作者,對恢復失地并沒有喪失信心。最后以封建士大夫慣有的感慨作結:“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謂古往今來,盛衰往復,國家總是要復興的。和“強弱與興衰,今古莽難平”(《夜賦》)意同。
這首詞因其平易,沒有特別深奧之處,較好理解。詞意清新,語出自然,詞意深沉雋永,平淡里見功夫,膾炙人口,數百年來被人們廣為傳誦。讀者欣賞此詞,不獨愛其清新自然之特點,作為自己寫作時的借鑒,且將受其愛國之情的感染。而增強自己對人生對國家的積極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