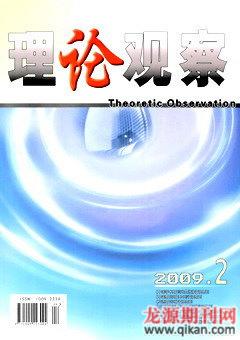“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簡論
鄧雪琳
[摘要]源于西方知識分子理論的“公共知識分子”思潮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必然產物。公共知識分子本身帶有很強政治傾向,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屬于一種立場、一個群體和一個目標,不可能成為“獨立”階級,應辯證應對“公共知識分子”思潮。
[關鍵詞]公共知識分子;思潮;概念
[中圖分類號]D66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2-0063-02
一、公共知識分子的界定
迄今對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界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987年,美國哲學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立足專業,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創作參與社會運轉,并呼吁富有社會責任感,勇于充當引路人。曼海姆認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的共同特點不在利益,而在他們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則使本來來自不同階層的人超越了本階級的利益,從而也超越了本階級的局限,成為不依附于任何階級利益的漂浮群體。根據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理論提出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主張,就是要把知識分子視為超階級的,是公共事務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
吉方平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但在實質上,“公共知識分子”是“獨立”的意見領袖,提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其實質是離間知識分子與黨的關系、和人民大眾的關系。朱蘇力將公共知識分子界定為越出其專業領域經常在公共媒體或論壇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識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的專業知識予以大眾化,并且獲得了一定社會關注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價值中性的經驗的界定。孫立平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有三個特點:理想,批判,分析。馬立誠則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維系著社會的主要價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楊曾憲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是超越專業而關注“公共事務”的人。正像世界上有“好的市場經濟”有“壞的市場經濟”一樣,同一“公共知識分子”概念,也可被注入不同價值內涵。但這并不能成為否定“公共知識分子”存在的理由。他還認為,正因為今天某些以“公共知識分子”面貌出現的人,或為“某些利益集團”張目、或企圖掌控“話語霸權”、或作秀于媒體顯眼于大眾,我們才需要真正以廣大人民利益、以公共利益為己任的公共知識分子站出來,進行揭露或批判,才需要有更多優秀的公共知識分子驅逐那些濫竽充數的學術明星。以中國龐大的人文、社科隊伍而言,今天,真正關心公共事務、獻身公眾利益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著眼于中國改革發展大局,理應大力倡導才是,怎能因一個概念的出處,因幾個人的獨斷言論就將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給扼殺呢!
筆者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是指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背景的知識分子,經常在公共媒體和論壇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
二、“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的緣起與發展
“公共知識分子”問題,從概念到基本觀點,都源于西方的知識分子理論。1894年法國發生了躁動一時的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受人誣陷事件。為伸張正義,法國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在報上刊登抗議書,要求對這一事件復審。這份抗議書被稱為“知識分子的宣言”,認為是現代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對社會公共事務發揮重要作用的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1899年,美國作家維廉,詹姆斯在論及此事件時,提出美國知識分子應保持自身獨立性。保持獨立于體制之外的品格的觀點。后來,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把知識分子界定為掌握文化成果并領導某一文化共同體的群體。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大學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業化,知識分子被一一吸納進現代知識的分工體制和資本主義文化商業體制,公共知識分子在整體上消亡了。1987年,美國哲學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之后,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布迪厄,美國學者薩義德等進一步論述了公共知識分子問題,德國哲學家卡爾,曼海姆系統闡述了知識分子的特征和作用,認為知識分子應是超越本階級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階級之外,并以知識為依托,保持對歷史和社會清醒的分析和判斷的“漫漫長夜的守更人”從而形成了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理論思潮。西方“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的出現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按照西方一些文化學者的觀點,資本主義發展到它的第三個階段多國化公司的資本主義或稱為后期資本主義、后工業資本主義、媒介資本主義、消費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對社會的滲透更深刻,造成了人與人類存在的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劇的疏離,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危機、科學技術的危機、文化危機、價值危機、道德信仰和倫理價值體系的缺失,人的精神世界和人創造的物質世界處于尖銳的矛盾中,文化成為反文化。針對西方社會這種異化現象,“處在黑暗時代”的知識分子為反抗現實推出了“公共知識分子”思潮。
在中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熱”中,涌現了一批社會知名度極高、擁有大量公眾讀者的公共知識分子。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隨著市場社會的出現和國外局勢的變化,知識界內部發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90年代末,一個統一的公共知識界蕩然無存,20世紀70年代出現在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缺失現象在中國開始重演。傳統的公共知識分子死亡了。但是,知識分子憑借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批判反思精神,重構公共知識分子成為可能。
三、理性應對“公共知識分子”思潮
(一)“公共知識分子”思潮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必然產物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各主要發達國家掀起了政府改革運動,即新公共管理運動。改革運動主要涉及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轉變,重視公民參與管理。新公共管理運動的開展,必然會帶來政府職能的縮小和公共領域的擴大,必然會激發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關注社會,針砭時弊,促進社會改良的公共知識分子聲音應運而生。于是就有了1987年美國哲學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最早提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立足專業,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創作參與社會運轉,并呼吁富有社會責任感,勇于充當引路人。越來越多的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現代化的不斷推進,新公共管理運動的開展。必然會帶來公共領域的擴大及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公共知識分子會借助顯性的和潛在的公共領域,適時地用普世性價值標準來衡量執政黨的治國理政實踐,從而以批判的方式間接甚至直接地對社會現實施加影響。因為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開放和民主的治理理念,必然會帶來公共領域的增多和擴大。伴隨著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最適合公共知識分子生存的公民社會及公共領域的出現,就不可避免的
出現公共知識分子思潮。
(二)“公共知識分子”并非“獨立”的階層
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認為,公共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的共同特點不在利益,而在他們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則使本來來自不同階層的人超越了本階級的利益,從而也超越了本階級的局限,成為不依附于任何階級利益的漂浮群體。顯然,這種觀點是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是“漂浮群體”,“不屬于任何集團和階級”。
其實,這種觀點主要是從人格精神方面對公共知識分子的一種描述,而不是從個體生存方面考慮。“公共知識分子”不可能成為“獨立”的群體,因為公共知識分子也是鮮活的人,他們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人性中必然有世俗的一面。在實踐中,人們發現,理想中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的德行與現實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存在著一些差距。很少,能在知識分子個體身上實現完全重疊。
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分子從來不是獨立的階級,而是腦力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階層。公共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一部分,是一個社會階層。公共知識分子本身就帶有很強的政治傾向,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屬于一種立場、一個群體和一個目標。這是由公共知識分子經濟地位上依附性所決定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可能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存在,而只能依附于別的階級。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知識分子必然依附于當時的統治階級并為其服務。例如在奴隸社會為奴隸主服務,在封建社會為地主階級服務,在資本主義社會為資產階級服務。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知識分子應為無產階級服務,并依附于無產階級。作為知識分子一部分的公共知識分子則應依附于無產階級,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三)辯證應對“公共知識分子”思潮
從以上分析可知,“公共知識分子”思潮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必然產物,是被現代國家普遍論定為檢查現實統治是否民主的一個標準。同時,公共知識分子的偏激性、批判性、獨立性、必然會與當下人們的社會實踐產生一定的摩擦和碰撞,有時甚至會因為執政機構的處置不當而使其走向對立面,從而最終變為國家發展的阻力。對于作為追求先進性的執政主體來說,應對公共知識分子問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要切實做到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要始終保持冷靜理性的態度。
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應當以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從更實際的層面把追求公平、正義、公正作為最崇高的社會責任,追求真、善、美。知識分子心中的理想應不再僅僅局限于以意識形態立場作是非判斷,而要關注于追求人類共同文明成果及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從我們黨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提出科學發展觀及構建和諧社會,以及把2007年定為“民生年”的實踐活動中可以看出,我們黨已越來越明確地強化和突出人類一些普遍追求的價值準則,如公平、正義、和諧、友善、穩定、和平、安康,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已和知識分子心中的理想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融合。因此,公共知識分子不但要“以放大鏡看社會”,而且要自覺地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堅持凡是有益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國家和諧,穩定、健康發展的一定要堅持,反之,一定要抵制。
責任編輯:李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