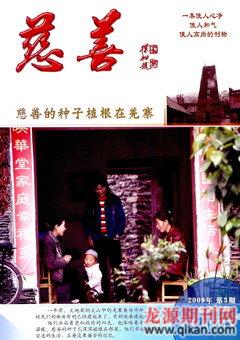古代笑史(之六)
黃 柳
何不出家
吳公留村,任兩廣總督時,揚州吳園次以同譜和舊友的身份來羊城游玩,住在長壽寺中。寺僧叫大汕的,擺設法筵甚為奢侈,而沒有什么真的道力。他知道園次是總督的重要客人,就早晚都來拜見。他常常皺著眉頭談到兩臺對他的頻繁延請、召見,談到與三司應酬之密切,整天都沒有休息的時間。
園次說:“你在這里遭受各種苦惱,何不出家?”
大汕臉紅了,感到慚愧而惶恐,這雖是文人的雅諷,實在可以作為佛門的當頭棒喝。
諸公滾滾
文這公張百熙,未辦大學堂前,明白辭世會有很多障礙,曾召集有關負責人,對他們說:“這學堂能辦好,是‘袞袞諸公不能辦好,是‘諸公滾滾了。”
祭文
有個讀書人去問候某位正在生病的官,走時,將一篇稿子遺忘在座位上。拿起來一看,是預先寫好的祭文。一天,讀書人又去問候一位生病的友人,友人說:“暫且不要放進來,等探明他懷中沒有祭文,我們再相見。”
咄咄逼人
恒玄與殷仲堪談話中間,一起說一些關于了結的話:顧愷之說:“火燒平原,沒有一處不在燃燒。”恒玄說:“白布纏著棺材,豎起了出喪的魂幡。”殷仲堪說:“把魚投入深潭,放鳥自由飛翔。”
接著又說一些形容危險境地的話:恒玄說:“在矛頭上淘米,在劍頭上做飯。”殷仲堪說:“百歲老翁攀在枯枝上。”顧愷之說:“井上一下一下的吊桶里臥著一個嬰兒。”殷仲堪手下的一名參軍也在座,這時說道:“盲人騎著瞎馬,半夜來到深水池旁。”殷仲堪說:“太咄咄逼人了!”原來他正好有一只眼睛是瞎的。
子曰
畢秋帆任陜西巡撫,道經某寺院,停下車來游覽,一個老和尚將他迎進去;畢秋帆問:“你也知道誦經么?”和尚回答曾經誦過。
畢秋帆又問:“一部《法華經》中,有多少句‘阿彌陀佛?”
和尚說:“荒庵老衲,深愧自己生性遲鈍,大人是天上文星,造福全陜,自然素來穎悟,不知一部《四書》中,有多少‘子曰?”
畢秋帆很驚訝,同時深為賞識,于是捐出自己的俸祿,作為香火錢為該廟購置田產,并將寺廟修繕一新。
屠豬貴侯
胡旦這人,文辭敏捷華麗,一時很受推重,晚年患眼疾,閉門在家閑居。
一天,史館官員共同商議為一位貴侯立傳。其人少時職業微賤,曾以屠豬為業。史官們認為,如果不提這段經歷,就不能算是實錄;照實寫出,又很難措辭;于是一起去請教胡旦。
胡旦說:“何不這樣寫:‘某人少時曾操刀以割,顯示自己有“宰”天下之志?”
大家聽了莫不嘆服。
兩個老子
弘治中期,我們鄉中有個豪家子弟,因為犯了法,官府搜捕得很緊,他逃竄,隱匿,不再出現。搜捕的官想盡各種辦法,都未能捉到他,有人說鄉中某老人多智謀,官便把他請來求教。老人請他讓左右退避,方才說道:“要捉的此人,須用《老子》。”官說:“老子已在這里了。”
老人的意思是“欲取先予”的計策:而官所說的是已把犯事的父親拘執在此。老人說:“不是這個老子。”官說:“正是這個老子。”
老人又重復一遍,官始終不懂,就把老人喝退出去,說:“這蠢東西,還說一人有兩個老子,哪里有什么智謀!”
趙鼻涕
臨安縣有個叫趙鼻涕的,因為軟弱無能,所以被起了這個綽號。
有個百姓叫錢德明的,拿著狀紙來告狀。狀上寫著“錢德明年多少歲”,趙發怒,下令對他鞭打。
錢德明不服,趙說:“你欺我,不說今年多少歲,而說明年。為什么?”原來趙把“德”當成名字,而把“明”歸到下句去讀了。
聽到的人不覺捧腹大笑。
鞋匠與樂師
有個制鞋匠,住在一個樂師的隔壁。鞋匠的母親死了,尚未裝殮,樂師仍然練習他的樂器,沒有停下來。鞋匠發怒,以至互相辱罵,訴訟到公堂。樂師說:“這是我的職業,如果不練習,衣食的來源都將失去。”
執政官員判決道:“這是他的本職,怎么可以為了你家的喪事而停下來呢?將來某一天樂師家有了喪事,也任憑你制鞋不停止就行了。”
糊涂加無禮
吏部尚書胡合庵,當年任湖北巡撫時,有下級官僚前來拜見,因某件實情遭到胡的訓責。下級官僚向他請罪,一再稱自己“糊涂該死”。
胡合庵因“糊”字犯了他的名諱,故又說道:“糊涂又加上無禮,此所以應該責備啊!”那人才醒悟過來,人們將此事當成笑柄傳揚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