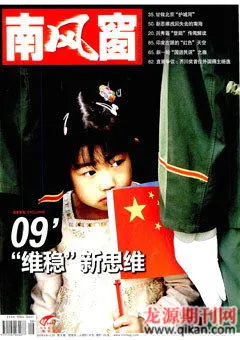土地流轉面面觀
秦 暉 黨國英 葉健民 陳小君 張善貴 李昌平 李 非
自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允許農地承包經營權“多種形式流轉”以來,關于農地流轉的討論有漸成兩級分化之勢。今年全國“兩會”上,吳邦國委員長在工作報告中,將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仲裁法的制定,列入本年的工作重點。3月12日,本刊和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在廣州大學城合辦“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研討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座談和交流。
3月下旬,《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見稿》經媒體披露,有意見認為,其在征地制度改革等核心內容方面沒有根本性變化。根本的利益
秦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現在很多人對地權歸農最大的疑慮,就是害怕農民如果不想賣地就可以不賣。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害怕農民漫天要價,害怕農民成為釘子戶。所以我覺得,土地問題一直就不是所有制的問題,照我看很簡單,土地問題實際就是農民的權利問題。講得更簡單一點,就是人權問題,就是你怎么看待農民的公民權。我經常講,農民問題的出路,要具體地說當然很復雜,但是實際上,無非就是把農民當作一般的公民看待,把農民工當作與市民一樣的產業工人看待,把失業的農民工當作一般的失業工人看待。
除了中國以外,唯一的例子就是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他們就是這么對待黑人勞工的。他們把黑人勞工叫做“流動勞工”,規定黑人勞工在黑人家園里是有土地的,但是這個土地他們不能買賣,是份地,也就是所謂的“土地保障”。他們可以在城里打工,到35歲就回到黑人家園去養老。_旦遇到危機,工廠不要他們了,就把他們趕回去。這種黑人家園集體所有制加上流動勞工制度,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保障了南非經濟的高增長,但最后的結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我認為,這應該成為我們的一面鏡子。
黨國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很多人認為,過去土地是不可以流轉的,中央開了個三中全會后才可以流轉。事實上中國的土地從來就可以流轉,問題是怎么流轉。我們過去的流轉不是市場化的流轉,是政府、國家在那里單向流轉農民的土地,國家過去處置土地是非常隨便的,甚至沒有給農民補償,給農民補償大概才有十來年的時間,這既丟失了公正又丟失了效率。丟失了效率我可以舉個例子,我國城市的土地利用率,大概在全世界是排在后面的,效率非常低。在公平方面,我們應該考慮的是,近10年來國家給農民的征地補償大概不到一萬億,這對農民是非常不公平的。
有人說私有制會造成兩極分化,我們必須消除他的憂慮。從外部的經驗來看,臺灣搞了私有制以后也沒有出現這個問題,政府最頭疼的問題不是兩極分化,反而是兩極不分化。有些人不想放開產權,是對我們的政府管制能力沒有信心,為什么會沒有信心呢?因為中國的體制和西方不一樣,農民的權利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我覺得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們先建成一個民主法制國家再搞土地規劃行不行?我看不行,我們等不及,所以我們還是要搞。
在這種情況下,可行的辦法是進行規模約束。小農在某種情況下,被忽悠把地賣給一個農場,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日本有過法律,對于最大土地經營面積有規定,遺憾的是我們現在沒有這個線,山東、東北、甘肅都有私人圈了很大面積的地,有商人親口跟我說,他在新疆圈了十幾平方公里。我們現在對土地經營的最高規模沒有限制。
另外,關于征地補償費用的問題,我認為應當參照商業用地的價格來定,但是關于補償問題需要法律上的細化。比如:土地的增值是否要歸農民?關于公益性的補償問題,有了市場交易后,公益性占地就可以參照了。
秦暉:我們國家真正的問題就是100多年以前,嚴復講的群已權界的問題。經過了100多年,不但未解決,還越搞越糊涂。公共生活又往往被極少數人所謂的自由意志來支配。公共領域沒有民主,私人領域沒有自由,這是現在很多問題的核心。比如征地拆遷,土地這個公共財產落到某人手里,也不需要大家的同意,當官的想給誰就給誰,這就造成公產私化。公共財產如果要真正有利于全部成員,前提就是應該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怎么減少征地引發的廣泛問題,三中全會提出的思路無非是兩條:一是完善征地制度,二是完善賠償制度,我們要求征地必須要給農民做社保。這些都是中央好的建議,但沒有提到兩個關鍵的問題:基層財政和民主。
為什么現在“賣地”財政這么多?大家都知道現在全國縣級財政的1/3都是來自賣地的,為什么地方政權這么熱衷于賣地?當然貪污腐敗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改革開放后地方政府普遍不夠錢來維持有效管治。有一個數據表明,1986年-1996年地方鄉鎮一級財政每年增長16%左右,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數據,但每年開支增長達25%,就是說收入遠遠跟不上開支。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這變得更加嚴重。
在征地過程里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我們_定要發揚基層民主。現在這個征地賠償的制度本身就很不公平,發展商基本上看中這塊地的商業價值,然后給土地定價,可是農民在這個過程中拿到的補償,是以該土地上過去的農業收益作為計算的基準,中間存在很大的差距,價格怎么定?錢拿回來怎么分?這涉及一個政治信任的問題。我們鄉鎮的干部和政府,是不是真的代表農民的利益來發言?實際上很多地區就因為農民不相信政府是真的為他們爭取利益,就會自發地嘗試很多不同的方式,激化了'社會矛盾。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要保護農民的利益,很基本的一點就是:農民要成立自己的農會。因為農民個體勢單力薄,但有合法的農會制度就不一樣,因為農會可以請非常好的律師打好官司。當然,媒體也起很大的作用。
我認為很基本的一點是:無論是從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還是從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法治的素質問題。即便我們在法律層面上規定農民有權向市場轉讓土地,但法治和公民權利的問題不解決,我們仍然很可能在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看到除市場外還有另兩種力量深深介入農村土地轉讓的過程中,一個是黑勢力,另一個就是濫用權力的官僚。
法律視角
陳小君(中南政法大學副校長):我主持的農地制度立法的調研已經進行了6年,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非常大規模的調研。我們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組織了65人次的5個調查小組,從5月到8月初,對10個省、30個縣、90個鄉、180個村、1800個農戶,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面對面的交流。
根據前期研究,我們認為農地立法的總的指導思想,是以農村土地權利體系的建構為奠基,以切實救濟農民的土地權利的實現為目標。所以,中心思想要圍繞權利體系,權利的運行展開,最終是權利的救濟。
張善貴(廣東同益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
我想著重談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中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其一,股東人數的限制,現行《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規定有50人的上限,在農民人數眾多的現實背景下,必須設計出適宜的利益代表機制。其二,經營權移轉的合法性問題,《土地承包經營法》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夠自由流轉。農民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移轉至公司需要突破法律上的障礙。其三,集體組織及其成員在公司內的角色定位及其各自權利仍存在沖突,需要完善的實施細則予以解決。其四,農民以農地入股后的身份重疊時,《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應該如何適用的問題。其五,農地入股之后有限責任公司遭到清算時,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公司資產用來償還債務,其額度、強度仍需要仔細拿捏。其六,現行諸多法律均架構于市場理念之上,農地入股完全市場化條件尚不成熟,存在一些問題,建議國家制定《農業公司法》,從出資方式、管理機構設置、利益分配、債務承擔分配、存續期間或資產清償等方面對農地入股等形式加以專門規定。
異域經驗
李昌平(三農問題專家):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土地問題,它是一個政治問題,我不認為是個產權問題。在黨中央開三中全會的時候,我在越南。越南在15年以前搞土地改革,它的所有農業制度幾乎都是向中國學的,但唯獨土地制度超越中國:它的土地是可以買賣的,可以兼并的,是可以依法“農轉非”的。在15年前,越南把集體所有制消滅掉了。對于他們的改革,我看了以后心情一次比一次沉重。一個村子的磚瓦廠,打工的農民一個月工資只有80塊錢,但糧價比中國還要高一點。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和土地制度相關。
越南有鄉鎮企業,土地是嚴格管制的,你不能把水稻田隨意用作其他用途,你在農村可以選擇的空間和機會被土地制度給限制了。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越南經常發生水災,水災過后水系怎樣恢復,道路怎樣恢復?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土地已經到戶了,對于這種公共設施的建設問題,怎么辦?所以從去年開始由國家負責這類工程的建設。
第三個年輕人結婚要100平方米的宅基地,100平方米的土地農轉非需要向國家交4萬元人民幣,而他們的工資只有80塊錢一個月。還有利息,如果你用土地去抵押,100塊錢的本金,最后要償還1萬。所以我們從理論上想象出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制不好,私有制好”,我在越南這么長時間,我沒看到私有制優越到哪里去。在越南,由于農村社區共同體的消亡,使得“誰的拳頭大誰就控制”,很多中介工作,只能由他們做,如果其他人插手他們就動手打人。這是我們搞農地流轉必須要警惕的。
李非(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臺灣的三次土改,時空,背景,條件都不一樣。很難和大陸的情況進行比較,所以大陸可以借鑒臺灣的經驗但不能照搬。其實臺灣的農會制度是很成功的,搬到大陸來可能有些地方適用,但絕大多數地方是不適用的。
臺灣農業制度是成熟的。但其與大陸遇到的困難又完全不一樣,所以臺灣的農業制度、農產品制度都可以借鑒,但還不夠,我們要借鑒全世界的經驗。因為大陸和臺灣的發展階段不一樣,臺灣現在已經是后工業化時期了,農業化早就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了。尤其臺灣現在是選舉社會,農民手中有票,這個票不得,我們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