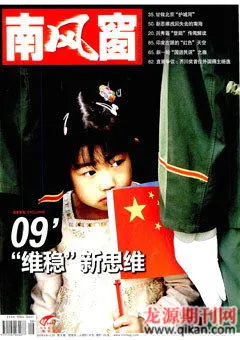直面爭議:芥川獎首位外國得主楊逸
李 瑩
“1989年后,一些西方國家曾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同時也把一些大陸出來的學生抬得很高,可這些人里有的只為了撈取自己的利益,我在《時光》里直接刻畫了這種人物形象。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大家又忙著搭上中國經濟發展這輛車,那些被抬得很高的人于是被甩到一邊,這種時代變遷、世態變化和人生百態,作為小說題材,是我想寫的。”
在日本眾多的文學評獎中,由文藝春秋社的創始人菊池寬于1935年為紀念芥川龍之介而設立的芥川獎具有較高的口碑。翻開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井上靖、遠藤周作、開高健等文學大家均得過芥川獎。2008年,芥川獎139屆的歷史里,頭一回出現了外國人獲獎者——楊逸。
楊逸,原名劉荍,1964年出生于中國哈爾濱。1987年赴日,先在日語學校學習,1991年考進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人學前和日本人結婚,育有小孩。2000年,楊逸提出離婚,孩子隨母,楊逸也沒按日本的常規那樣要求前夫支付贍養費。2002年,楊逸辭去了在日華文媒體的工作,全職教中文。
2005年前后,中日關系進人所謂政冷經熱狀態。楊逸獲獎后回憶她用日語創作的起因時表示:“那個時期,跟我學中義的學生少了很多。學生人數的減少自然影響到收入。我必須認真考慮找一個能夠維持家庭生活的工作,我還要帶小孩,所以這工作最好還能在家里進行。因此,我想到了寫小說。”
楊逸可謂出手不凡,2007年,她的第一部日語處女作《小王》獲得第105屆“文學界”新人獎,且首度被芥川獎提名。2008年,楊逸以《浸著時光的早晨》、以下簡稱《時光》成功問鼎,又因其為芥川獎創辦74年來首位以日語寫作獲獎的外國人作家,故成了日本媒體的關注焦點。然而,楊逸的獲獎及《時光》旋即引發爭議。網上有評論說,2007年是溫家寶總理訪日“融冰之旅”,2008年是胡錦濤總書記訪日“暖春之旅”,加上北京奧運舉辦,因此,文藝春秋社在這個時間點把芥川獎頒給在日中國人作家,未免“太巧合”。也有說,楊逸獲獎只因文藝春秋社要制造外國人首得芥川獎這種熱點話題來推高《文藝春秋》的銷量。
評委村上龍公開表示,反對楊逸獲獎。他認為,與2007年楊逸的提名作品《小王》相比,在日語水平上,《時光》不見有進步,雖然,外國作家首次獲獎的確可稱作芥川獎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但該獎畢竟還需講究日語水平,否則如何面對那些精研日語的作者呢?而從作品內容看,以國際婚姻為題材的《小王》從外部視點有效地觀察描述日本地方社會的具體問題,讓他(指村上龍)讀后獲得不少信息,并引發思考,但有學生事件背景的《時光》卻完全沒有給他這種感受。雖然有評委認為《時光》寫出了1980年代末中國學生的單純,但村上龍認為這不叫單純,而是無知。他認為《時光》并非像某些評委認為的那樣,以大陸的民主化運動史為作品的時間長軸,而恰恰對大陸青年民主化的追求既不關心也無興趣。評委宮本輝和村上龍的意見大致相同,也公開表示不贊同把芥川獎給《時光》。評委之一的石原慎太郎(石原慎太郎曾是一名文學青年,23歲時憑《太陽的季節》獲得第34屆芥川獎,是當時芥川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現長期擔任該獎的評審委員),則先以身體不適為由缺席了該屆芥川獎最后的評選,他后來對媒體爆料,他在選票的三種評價(○△×)中畫了一個△,還說,《時光》不過是部“風俗小說”。
但與此同時,芥川獎評委高樹のぶ子在芥川獎的記者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時光》是保留到最后一輪評選的兩部作品之一,并在最后的投票里獲得超半數的高票,該屆芥川獎共9名評委,除缺席的石原慎太郎,8名評委里有5名畫葉挺。

除了獲獎資格成為焦點之外,日本媒體還關切到大陸傳媒雖普遍報道了楊逸獲獎的消息,卻甚少涉及作品的主題和內容。《時光》究竟寫了什么?楊逸如何看待她的日語創作?3月23日,筆者在東京獨家專訪楊逸。
為了生活
《南風窗》:您曾說過,當初用日語創作是為了生活。那么,在寫小說的時候,要不要考慮日本讀者方面的因素?
楊逸:大多數作家,尤其是有生活壓力的作家,恐怕都會考慮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吸引讀者,有沒有足夠的銷量。不僅僅作者關心,大多數出版社也關心。我有考慮到日本讀者,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們對什么題材感興趣,什么內容才能吸引他們?二是我關心自己的作品能否有別于日本作家。我是個外國人,雖然一定要去磨煉日語水平,但坦率說,到目前為止,相對于日本作家,我在日語表達上沒有優勢。因此,這個階段的創作,我更需要在主題、內容等方面有突出的東西。
《南風窗》:處女作《小王》就是在這種考慮下創作而成的嗎?與您本人的跨國婚姻經歷有關嗎?
楊逸《小王》與我本人的婚姻經歷沒有多大的關系,我到今天還認為,前夫是一個好人。我也曾希望可能的話盡量不要離婚,但緣分盡了就盡了。
作為我的第一部日語作品,寫之前我考慮過,什么內容會和日本讀者拉近聯系?一般的留學生活對日本讀者來說,可能就薄弱點吧?寫中日的國際婚姻,會不會更有意思呢?
《小王》的創作靈感主要源于我在華文媒體工作時聽到的中日婚姻故事。當時,常有嫁到日本各地的中國新娘打電話來報社傾訴她們的生活問題。她們在中國時,有些人學過一點日語,有的完全不懂,對日本的風俗習慣更談不上了解。很多大陸新娘,無非抱著想出國,或者過上好,點的生活的目的,通過國際婚姻介紹認識了后來的丈夫。嫁到日本后,有的因語言不通無法和夫家很好地交流,融不進日本的生活;有的發現在日生活和預想的不一樣,或許也和在中國相親時對方所描述的不大相同,覺得上當了,卻也、無法對丈夫說清感受,又因為怕國內的家人擔心,因此也不敢和家里人明說自己的處境,因此,她們打電話到華文媒體里往往抱著求助心態,一講就很長時間。
我也幫不上什么忙,但至少可以傾聽,多少也從旁開解。可作為旁觀者來看,或許自己在日本也生活了很長時間吧。我很難一邊倒地說誰對誰錯,也能夠理解婚姻雙方的不同立場和做法。我在寫《小王》的時候,固然想寫出這些新娘的生活狀態,同時也努力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更客觀、全面地寫出日本社會對這些新娘的看法和接受程度。這樣的生活和觀察不是一般的日本作者、讀者所能接觸到的,我想把它呈現出來,于是有了《小王》。
紀念青春
《南風窗》:《小王》以國際婚姻為題材,第二部《時光》卻完全是另一題材,有評委還專門提到這個問題,好像認為選您的一個原因在于認可您在一年之內,以題材完全不同的作品來參選,顯示出您的小說創作能力。究竟什么原因讓您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換了創作題材?
楊逸:我是寫小說的,嘗試不同題材不是很自然嗎?《小王》之后,我寫《時光》,
有紀念青春的意思。《小王》2007年得文學界新人獎,2007年下半年獲得芥川獎提名。坦白講,《時光》那么快就在2008年上半年刊出,并且獲獎,是我完全沒有想過的。《時光》很大篇幅寫了大陸青年在中國轉型期20年來的成長故事,我原以為這個小說也許會到2009年才刊登。
1987年,我到日本留學。在日生活和國內完全兩個世界。父親雖然在哈爾濱當教師,但那時哈爾濱的發展剛剛開始,家里生活還是清貧的。我來日后不久就找到兼職工作,白天在語言學校讀書,傍晚5時到第二天8時都在打工,這樣一天約能賺9800日元,日本人嫌這樣的工作太累太便宜,可我當時真覺得就算24小時打工都行。隨著日語水平慢慢提高,我找到的兼職工作也越來越輕松,于是能騰出時間到處看看,所見所聞和國內的大不相同,那是一段我至今懷念的快樂時光。
到日后兩年,也就是1989年,日本媒體經常報道大陸學生的言論和想法等等,這給我很大震動。盡管親友勸阻,我還是在,5月下旬到了北京,就是想親眼看看當時的情況。我接觸到的學生,大都很興奮。那個時候,雖然對民主化是什么,怎樣才能民主化都不很了解,但就是興奮,當時覺得學生這么做好像就能讓中國。下子就強起來。我在北京滯留數日,5月底回到哈爾濱,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以旅游為名,帶著妹妹再次進京。我們乘坐的列車在濟南突然停住了,當時預感到也許發生了什么事情,等我們來到北京后,已經是事件發生幾天后了,回日本前,我把妹妹送上開往哈爾濱的列車,沒想到妹妹感染了傷寒,后來還住進醫院。這段經歷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存在,不是要去做對錯的判斷,我只是希望從中思考,得到些經驗,算是成長的紀念。
回到日本后,我意識到既然來留學,怎么樣也得上大學吧?私立大學學費太貴,我以考國立大學為目標,1991年考上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文教育學部地理學科。從柳田國男等人的作品開始,我開始閱讀地道的日本文學。讀地理,讓我有很多機會到日本各地去參觀、實習。回想起來,這些學習好像都為日后寫作做準備一樣。這種前后關系很奇妙,解釋不了。
《南風窗》:《時光》不僅寫了大陸學生在1980年代末中國社會轉型期里的生活經驗,還寫了不少學生后來出國,切實體驗著外國生活,一方面生活讓他們感受到世間百態,給他們以很大影響;另一方面,2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1997香港回歸,北京成功申奧等大事,透過媒體報道和親朋的介紹,對這些學生乃至海外華人產生了強烈的心理沖擊。您為何要表達這種變化?
楊逸:前面說過了,《時光》是對一段人生經歷的紀念。80年代末,我到過北京,后來國外的一些集會,我也有去看。正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我才能客觀說出所見所聞,也才更能感受到時代變遷、世態變化對人的影響。1989年后,一些西方國家曾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同時也把一些大陸出來的學生抬得很高,可這些人里有的只為了撈取自己的利益,我在《時光》里直接刻畫了這種人物形象。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大家又忙著搭上中國經濟發展這輛車,那些被抬得很高的人于是被甩到一邊,這種時代變遷、世態變化和人生百態,作為小說題材,是我想寫的。
我對一些事情也逐漸有了更深的思考。改革開放之初,一方面國內大力反思“文革”帶來的傷痛,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文化、思潮和技術都涌進來,大家以前看得不夠多,哪見識過這么多東西:一下子消化不了,理解不了為什么外國能產生那么多東西。當時不少人只能解釋,外國之所以出這么多東西,在于他們的制度比較好,在于他們有民主。在這種國內、國際環境的共同影響下,很多學生都希望祖國要改變,希望祖國強大。但怎么變才能更強大?變了以后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強大起來?別人當時有沒有想、怎么想,我不清楚。我當時雖然興奮,對未來充滿憧憬,但怎么才能強大,民主化運動是不是能讓當時的中國一下子強大起來,還真沒有多想。
不過,或許曾經過了一段不短的窮日子,或許是在國外逐漸看多了,漸漸覺得恐怕還是要先發展經濟,讓13億人先吃上飯,保障大家有一個相對安定和平的生活環境吧。民主很好,民主發展當然重要,但它也是不斷發展的吧。所以回過頭來看當時發生的事情和這20年,難免有些想法。作為一名作者,我只能寫自己的,而不可能是別人的想法。
直面爭議
《南風窗》:怎么看芥川獎一些評委對您獲獎的不同意見,以及對《時光》的批評?
楊逸:有不同聲音很正常。一部作品要讓大家喜歡,不容易。我得獎后,有評委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員與我交流過。據相關統計,芥川獎和直木獎推薦的新人在寫作途中的生命力是比較強的,所以評委們都覺得自己的工作相當神圣,因此,整個評選過程非常嚴格、公正。每一位評委必須反復認真閱讀每一部提名作品,還必須具體說出評價的根由。所以,我相信評委們的最后決定。另一方面,一些評委多次閱讀我的作品后,提出批評意見,令我尊重。
《南風窗》:那么,媒體對您得獎的議論呢?說是奧運年讓中國作家首度得獎,太巧合了。
楊逸:作品得到的反應顯然和這種假設性議論不一樣,簡單說來,兩邊都不討好啊,當然我也沒想過要討好哪邊。日本有些反應是,我沒有站在更批判的立場上去批評中國。中國媒體雖然廣泛報道了我得獎的消息,但我的書也還沒在國內出版。至于說文藝春秋社制造話題推銷量,我前面談了,整個評選有著非常嚴格公正的機制,評委和出版社的人都告訴我,這個評選結果不可能由主辦單位或什么人隨意左右。
《南風窗》:您曾經和日本人結婚還生了小孩,為什么沒有加^日本籍?
楊逸:我也有不少好朋友加入日本國籍,每個人有選擇的自由,這點沒什么好說的。我呢,是這么想的,說著~口中國口音很重的日語,對著別人介紹自己是山田,是田中,總覺得沒有必要吧。我和前夫結婚時,也沒按日本人的習慣從夫姓。自己是怎么樣就怎么樣吧,自然就好。
《南風窗》:獲得這么重要的文學獎,成名成家是否讓您的生活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楊逸:不是“家”,還是一個以寫作為生的匠人吧。得獎對我來講是很大鼓勵,但不是我寫小說的終點。還要繼續寫下去,還要考慮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吸引讀者。
不過,今年4月開始,我將在某大學當客員教授,算是讓生活比較穩定,有個基本保障了,也可以有更多時間寫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