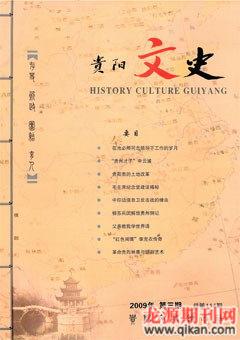貴陽市的土地改革
郝承先
從農業合作化開始,我長期在中共花溪區委工作。1982年調市農辦至1996年退休。因此,對包產到戶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有關文件資料,將這段歷史反映出來,可能不一定全面準確,權當拋磚引玉,供有興趣的同志作進一步探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遭到挫折
解放后貴筑縣(1958年劃歸貴陽市后分為烏當、花溪兩個區)廣大農民翻身做了主人。經過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積極響應黨的號召,走互助合作道路。1952年,全縣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5101個,人社農戶占總農戶的74.7%。1953年,黨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全縣試辦58個初級農業合作社(土地入股按勞分配),人社農戶占總農戶的3.4%。1954年,在試辦54個高級社陬消土地股,完全按勞分配)的同時,初級社發展到132個,人社農戶占總農戶的11%。1955年秋,在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引下,批判“小腳女人”,全縣農業合作化運動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1956年春,入社農戶達到農戶總數的95%以上,其中:高級社57個,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79%,初級社109個,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16.15%。一年時間人社農戶增長7.6倍。應當肯定《合作化道路是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大方向是正確的,試辦初級社也是社社增產的。問題是后來急于求成,工作粗糙,經營形式單一。高級社還未站穩腳根,1958年又掀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大搞“一平二調”,刮起一股強烈的共產風,嚴重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很大破壞,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主要農副產品大幅度減產,出現了全國性的糧食副食品危機。據市統計局資料,全市1961年糧食總產量17.06萬噸,比1957年的29.52萬噸減少42.2%,比1949年減少9.7%。油料1850噸,比1957年的4269噸減少56.6%。一些農戶因長期缺糧,營養不良,出現了“浮腫病”,有的地方甚至餓死人。
針對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和出現的困難,黨中央自1960年冬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調整農村政策,動員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先后制定了《關于發展農業的十二條》、《人民公社工作條例60條》和《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逐步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并進行退賠,由生產大隊向生產隊實行三包一獎(包工分、包產量、包投資、超產獎勵)和四固定(固定土地、勞力、耕牛、農具)的管理辦法。1962年修改的《60條》,進一步明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從而基本結束了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但是戶與戶之間平均主義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
包干到戶應運而生道路艱辛
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克服眼前困難,區委號召大種蔬菜,大搞瓜菜代,每天按5:5:2的比例安排群眾生活(即5兩糧食,5兩代食品,2斤蔬菜)。農民為了吃飽飯,在生產大隊推行“三包一獎”“四固定”,有的生產隊又對農民定土地、定產量,包完成公余糧任務、包完成農副產品交售任務、包完成上交提留的兩定三包責任制,實際上就是包干到戶。有些邊遠生產隊的農民要回入社的田土自己耕種。1961年,省委召開“三干會”期間,時任馬林公社書記的楊應林,曾總結牛鼻箐生產隊包產到戶的“十大好處”,打印10多份送區委辦公室轉省三干會。我看后認為與當時政策相悖,不宜擴散,征得他的同意,除將一份送參加會議的區委主要領導外,其余存區委辦公室。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把包產到戶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單干風加以批判。各級都組織工作組深入農村糾正包產到戶。由于農民嘗到了包產到戶的甜頭,工作組雖然做了大量工作,結果是這邊糾,那邊搞,工作組在糾,工作組走搞,明糾暗不糾,總是糾不徹底。到1965年“四清”時,中央工作團認為花溪區的單干、半單干(包產到組)的生產隊達30%。此數雖有夸大,但單干、半單干確實存在。因此,從“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從沒有停止過糾正單干、半單干的工作。
粉碎“四人幫”后,1978年11月11日《貴州日報》加編者按發表《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行之有效》兩篇報導,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紛紛效仿,有的搞包產到組,有的又恢復包產到戶。1979年春,我到麥平公社。公社書記反映:杉木一、二大隊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合并為一個生產大隊并實行大隊核算,現在他們要求分回原來的兩個大隊并實行生產隊核算,公社多次做工作,群眾還是要求分。我調查兩個大隊并隊前后的生產、分配情況后,召集大隊干部和黨員到公社開會,發給每人一份調查表,內容是維持現狀堅持下去,分回原來的兩個大隊,實行大隊核算,實行生產隊核算,由黨員干部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意的打、/,結果除一人在調查表上寫“前進方向不明”外,其余的人都同意分回原生產大隊并實行生產隊核算。看到這個結果,公社同志問:“我們學大寨搞大隊核算是不是搞錯了?”我說,過去學大寨強調“一大二公”,干部、群眾要求并隊搞大隊核算,我們支持是對的:經過實踐。隊大了不便管理,糧食減產了,原來兩個大隊人均占有耕地數量不一,在分配上有平均主義,現在群眾要求分回原來的生產大隊并實行生產隊核算,符合“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策,我們支持也是對的。公社書記說:就按郝書記的意見。其實他們也是同意分隊的,只是怕犯“四清”“文革”時批判的“右傾”“倒退”錯誤讓我表態罷了。
同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的人民來信,編者加了一段按語,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應充分肯定,不能隨意變動,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干到組的地方,應當堅決糾正”。與貴州日報的編者按《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的導向完全相反。市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貫徹人民日報編者按精神,當我匯報杉木大隊情況時,市委書記夏頁文嚴肅指出:“過去(‘四清前)你們分隊,現在還分隊,回去要堅決糾正”。我解釋不是分隊,是在農業學大寨時兩個大隊合并為一個大隊現在要求分回原來的大隊,對其他鬧分隊的我們堅決糾正,只對個別“四清”時合并又居住分散的隊作適當調整。夏書記說“要做好工作,不能一陣風”。
1980年1月,區委經過調查研究,制定了《關于進一步落實農村經濟政策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左”的影響仍是我們
迅速發展農業生產,活躍農村經濟的主要障礙,必須解放思想,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切實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因隊制宜實際包產到組、包干到戶等靈活多樣的管理形式。得到省委副書記、市委第一書記徐健生的肯定和支持。2月8日市委將這個意見轉發各區“參照執行”,使“雙包”責任制得以公開化,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歡迎。但有少數干部擔心包干到戶以后“干部難當”“不好領導”,有的甚至認為是倒退,“辛辛苦苦30年,一朝退到解放前”。多數干部認為:只要堅持土地歸生產隊集體所有,社員只有使用權,不能買賣出租,也不能改作他用,就是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雖然認識不統一,卻沒有影響改革的進展。7月13日市委發出《關于貫徹執行省委(關于放寬農業政策的指示)的意見》,允許實行包產到戶,擴大生產隊經營范圍。于是“雙包”責任制在全市糧區迅速鋪開,這一年全市有74%的生產隊實行了包干到戶的責任制。
1981年7月,市委、市革委又制定了《關于蔬菜社隊實行“雙包”責任制若干規定》,年底,全市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99.4%。1982年中央1號文件給包干到戶、包產到戶上了社會主義的戶口,稱它“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責任制”。1983年中央l號文件認為包干到戶“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以后中央文件進一步肯定“一定要作為農村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加以完善”。從此,“恐右癥”、“怕倒退”等疑慮也就煙消云散了。
從1982年起,全市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工作進入穩定和完善階段。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有關指示精神,一面抓處理包干到戶的遺留問題和出現的新問題。如:堅決制止亂占濫用耕地、亂砍山林、強占折分集體財產,整頓社隊財務、推行承包合同、購銷合同和農業技術聯產承包合同;一面把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農業向林、牧、副、漁業,水利、農機、社隊企業和國營農林牧場推進。全市小(二)型以上水利工程516處,建立了各種管護責任制的占95.7%。大中型農機具693臺(件),實行各種承包責任制的占90%,社隊企業914個,推行多種經營責任制的占88.2%,3045個有林業“三定”任務的生產隊,通過驗收補課,增劃自留地13.4萬畝,責任山18.9萬畝,不僅維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還為開發利用荒山、草坡,加速林牧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簽訂土地承包合同的具體作法
明確土地承包關系,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是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搞好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基礎。其基本作法是:在維護土地歸生產隊集體所有的大前提下,以生產隊為單位,將集體耕種的土地,按人口平均的數量,聯系產量承包到戶。農戶對承包的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不準買賣或出租,不準擅自用于建房或改作他用。在進行土地承包中,按當時的合法人口,人人有份,對現役軍人一律按田土份額和承包任務劃交給戶。承包土地的劃分不準繼祖業,盡可能做到好壞搭配,遠近搭配,相對聯片,方便生產,落實到戶。具體辦法由群眾民主議定。在執行中,多數生產隊采取拈鬮的辦法,個別邊遠隊分回入社時的田土。土地承包期限宜長不宜短,一般以15-20年為限,以利于群眾長期打算,精耕細作,培肥地力。
在此基礎上,由生產隊對農戶實行三包,即包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包完成生豬、禽蛋、辣椒等農副產品交售任務,包完成各項上交提留,以解決烈軍屬、五保戶、干部報酬等開支。以上的內容均列入承包合同,一式三份,簽字劃押,公社、大隊、社員各存一份。社員完成包干任務后,收多得多,收少得少。這樣既避免了包產獎賠等煩瑣程序,又兼顧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
群眾之所以喜愛包干到戶的形式,用他們的話說:一是能增產增收,“這辦法,那辦法,能增產增收就是好辦法”。同是一塊田,包干到戶后精耕細作,增施肥料,比包干前要多收幾挑谷子。二是干活自由,能適時播種、管理、收割,特別是農忙季節,一家老小起早摸黑干,心里很高興。他們說:“感謝鄧伯伯,我們兩頭黑,雖然辛苦點,做來自家得”。三是避免無效勞動。過去“出工等敲鐘,干活一窩蜂”出工不出力。秋收時,糧食收下來挑到曬壩要秤一次,收完會計算帳分到戶又要秤一次,分一次糧食要搞到深更半夜。包干到戶后,各家收了往各家挑,減少了好多麻煩。四是各種‘能工巧匠經營能手的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出現了一批重點戶、專業戶,為建立生產基地,實行產業化經營創造了條件。五是群眾對干部的意見少了。過去統一核算,有的生產隊帳目不清,分配沒有兌現,加上有的干部多吃多占,借支挪用,多記工分等,社員對干部意見紛紛。包干到戶后這些問題就避免了,從而密切了干群關系。
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雙層經營體制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1983年3月7日,市委召開區書會議,討論人民公社政社分設問題,聽取中曹公社政社分設試點情況的匯報,形成會議紀要。決定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
鄉的規模,原則上以現有公社范圍建立鄉人民政府,少數規模過大,與經濟區域不一致,和交通不便的公社,規模可以適當劃小。鄉政府是國家在農村的基層政權機關,除負擔民政、公安、司法、文教衛生、計劃生育等方面工作外,還要領導經濟工作。
村民委員會的設置,一般以現有大隊建村,成立村民委員會。現有大隊規模過小的,可以合并;個別規模過大的,也可以適當劃小。村民委員會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在村黨支部和鄉政府領導下開展工作。村民委員會下設村民小組,村民小組以自然村或現有生產隊建立。經過調整,全市31個公社,378個行政村,2676個村民小組。
同時,建立了一批以土地公有,戶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為特征的鄉村合作經濟組織。鄉建立農工商聯合公司。
村由村民委員會兼管經濟。他們通過土地發包,管理農業承包合同,從服務工作人手,搞好管理協調,幫助農民解決一家一戶辦不了、辦不好、辦起來不劃算的事情,如水利灌溉、病蟲防治、供應良種化肥農藥等。有的村還圍繞服務辦經濟實體,辦好經濟實體促服務。隨著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各種協會(蔬菜、養豬、養雞、辣椒、烤一煙、農機等)應運而生,為農民提供信息、技術、運銷等服務。有的村利用荒山草坡資源,實行統一規劃,集體所有,分戶經營,收益分成的管理辦法,既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發展壯大了集體經濟。
實踐證明,把家庭承包經營的形式引入集體經濟,建立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完全適應農業生產特點和當前生產力發展現狀,有很大的靈活性,能容納農村不同程度的生產力,是促進農業發展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