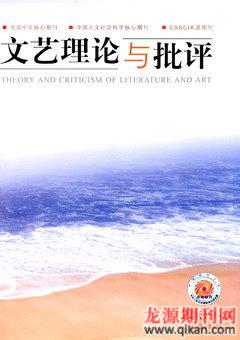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性傳承及保護
李秀清
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大的特點是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顯現。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并以身口相傳作為文化鏈而得以延續。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地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二胡在我國眾多民族樂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二胡音樂也具有非常濃厚的地域特色,它取決于當地的自然環境,經濟基礎,民間習俗和文化傳統等。而人又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生存發展的,音樂的創作和欣賞都離不開人具體的思想感情。因此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來說,二胡演奏者的傳承就顯得尤為重要。20世紀初至今,二胡演奏藝術在眾多二胡音樂家的努力下,發展出不同流派且初具規模。細膩、甜美風韻演奏風格的南派,粗獷、爽朗性格而在演奏中比較注重運弓功力的北派,富有秦腔、眉戶戲等戲曲特色的秦派和獨具特色風韻的豫派等都是在特殊的人文社會環境里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而且異彩紛呈。正因為如此,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性角度來加強對二胡音樂的傳承與保護意義是重大的。現以南北派為例,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南派二胡音樂的地域性傳承與保護
南派二胡音樂發源流行于長江三角區,江、浙、上海一帶。江南水域面積遼闊,江河縱橫,是全國有名的“水鄉”,有十分密集的水運網。地形以平原和低山丘陵為主,地勢低平,鐵路、公路等交通方式也十分便捷。這里是我國交通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人口流動性大,內外文化交流頻繁,使得江南二胡藝術加工的成分比較多,表現出細膩、含蓄、精致的音樂性格。江南地理位置優越、物產豐富、人們生活富足,這些造就了江南人性格中的啟信和滿足。江南人的生存狀態是和諧的,他們始終處于比較充實、安定的生活狀態,帶有享受的心理。所以江南二胡音樂更多的表現出從容、悠閑和平靜,但也有表現激情奔放的樂曲。
南派二胡音樂發展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它是江南音樂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江南音樂的特點正如《中國民族民間器樂集成·江蘇卷》所歸納的:花、細、輕、小、活。“花”即華彩;“細”即細膩;“輕”為輕快;“小”即小型;“活”即活動。南派二胡繼承了這些特點,具體表現在演奏上節奏平穩和節拍均勻,在速度上很少出現大起大落和對比轉換,在整體上感覺柔和缺乏棱角,使演奏者和欣賞者產生涵養性情、愜意放松的感覺。
在創作方面,從南派二胡音樂藝術家劉天華重視國樂、改進國樂、發展國樂之初起,他手中的二胡就是有感而發,有思而作的,如光明行十首二胡曲等。他的貢獻主要在于通過創作、演奏和教學實踐,把民間的二胡帶進高等學府講壇,推向專業音樂舞臺,提高了二胡的文化品位,正是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域性特點使二胡音樂的傳承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南派二胡藝術家中,生活于清末至共和國初期的江南民間藝人華彥鈞,是二胡藝術傳播者的杰出代表。在阿炳的代表作中,《二泉映月》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該曲采用江蘇民間音樂材料寫成,運用多種二胡弓法和不同力度的變化,細致地表現了飽嘗生活艱辛的社會底層人們悲愴的心情和倔強性格,在近代新生的民間器樂曲中是極富創造性的。”阿炳的音樂修養最主要的基礎來源于道家的音樂,阿炳從小生活在道觀里,自幼從道習樂,他在道觀生活了30年,對道家音樂、民間音樂等有“相當廣泛而且相當深刻的修養。”(楊蔭瀏,音樂出版社1956年版《瞎子阿炳曲集》)。阿炳的生活環境為他的音樂生活構筑了典型的道家文化的氛圍。中國傳統的詩、樂、書、畫所共有的道家藝術精神,也是阿炳音樂的精髓所在。他的音樂富有民間氣息,他的生活經歷和生活環境影響著他的感情,這一切都在他的音樂技藝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阿炳的音樂修養、人生際遇和道家藝術精神共同影響著他二胡作品的創作,他的二胡音樂意蘊和二胡音樂家的文化品格,都具體體現了國樂文化的中國特色。
劉天華和阿炳是推動二胡藝術發展的重要力量。二胡藝術在阿炳、孫文明生活的20世紀上半葉達到發展的頂峰。在阿炳和孫文明之后,民間二胡逐漸走向衰微,他們的二胡音樂由職業二胡藝術家繼承和發展,如王乙教授、二胡演奏家閔惠芬等。民間二胡傳統音樂直到20世紀80年代被城市音樂文化沖擊而喪失發展空間之前,仍是江南職業二胡藝術家們的“搖籃”。
南派二胡音樂在地域上長期受江南音樂文化熏陶,無數二胡藝術家在自然狀態下經過一代代傳承,已經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實屬不易。在二胡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江南二胡藝術家所作的貢獻無疑是最大的。在二胡藝術發展早期,具有濃郁江南意蘊的二胡作品成為將二胡藝術推廣至全國的主要傳播內容。在20世紀下半葉,江南音樂風格的二胡作品則以其柔美、細膩、精致、優雅的地域性藝術特征成為二胡藝術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二、北派二胡音樂的地域性傳承與保護
北派二胡音樂的演奏風格具有粗獷、爽朗的性格,在演奏上比較注重運弓的功力。自20世紀60年代起,一批二胡演奏家和教育家在二胡傳統演奏法的基礎上,大膽地吸收了西洋弦樂器的一些演奏特點,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演奏規范,現為各藝術院校的二胡專業教學所認可。其代表曲目有《三門峽暢想曲》、《長城隨想》等。北派演奏的作品不僅在藝術上漸漸形成“北派風格”,而且刻意于思想性、民族性、藝術性、時代性的有機統一,聽起來與人們的心靈是那樣貼近,那樣融通,那樣的感人肺腑。比如,北派的典型傳承人宋飛在“紀念劉天華一百周年誕辰—北派二胡獨奏音樂會”上演奏的《二泉映月》,是未經刪剪的阿炳的原版,結構上反復多,沒有足夠的功力很難被聽眾認可。但宋飛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神韻有獨到領悟,每一次反復都有獨到處理。宋飛認為,二胡的表現力要適度、貼切和有分寸,讓大家感受到深層的含蓄情感。過去對《二泉映月》的山光水影的注釋是不貼切的,某些演奏家的演奏,囿于成見,沿襲舊說,人云亦云,過多地流露阿炳的苦難與悲慘,而聽了宋飛的《二泉映月》能夠感受到阿炳的性格倔強、精神不敗、骨氣凜然,有一種奮發向上、直面人生的軒宇之氣。宋飛的《二泉映月》闡幽發微,言前人之所未言,發前人之所未發,極富創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國傳統音樂美學觀,宋飛把握適度,其實就像鹽溶于水,化得無跡而其味雋永。
從地域性的角度來看,宋飛在處理北派與南派的關系上,做到了兼容并蓄,融會貫通,“吸取精華,去其糟粕”。所以,宋飛奏出的作品既有北國大漠落日、燕山峻嶺、草原奔馬的古樸豪放,又有江南絲竹、小橋流水、杏花春雨的婉約風流,同時還有鮮明的時代精神。例如她與姐姐宋月合奏的《慢三六》,既繼承了民間支聲的優點,又汲取了西洋的復調手法,聽起來感情真摯細膩,音樂清新秀麗,音色柔美和諧,不乏北國風采,更有江南水鄉的旖旎,使人很容易進人“云銷雨霧,彩徹區明”的境界。1998年8月15日宋飛在北京音樂廳舉辦的“胡琴漫話”二胡獨奏音樂會上,演奏的《聽松》、《獨弦操》、《道拉基》、《春野》、《芽》、《一枝花》等作品,是宋飛探索二胡演奏藝術升華的又一重要標志,較好地演釋了宋氏琴韻的個性及北派的特點。無論是宛如小溪潺潺般的細潤,還是猶如江河奔騰般的壯觀,或蘊涵溫文爾雅,或激蕩著雄渾,都令人神往與流連。北派還有許多出色的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如:劉文金、甘柏林、劉長福、唐毓斌、宋國生、趙寒陽、印再深等。
總之,從地域性的角度來恭聽北派的音樂,切實感受到北派的歷史文化知識豐富,音樂理論功底扎實,生活體驗深厚,北派的二胡演奏具有深刻、大氣、永恒、端莊魅力的重要基礎所在。
從地域性的角度來看,秦派和豫派二胡的演奏技法也有獨到之處,例如豫劇板胡的快速抹指、墜胡中的大滑,豫劇四三拍的“強、弱、強”,這都是組成河南二胡流派的要素。
三、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地域性理論重新確立二胡音樂的傳承與保護
要保護我國地域性二胡音樂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加強宣傳,增強全民族保護意識;在不同地區有典型文化特征和優良傳統的地方,建立專門組織機構和場所,發現并有計劃地培養優秀二胡音樂人才;定期或不定期組織、舉辦活動,以推動交流,提高水平。例如,由中國音樂家協會和江蘇無錫江陰市人民政府舉辦的四年一屆的“天華杯”全國二胡比賽,吸引了全國各地二胡高手比賽、交流技藝。由中國音樂家協會和江蘇徐州市人民政府不定期舉辦的徐州國際胡琴節等都是成功的范例。
中國幅員遼闊,地域文化特色鮮明,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二胡音樂因地域不同而異彩紛呈。隨著我們國力的增強,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在理論和實踐上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地域性研究與保護,那么包括二胡音樂在內的一個品種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定會得到適當和更和好的傳承與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