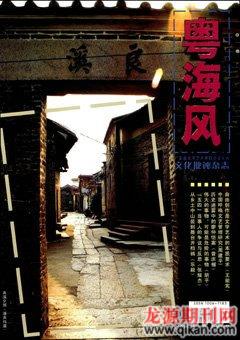新民歌運動:“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
巫洪亮
如今,“底層寫作”已成為學界一個聚訟紛紜的話題。人們常常借助中國“左翼文學”的話語資源,探討“底層寫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相關的問題。在“十七年”文學中,“工農創作”被認為是“底層寫作”的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實驗,它有力地推動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生成和發展。尤其是“新民歌運動”中大規模的“工農創作”,不僅使“代言者”(知識分子)自覺以“工農”姿態展開想象,同時也使“工農”這群“文藝新軍”學會了如何表述“自我”。這場“文化翻身”運動,旨在“解放”底層的“工農”,讓這一“弱勢群體”在政治、經濟“翻身”的同時,實現“文化翻身”。“工農”的“文化翻身”,其實并非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的“神話”,它既有“真實”的一面,也有“虛幻”的一面;既是一種“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那么,這種“可能”和“限度”是什么?它包括哪些方面的要素?為什么存在這些“可能”和“限度”?在這里,我們以1958年“新民歌創作運動”中的“工農創作”現象為例,努力解開上述問題所形成的層層“疑團”,揭示“工農”“文化翻身”的復雜性。
一
人們這樣描述“新民歌運動”中的“民間詩人和歌手”的“文化翻身”:他們“原來大多數是不識字的群眾,確實是‘連一封普通信都寫不明的,因為舊制度把他們壓榨得只剩了一口氣。可是社會主義社會卻使他們恢復了青春,給予了他們在文藝的太空中飛翔的翅膀。他們用拿鋤頭的手,開動機器的手,握起了文藝的筆,高歌猛唱,描繪祖國的大好春天,成為社會主義時代的新詩人”。[1]這里,“工農群眾”從“不識字”(文盲)到“握起文藝的筆”(詩人);從“一封普通信都寫不明”(無法表述)到“在文藝的太空中飛翔”(“自由表述”);從“壓榨得只剩下一口氣”(“沉默”)到“高歌猛唱”(“放歌”)。這種“過去——現在”對比式的敘述,以強有力的邏輯說明了“社會主義”、“革命”完全“解放”工農“才智”和“束縛”,“工農”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文化翻身”。諸如此類的“文化翻身”的敘事文本,不僅僅在知識分子筆下不斷涌現,同時還在“工農”的自我講述中不斷重復。這種現象引發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工農”在“新民歌創作”中獲得的感受都是“虛幻”的嗎?如果是,難道“工農”這一龐大的群體的感受都出了問題?顯然,事實并非如此,“工農”的“文化翻身”有其“真實”的層面,這些“真實”的側面,型構了“工農”的“文化翻身”之感。
首先,從“無權說”到“有權說”。“五四”以來,“底層的民眾”因其文化知識和精神擁有的匱乏,往往處于現代文明的邊緣位置。在整個社會的話語層中,他們的聲音不斷受到統治階級的監控、壓制、同化與剝奪,不斷被權力話語所肆意篡改。也就是,他們“無權”以自己的話語方式,參與到現代文明的建構之中。這正如魯迅筆下的阿Q,生活在未經現代文明徹底洗禮的未莊中,身上具有愚昧、麻木、狹隘、自私等“劣根性”,在統治者看來,像阿Q這樣有“劣根性”的“貧民”,他的生存權、話語權、戀愛權、性權等等是可以隨意剝奪的,而且也必須剝奪。這種失去了“話語權”的底層民眾,通常被認為是“沉默的大多數”。在這種情勢中,知識分子出于人道主義關懷或受特定時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從忍辱負重且默默前行的底層民眾身上,發現了許多“有意味”的時代話題,并樂于為底層民眾“代言”。然而,在“代言”的過程中,由于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之間形成了兩套話語系統,“代言者”和“代言對象”之間存在難以消除的隔膜,底層的聲音要么被知識分子誤讀,要么在無形中被改寫。某種程度上,“代言”知識分子贏得了底層民眾的“言說權”,因為在知識分子看來,底層的聲音未經他們的轉譯和提升,是模糊、嘈雜、膚淺的,難登上大雅之堂,難以匯入總體歷史和時代潮流之中。總之,無論是專制的統治階級也好,還是富有良知和正義的知識分子也罷,他們認為的底層“不應”獲得和“不能”實現“言說權”,于是,底層民眾只好轉入自身內在的話語系統中,進行鎖閉式的交流。比如,在“新民歌運動”中,一些底層的“工農”詩人說,在“舊社會”“二十年的童養媳生活,折磨得我逢人講不了三句話”[2],為了編“順口溜”,“受到當地的鄉紳和地主們的逼迫”[3],“窮人要想說心里話,就是那樣不容易;窮人愛聽的聽不到,我們要唱給窮人聽,也不敢大膽地唱”[4]。1942年《講話》以降,“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成為知識分子必須承擔的文化使命。“共和國”成立之后,一系列的文化批判和政治運動,使知識分子的思想、立場、趣味等等實現了艱難且有效的轉換。雖然他們不乏真誠地去體驗、揣摩、把捉“工農兵”的思想情感,但是“知識分子并未真正地刪除內心的小資產階級王國,相反,小資產階級烙印頑強而又隱秘地戳在他們所提供的文本之中”[5]。在毛澤東看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如何讓“工農兵”這些“卑賤者”“敢說敢想敢做、破除迷信”,走向文化的前臺,獲得文化“言說權”,成為他始終關注的問題。于是,1958年他發起了一場全國規模的收集民歌和寫民歌的“新民歌運動”。在這場詩歌運動中,不但創作者和接受者發生了變化:“民間歌手和知識分子詩人之間的界限將會逐漸消失”,“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所共賞”[6],而且創作的內容也實現了更新:“新民歌不再是勞動人民被剝削的痛苦的反映,也不再是小生產者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心理和習慣的反映”[7],而是“工人、農民在車間或田頭的政治鼓動詩,它們是生產斗爭的武器,又是勞動群眾自我創作、自我欣賞的藝術品”[8]。同時,“工農”的政治文化地位不斷得到提升:有人曾感嘆道,“舊社會我是下等人”,如今“是排長,還是全市婦女積極分子,跟首長平起平坐,好多領導、有學問的人,都來訪問咱,稱咱是農民詩人”。可以說,“新民歌創作”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工農”文化奪權的運動。這里,底層民眾“言說史”經歷了“不能說”(受壓迫)到“別人替自己說”(代言)再到“自己說”(言說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再到“有尊嚴地說”(受尊重)一系列的變化過程。于是,在這場詩歌運動中,“幾千年來被壓抑、蹂躪和窒息的人民群眾的潛力,爆發出來了,勢如銀河倒瀉,不可遏止”[9],他們身處文化奪權的時代漩渦里,體驗著前所未有的“文化翻身”的快感。
其次,從“無法說”到“學會說”。在國家權力的運作下,“工農”被推向文化的中心舞臺。當言說的空間向“工農”敞開之時,他們卻遭遇到“無法說”的問題。對于絕大多數的“工農”而言,他們都是“文盲”、“半文盲”:“解放十年來,黨對我的關懷無微不至,滿肚子的話,提起筆來,又不知從哪說起”[10],“我原來實際上還是個文盲”,“拿起筆寫東西,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文化問題”[11],為此,1950年,一場從政府機關開始,面向全國,“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廣泛地開展起來。其實,從某種角度上說,“新民歌”創作運動也是“群眾”“識字掃盲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化程度本來就很低”,“搞創作很困難”的“工農”詩人,為了克服這些“困難”他們“就下決心學習文化”[12],從而自覺自愿地實現了自我的“文化掃盲”。這樣,底層民眾從文盲、半文盲到識字,再到參與文化生產,逐漸擺脫了“無法說”的困境。他們從唯有“沉默”到放聲“歌唱”不能不說是一種“解放”。當然,在“新民歌運動”中,掃盲后的“工農”詩人還必須“學會說”,即學會“說什么”及“如何說”。有組織的理論學習和文化實踐活動是他們“學會說”的重要保證,這一點下文將予以詳述。有趣的是,“工農詩人”這種“學會說”沒有真正贏得“話語權”,為什么也能產生“文化翻身”之感呢?這是因為,“工農” 詩人利用、改造清新、活潑的傳統民歌,學會創作“新民歌”能實現自身的價值。“新民歌”創作不僅是“工農”詩人展示自我的“精神符碼”,同時也是他們實現自我價值的生存之道。“新民歌”所涌動的人們的“沖天干勁”,所謳歌的英明的領袖,所表達的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勇氣和決心,所描繪的 “共產主義”的美好藍圖等等,可以充分展現這些“新民歌”的“新力軍”文化精神面貌,以及時代“弄潮兒”的自豪感,改寫現代以來那種“愚昧、麻木、落后”的形象。可以說,在“工農”看來,正是“文化翻身”才刷新他們既有的“精神”和“形象”。另外,“學會說”讓他們實現了由“工農”到“詩人”的身份轉變的夢想,從而使他們有資格參加各種文化演出以及創作交流會,并可以得到政府的獎勵,甚至到大學講課(傳授經驗)。總之,隨著“民間歌謠”的無價值到“新民歌”有價值的變化,以及“新民歌”不斷價值化,“學會說”使“工農”詩人逐漸產生一種由詩歌“價值翻身”帶來的“文化翻身”之感。說白了,這種“解放”之感既源于詩歌之外,又存在于詩歌之中。
再次,從“不敢說”到“大膽說”。在“新民歌運動”發起之初,許多“工農”心中普遍存在這樣的觀念:“認為寫詩作文是文人干的事,工人農民斗字不認識幾個,如何能夠寫詩”;“認為唱民歌是不正派”[13]。這種觀念反映了“工農”對“寫詩作文”這一“文人”職業的敬畏,以及對“民間文化”和自身文化擁有的不自信。產生這種現象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等級差異。可以說,由于不同文化群體擁有的文化“言說權”的差異,出現了文化的分層。雖然不同文化層內部有各自的系統和結構,但是不同層級間文化系統和結構之間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等級關系,這種“等級關系”隨著時代主潮的嬗變而發生“錯動”。在中國現代文學生成和發展中,“精英文化”占據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民間文化”常常作為需要“重塑”的文化對象而被邊緣化。在人們的意識世界里,“精英文化”背后總是閃耀著“深奧”、“精致”、“品味”、“優秀”的光輝,“民間文化”跟隨太多諸如“淺顯”、“粗糙”、“低劣”、“愚昧”、“落后”的影子。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民間文化”自身的保守性和自足性,使得它難以和“精英文化”一樣,有效吸納現代化的文化因子,以獨特的形式,深邃的內涵,旺盛的生命力加入時代文化的重構之中,因而在歷史文化總體架構中,“民間文化”一般潛入“底層”,在村落、街頭,在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中延續生命。更重要的是,在現代化的教育體制中,知識分子接受的大多是“精英文化”教育,這使他們養成了“精英”審美趣味和眼光,并習慣以此標準去審視“民間文化”,而且很大程度上不愿意加入到這一文化的建構之中。這樣一來,“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就生成了一種文化“區隔”。深受“民間文化”濡染的底層民眾,即便在自身文化的話語系統中自由穿梭,達到游刃有余的程度,一旦面對“精英文化”時他們常常“失語”,并且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自卑”情結。因而當這種等級結構未出現新變時,底層民眾“不敢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現代新詩“大眾化”運動未能使詩歌真正抵達“底層”。綜觀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歷次新詩“大眾化”運動,不難發現,詩歌常被作為一種“運動”群眾,實現“革命”的工具,其實很難真正傳達底層的“聲音”。對于底層民眾來說,民間歌謠“難登大雅之堂”,新詩似乎又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奢侈品,因此“與詩無緣”幾乎成為底層民眾的共識。《講話》以降,“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原有的等級關系被打破,“民間文化”得到國家權力主體的極大重視,其地位迅速得到提升,而“精英文化”則被作為一種腐朽、落后的文化遭到無情的批判,其位置也順勢從中心滑向邊緣。在這種情勢中,“工農”作為“民間文化”的主體,他們不但是知識分子想象的對象,而且也是自我建構的對象。“新民歌”運動中極力倡導破除“詩歌神秘”的“迷信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破除和顛覆既有的文化等級觀念,重建文化新秩序。有人曾為此感慨到:“我們那會兒的土文化今天政府要讓它翻身。”[14]雖然“工農”詩人筆下的“新民歌”已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民間歌謠”,但它至少打破了知識分子一統詩歌天下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特權,使“工農”能最終消除了文化自卑,大膽書寫,放聲歌唱,獲得文化上的初次“解放”。
二
可以說,在“新民歌運動”中,“工農”的“文化翻身”既是真實可感的,又是相對而言的,也是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的。就“新民歌”而言,其中所發出與其說是“工農”的聲音,毋寧說是意識形態的聲音。雖然人們無從知曉“工農”真實聲音,但是在現實中,它不可能如此透亮、諧和與單一。因而,“文化翻身”的限度就是“學會說”,而不是“自由說”、“自主說”。新意識形態“規限”已經化入“工農”的文化“解放”行動之中。這些“規限”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新民歌”的生產方式,二是“工農”創作主體本身。
從生產方式來看,“新民歌” 是一場有組織文化生產運動。新民歌搜集、創作是在“黨的領導下”,“各級黨組織的提倡和組織”[15]下開展起來的,并且是“一項政治任務”:“黨和領袖的倡導給群眾火樣的熱情,黨在理論上和政策上的指導,給運動發展以正確的方向。各級黨組織的深入細致的組織工作,又保證了運動的廣泛開展。”[16]通過“理論和政策上的指導”,“工農”詩人認識到了詩歌創作的目的,不是像“小資產階級”那樣表現自己,而是為了表現“大躍進”時代人們的生產、斗爭的豪情,是配合各項中心工作、鼓舞人們“斗志”的文化武器,這是從觀念層面對“工農”的言說進行定位。通過“深入細致的組織工作”,他們的創作被納入到有序的組織生產中,比如有黨委組織的“專題賽詩會”:“歌唱豐收賽詩會”、“共產主義教育賽詩會”、“鋼鐵賽詩會”、“畝產賽詩會”等,還有“民歌演唱會”、“聯唱會”、“詩歌展覽會”、“戰擂臺”、“詩街會”等等,這些名目繁多的“賽詩會”對詩歌的主題、基調和競賽規則等要求都是相當明確的。“工農”詩人通過親身參與這些“組織活動”,一方面在競賽的游戲中獲得一種快樂、新奇的體驗,另一方面也不知不覺地被這些賽詩方式、詩歌想象方式等所吸引、感染,被迅速卷入這銳不可擋的詩歌狂潮中。于是,在耳濡目染和親身體驗中,“工農”詩人認識到了什么樣的詩才能加入這場“游戲”和“競賽”。如果他們為了這種“詩歌競賽”而創作,詩歌內容和想象方式就必須符合競賽的規則。這種潛在的“游戲”規則,使“說什么”和“怎么說”只能在一定的范圍內展開(圍繞某種政治和生產主題)和一定的軌道上滑行(用山歌、歌謠等形式進行“詩化”想象)。總之,一旦詩歌創作被納入各級政府的行政“任務”之后,就進入了有規則、有紀律的生產“程序”之中。這種“詩歌生產”的模式體現了“新民歌創作運動”中那種“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權力”運作方式。
另一種“權力”來自于下層,即“工農”詩人之間相互“交流”和“學習”。在這場詩歌運動中,各級黨委和文化部門還經常組織召開創作經驗“座談會”,這些“創作經驗談”,不僅僅是個人創作的經驗總結,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對創作經驗不斷“范式化”和“知識化”的過程,一旦某些知識成為其他創作者的創作“常識”時,意識形態的效應便產生了:它使創作主體學會了自我監督和相互監督。這樣“工農”詩人在“理論(上層)——實踐——經驗——理論(下層)”的不斷學習中,領會了“為什么寫”、“寫什么”和“怎么寫”。
從“新民歌”創作主體來看,“解放”需求層次的低下和意識形態化的感恩情懷是阻礙工農“文化翻身”的一雙隱形“巨手”。
“工農”詩人解放訴求限制了“工農”詩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翻身”。“五四”以來,許多現代知識分子經受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洗禮,豐厚的文化知識儲備和豐富詩歌創作經驗,使他們能夠對詩之所以為詩進行形而上的思索。比如,現代“中國一批新詩人”認為詩歌應該“張揚個性”;“詩是詩人情緒的‘自由抒寫”;“詩是‘表現的藝術”[17];“詩應該是民主精神的大膽的邁進”;“一首詩是一個人的人格”;“詩”必須有“豐富的思考力”;“僵死的理論,沒有思想情感的語言,矯揉造作的句子,煞費苦心的排列”是“詩的敵人”[18]。這里表達了這些詩人對詩之于創作主體的思想、情感、個性等“解放”的意義。而“工農”詩人則認為,“咱寫詩也是革命,為了大家跟上共產主義上天堂,所以寫詩也要往高處想,往遠處看,還要往大處說”[19];詩人“必須樹立正確的觀點,提高思想認識”,“必須時時刻刻聽黨的教導,多學習政治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虛心向勞動人民學習”。[20]在這兩種詩學觀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層次的“解放”需求。知識分子追求的“個性”、“民主”和“人格”通常和“自由說”及“自主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與知識分子“自主說”和“自由說”才算真正“解放”不同,對于底層民眾來說,“有權說”和“學會說”就意味著大“解放”,就意味著“站起來成了一個真正的人”[21],因而,他們無法感受到這種“解放”背后的新“束縛”。 回顧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不難發現,他們的“解放”層次越高,他們發現的問題也就越多,也就越不容易“滿足”,越喜歡“挑刺”,延安時期的丁玲、王實味就是這類知識分子。除通過精神的“不滿足”實現個體“解放”之外,梁實秋、沈從文、朱光潛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則通過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來實現自身的高層次“解放”的訴求。作為底層的民眾,他們既極易“滿足”,又愿意加入到新政權的建設中去,因而沒有知識分子可能有的痛苦、矛盾、猶豫和困惑,也不可能在詩歌中提出個體“解放”的更高層次的要求。于是,“工農”在“解放思想”和破除“詩歌神秘觀念”號召下,毫不猶豫地加入到這場詩歌狂歡中,收獲歡樂與激情,展現夢想。可以說,“工農”詩人對于“解放”的短視,使真正的“文化翻身”成為一個永遠的烏托邦。
意識形態化的倫理情懷是限制“工農”詩人實現真正“文化翻身”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施恩不圖報”和“知恩圖報”是個體在處理人倫關系時的重要美德。在古人看來,“知恩圖報”者具有君子之風范。這種儒家倫理觀念,已深深地鉚入大多數底層民眾生活中,有時甚至出現“日用而不知”的情況。在這場詩歌運動中,底層“工農”所受的“恩惠”感觸最深的是身份轉變,即由貧苦“工農”轉變為業余或專業的文藝工作者,享受較高的政治待遇。比如工人黃聲孝在解放前是個賣苦力的裝卸工,建國后成了一名業余詩人,他的創作得到武漢市委宣傳部長和黨委書記的重視和幫助。政府不但出資為他出版詩集,而且讓他參加“全國海河躍進會”、“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等各種會議,甚至還到華中師范學院參加文藝理論教學大綱教材的編寫。他說:“一個捏杠子的裝卸工人,能和大學生們一道生活,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事情。”[22]可以說,黃聲孝身份經歷了“工人——業余詩人——專業文藝工作者”以及勞苦大眾到國家主人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工農”創作“經驗談”中體現為回顧、體驗和展望人生敘述的模式:“苦難的過去——幸福的現在——美好的未來”。當然,在“工農”看來,給他們人生帶來三段不同景觀的“恩人”是新國家政權——“共和國”,它通過占有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方面的大量資源,為“工農”身份轉變“權力”保證。當底層民眾在身份、物質和精神層面受到“恩惠”時,他們便進入“知恩圖報”的倫理關系之中,并在言語、觀念和行動層面表現出來。在言語上體現為自我對“施恩人”的感激之情及報答“決心”。比如“我要堅決站穩無產階級立場,高舉毛澤東文藝紅旗,堅決向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文藝思想作無情的斗爭。為了感謝黨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我要在明年寫好一篇長詩向黨的四十周年獻禮”[23]。“工農”的這些謝辭和決心,并非全都是俗話或套語,其中肯定有真誠的成分。不可否認的是,口頭或書面的“感恩”言語形成一種輿論場,對其他的民眾起到教化作用,于是,在濃厚的“感恩”氛圍中,“施恩者”的頭上逐漸形成多重迷幻的光圈,并不斷被“圣化”和“完滿化”,從而使底層的民眾滋生一種崇拜心理。在觀念層面體現為對國家權力主體所提出的一切政策和理論的認同。“認同”其實就是對“政權”合法性和理論合理性的全部接納,也是對“政權”的一種尊重和服從。對于“工農”而言,“認同”的方式就是“牢記”國家權力主體的“囑咐”,并以這些“囑咐”武裝詩歌。在行動層面表現為積極投入到“新民歌”的生產當中,有些詩人“中心運動一來,馬上把報紙一看”,“立即動手”[24];有些“宣傳員不分晝夜在朗誦、說唱他們的新歌謠、新作品”[25],鼓舞人們生產斗志。這些“努力”從大的方面說是為了回報社會和國家。這種光有熱情而缺乏理性的“感恩”行動,很難對“感恩”行為本身可能存在的使人異化的因素,進行必要的反思。
此外,政治倫理向家庭倫理的巧妙對接和轉換,也使得“工農”深深陷入倫理的規約之中。有首新民歌這樣寫到:“老爺爺,笑哈哈,/手捧書本轉回家,/進門就把哥哥問:/‘你看這是‘社字嗎?/哥哥抬頭說聲‘是,/爺爺心里開了花:/‘當了一輩子睜眼瞎,/今天也能識字啦;/受了一輩子牛馬苦,/今天才知‘社是家”[26]。這是一首典型的表現翻身農民把“公社”(國家)想象成“家”的詩作,也反映了底層民眾普遍的想象方式和心理狀態。建國后,“人民當家做主人”這一宣言式的短語競相在各類傳媒中出現。新生的國家為了鞏固和發展,使政權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須在意識形態領域宣傳“家國合一”的思想,即“祖國是大家庭”,“國”是“家”的集合體。在這種思想中,由于政治倫理和家庭倫理之間存在某種內在勾連,傳統家庭倫理中的“孝”、“敬”、“父慈子善”等,也就巧妙轉化為政治倫理中的“服從”、“付出”、“犧牲”、“忠誠”、“報答”等等。這樣一來,政治倫理中的剛性要求,就順勢被“家庭倫理”柔化了。由于“家庭倫理”對于個體具有極強的約束力,它強調等級、有序、服從、尊重等等,哪怕是建設性的“質疑”、“批判”都被視為是對這一倫理的挑戰,因而可能遭到輿論的譴責,進而使那些“質疑者”產生深深自責。在這種情勢中,作為受過“恩惠”并且深受倫理觀念影響的底層大眾,也就不可能通過“介入”方式,對“施恩者”提出更高層次的自我“解放”的要求,因為這樣可能會背負“大逆不道”、“忘恩負義”、“無情”等等罵名。
[1]編后記[J].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175
[2][21] 殷光闌.唱的人人爭上游,唱的紅旗遍地插[A].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54,66
[3]李希文.我是怎樣編快板的[A].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67
[4]蔡恒昌.過去想唱不能唱,今天要唱唱不完[A].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111
[5]南帆.底層與大眾文化.東南學術[J].2006(5):4
[6][7][8]周揚.新民歌開拓了新詩的新道路[A].新詩歌的發展問題(第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13,3,2
[9][13][15][16]天鷹.1958年中國新民歌運動[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3,72,16,72
[10]包立春.黨給我一支筆[A].民歌作者談寫作[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12
[11]杜來盛.我是怎樣學寫作的[A].民歌作者談寫作[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34
[12]朱昭仲.我是怎樣創作山歌和花燈的[A].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76
[14]杜晶鐸.詛咒敵人,謳歌自己[A].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116
[17]龍泉明、鄒建軍.現代詩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34—42
[18]艾青.詩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73—196
[19]王老九.談談我的創作和生活[A].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10
[20]王應礎.初學者的感受[A].民歌作者談寫作[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60-61
[22]黃聲孝.站在共產主義高峰上看問題[A]. 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146
[23]潘傅明.做生產上的能手,當文化上的尖兵[A].民歌作者談寫作[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29
[24]黃聲孝.鼓起干勁來[A]. 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23
[25]李根寶.工人歌謠是工廠里的戰鼓[A].民歌作者談民歌創作[C].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23
[26]郭沫若、周揚編.紅旗歌謠[M].北京:紅旗雜志社,195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