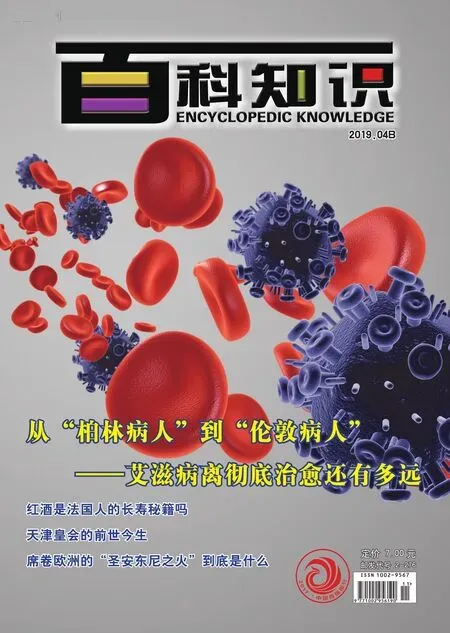中國(guó)歷史上的4次大旱荒
朱奎澤
有史以來(lái),人類(lèi)的生存與發(fā)展就伴隨著無(wú)盡的自然災(zāi)害。中華大地幅員遼闊,地理環(huán)境與氣候條件復(fù)雜多樣,災(zāi)荒之多,世罕其匹。自古及今,災(zāi)荒成為中華民族發(fā)展的一大威脅。縱觀近代的中國(guó)社會(huì),由于經(jīng)濟(jì)、政治、社會(huì)等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災(zāi)害更加頻繁,災(zāi)情也更為嚴(yán)重。而在接連不斷的災(zāi)害中,旱災(zāi)尤重,為害尤烈。據(jù)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表明,在整個(gè)近代時(shí)段內(nèi),中國(guó)的旱災(zāi)竟達(dá)60余次,而就全局性影響與危害程度重大者,動(dòng)輒幾十萬(wàn)、幾百萬(wàn)甚至上千萬(wàn)人被奪去生命,不計(jì)其數(shù)的人流離失所。歷史上有4次重大旱荒無(wú)需我們沉痛哀念。
“丁戊奇荒”
歷數(shù)近代中國(guó)的大旱荒,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指的是19世紀(jì)70年代后半期(即光緒初期)發(fā)生于我國(guó)黃河流域廣大地區(qū)(華北地區(qū)尤重)的一次特大災(zāi)荒——以干旱為其突出表征。這場(chǎng)大旱荒是光緒元年(1875年)拉開(kāi)序幕的。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區(qū)先后出現(xiàn)干旱的跡象,京師和直隸地區(qū)在仲春時(shí)節(jié)便顯現(xiàn)了災(zāi)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與此同時(shí),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等省,都在這年秋后相繼出現(xiàn)嚴(yán)重旱情。光緒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此后持續(xù),受災(zāi)范圍也進(jìn)一步擴(kuò)大,尤以光緒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最為嚴(yán)重,而這兩年陰歷干支紀(jì)年屬丁丑、戊寅,故名“丁戊奇荒”。局部地區(qū)的旱情持續(xù)到1879年。以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5省為主要災(zāi)區(qū),北至遼寧,西至陜甘和川北,南達(dá)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旱荒區(qū),總面積超過(guò)百余萬(wàn)平方千米。其中又以河南、山西受災(zāi)最重,因而又稱“晉豫奇荒”或“晉豫大饑”。這次旱荒持續(xù)時(shí)間長(zhǎng)、波及范圍大、后果特別嚴(yán)重,被認(rèn)為是清朝“二百三十余年來(lái)未見(jiàn)之凄慘,未聞之悲痛”,其為害之烈、為患之深,在整個(gè)中國(guó)歷史上也屬罕見(jiàn),實(shí)屬“大衩奇災(zāi),古所未見(jiàn)”。大旱使農(nóng)產(chǎn)絕收,田園荒蕪,樹(shù)木枯槁,青草絕跡,赤地千里,餓殍載途,白骨盈野。旱荒過(guò)后,繼之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慘絕人寰的境地。
從一些時(shí)記來(lái)看。旱荒景象駭人聽(tīng)聞。河南省“歉收者50余州縣,全荒者28州縣”,“乏食貧民,所在多有”;山東省“饑?yán)桢髌拶u(mài)子流離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狀”:山西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wàn)口之多”,“民人或什損六七,或十死八九”:直隸地區(qū)“旱蝗相乘,災(zāi)區(qū)甚廣”,“經(jīng)年不見(jiàn)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轉(zhuǎn)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運(yùn)河官道之旁,倒斃滿路”:蘇北、皖北各地“逃亡餓死者不計(jì)其數(shù)”,災(zāi)民甚而“饑則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蹤,相戒裹足”;甘肅、四川受災(zāi)區(qū)“赤地?cái)?shù)百里,禾苗焚槁,顆粒乏登”,“登高四望,比戶蕭條,炊煙斷縷,雞犬絕聲”。“父棄其子,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hào)哭于路途。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陜西“赤地千里,幾不知禾稼為何物矣”。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從1876年到1879年,僅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陜西等北方5省遭受旱災(zāi)的州縣高達(dá)955個(gè)。整個(gè)災(zāi)區(qū)受到旱災(zāi)及饑荒嚴(yán)重影響的居民人數(shù),估計(jì)在1.6億~2億左右,約占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饑荒和瘟疫的人數(shù)在1000萬(wàn)人左右;從重災(zāi)區(qū)逃荒流亡者不少于2000萬(wàn)人。災(zāi)荒對(duì)當(dāng)時(shí)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及以后歷史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連年的旱荒,清政府不可能視而不見(jiàn)。為防止因天災(zāi)而引發(fā)的民變,力求社會(huì)穩(wěn)定,度過(guò)難關(guān),政府一度對(duì)救災(zāi)工作頗為重視,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疏困,洋務(wù)派官僚更是積極參與其事。巨大的災(zāi)難也引發(fā)了國(guó)內(nèi)外民間力量的關(guān)注和賑濟(jì)行動(dòng)。南方省區(qū)的紳富、香港同胞及新加坡、菲律賓、泰國(guó)、越南等國(guó)華僑,紛紛解囊捐款。盡管如此,囿于客觀條件限制,加之清政權(quán)整體腐敗的頹勢(shì),賑災(zāi)活動(dòng)難見(jiàn)力挽狂瀾之效。與此同時(shí),列強(qiáng)侵略活動(dòng)的日益加深,強(qiáng)化了旱荒對(duì)中國(guó)人民的沉重打擊。
華北大旱荒
有學(xué)者曾言及,由于1919年(五四運(yùn)動(dòng))和1921年(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誕生)的標(biāo)志性年份意義為人們津津樂(lè)道,1920~1921年的旱荒,卻似乎被人冷落甚至淡忘了。其實(shí),這是一個(gè)由于嚴(yán)重的旱荒造成80萬(wàn)生命的悲慘滅寂和3000余萬(wàn)饑民在死亡線上痛苦掙扎的大稷之年,是近代中國(guó)人民綿延不絕的苦難鏈條中巨大而沉重的一環(huán)。
反觀1920年中國(guó)北方地區(qū)發(fā)生的特大災(zāi)荒,在許多方面和40年前那次慘絕人寰的“丁戊奇荒”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重災(zāi)區(qū)域,東起海岱,西達(dá)關(guān)隴,南至襄淮,北抵京畿,恰好也包括今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等省的廣大地區(qū)。自“丁戊奇荒”以來(lái),北方地區(qū)還不曾出現(xiàn)過(guò)像1920年這樣長(zhǎng)時(shí)間、大面積的嚴(yán)重旱荒局面,以致時(shí)人每每將兩者相比擬,稱后者為“四十年未有之奇荒”。
就時(shí)序而言。大約從1919年夏秋之交,北方大部分地區(qū)就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旱情。1920年自春至秋,旱情更是酷烈異常。著名的華洋義賑團(tuán)體“北京國(guó)際統(tǒng)一救災(zāi)總會(huì)”在其總結(jié)報(bào)告中曾言“此次災(zāi)荒最近原因?yàn)?920年秋收前已一年無(wú)雨是也”。
就地區(qū)而言,包括直隸省在內(nèi)的畿輔之地,幾乎全境皆旱,遭災(zāi)最重。山東“赤地千里、野無(wú)青草”;河南更是無(wú)處不早,顆粒未收;陜西“赤地千里、人民嗟怨”:山西出現(xiàn)“禾苗盈尺、蔓草同枯”的凄惶景象。
各地災(zāi)民生活的困窘狀況令人扼腕。饑民無(wú)所不食,賣(mài)兒鬻女,隨處可見(jiàn)。據(jù)載,順德一府就有2萬(wàn)5千余名幼童被出賣(mài):山東不少地方的農(nóng)民因“無(wú)力養(yǎng)子”,甚至“投諸井中”,陵縣附近之井,“竟至湮塞”。饑民到處流徙,自清初以來(lái)即已綿延不絕的“走關(guān)東”由此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時(shí)期,在1920~1921年間,遷入東北的流民數(shù)量連續(xù)突破了10萬(wàn)、30萬(wàn)大關(guān)。
據(jù)有關(guān)資料估算,整個(gè)旱荒期間。被災(zāi)縣份320余個(gè),災(zāi)區(qū)面積約272萬(wàn)方里,受災(zāi)人數(shù)在3000萬(wàn)左右,死亡人數(shù)約50萬(wàn)。
在此次旱荒中,除北洋政府名存實(shí)亡的賑濟(jì)措施外,民間義賑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尤以1920年間的“華洋義賑”最為突出,使義賑工作得到了較大地完善和改進(jìn),這無(wú)疑是一個(gè)歷史的進(jìn)步。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千百萬(wàn)中國(guó)人民長(zhǎng)期承受大災(zāi)巨稷而付出了極其沉重的歷史代價(jià)之后,所得到的一種補(bǔ)償吧。
10余省大旱荒
風(fēng)雨過(guò)后,彩虹未現(xiàn)。就在人們對(duì)1920~1921年間的大旱荒心有余悸,加之軍閥紛爭(zhēng)、兵連禍結(jié)之時(shí),又一波早荒接踵而至。這就是起于1928年,持續(xù)至1930年的遍及華北、西北、西南10余省的大旱荒(以陜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yuǎn)、
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6省,并波及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省的部分或大部分地區(qū),局部地域的旱情持續(xù)至1932年)。旱荒,將田野變成荒丘,把生靈化作白骨,使農(nóng)莊淪為廢墟。這場(chǎng)以旱荒為主的巨災(zāi)曠日持久,加之各地蝗、風(fēng)、雪、雹、水、疫并發(fā)的情況,全國(guó)至少有20余省被災(zāi)。
西北陷入“活地獄”,親見(jiàn)當(dāng)時(shí)慘象的一位傳教士曾留下了這一說(shuō)法,形象地反映了西北民眾所面臨的恐怖景象。有數(shù)據(jù)表明,陜西淪為餓殍、死于疫病的有300多萬(wàn)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wàn),兩者合計(jì)占全省人口的70%。甘肅災(zāi)情和陜西大體相似,“莊稼無(wú)收,饑饉薦至”,疫病大作,死亡者達(dá)50多萬(wàn)人。陜甘大地成為極重災(zāi)區(qū)。
華北平原荒墟成片。據(jù)1928年華洋義賑會(huì)報(bào)告書(shū)敘述,華北災(zāi)情之重、災(zāi)區(qū)之廣,為數(shù)十年所未有。山西的旱情次于陜西,全省105縣,早區(qū)占80%以上,“禾稼盡枯”,災(zāi)民約600余萬(wàn)。察哈爾境內(nèi)“一片荒涼”,“顆粒未登,人民凍餒交迫、死亡枕藉”,死亡率約占饑民總數(shù)的十分之三四。位處中原的河南被時(shí)人稱為“災(zāi)上加災(zāi)”的荒情奇重地區(qū),災(zāi)民累計(jì)達(dá)3590萬(wàn)人。綏遠(yuǎn)、河北兩省,則在旱情交錯(cuò)中苦熬。有材料表明,綏遠(yuǎn)人口約250萬(wàn),災(zāi)民就達(dá)190萬(wàn);河北129縣先后被災(zāi),災(zāi)民共計(jì)600余萬(wàn)。熱河也是多災(zāi)并發(fā),饑民百余萬(wàn)。山東先早后蝗,繼而黃河連續(xù)決口,災(zāi)民累計(jì)1000萬(wàn)以上。旱情所及之蘇北、皖北未逃其劫,連洪澤湖都枯竭了。南向延及的湖北,西南向延及的四川,災(zāi)民均以數(shù)百萬(wàn)計(jì),河井枯竭,五谷絕種,雞犬無(wú)聲。
對(duì)于這場(chǎng)大旱荒,美國(guó)記者斯諾曾寫(xiě)下這樣一段筆記:中國(guó)西北,我目擊數(shù)以千計(jì)的兒童死于饑荒……從1924年起,久旱無(wú)雨。今天,饑荒的魔影實(shí)際上威脅著中國(guó)的四分之一的土地。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圖景。一切生長(zhǎng)中的東西,仿佛都被新近爆發(fā)的火山灰燼一掃而光。樹(shù)皮剝落以盡,樹(shù)木正在枯死。村子里,大多數(shù)泥磚房屋已經(jīng)倒塌。
據(jù)相關(guān)數(shù)據(jù)表明,在這場(chǎng)大災(zāi)中,全國(guó)被災(zāi)人口總計(jì)近1.2億,難民約5000萬(wàn)左右,死亡1000余萬(wàn)。而忙于爭(zhēng)斗的各路軍閥和蔣介石政權(quán),均未有實(shí)質(zhì)性的行動(dòng)以賑濟(jì)苦難纏身的災(zāi)民。
南北大旱荒
就在中國(guó)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zhēng)陷入了極端嚴(yán)峻的局面時(shí),一場(chǎng)曠日持久的特大干旱,夾雜著蝗、風(fēng)、雹、水等各種災(zāi)害,洶涌而來(lái)。這場(chǎng)早荒漸起于1941年,至1942~1943年達(dá)于極致,橫掃了以中原大地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兩岸,在南至湖南,北至京津,東瀕大海,西及甘肅的廣大范圍內(nèi)。形成數(shù)十年未有的大稷奇荒。而遠(yuǎn)處南方的廣東也未躲過(guò)此劫。部分地區(qū)旱荒持續(xù)至1945年。
對(duì)于地處中原的河南而言,這是20世紀(jì)20年代末以來(lái)最嚴(yán)重的早荒。據(jù)調(diào)查表明,全省饑民達(dá)1000萬(wàn),近300萬(wàn)人困餓而死,在旱荒第一年可能就有近100萬(wàn)人殞命。這一數(shù)字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了60多年前的“丁戊奇荒”中河南人口的死亡總數(shù)。美國(guó)《時(shí)代》周刊記者自修德曾提及從洛陽(yáng)到鄭州的情況,“絕大多數(shù)村莊荒無(wú)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聽(tīng)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jiàn)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體并撕咬著上面的肉”。災(zāi)民們?cè)诮^望之后紛紛踏上了逃荒之路,300萬(wàn)人流離失所,從而形成了自花園口決口之后河南災(zāi)民的第二次人口大遷移。按1944年1月17日《大公報(bào)》的描述,所謂“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的情形“已成過(guò)去”,因?yàn)檫@里已是“百余里人煙絕跡”,真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的無(wú)人地帶了。
此次旱荒,除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大地外,廣東受災(zāi)也極其嚴(yán)重,全省大饑,災(zāi)民無(wú)數(shù),凍餓而死者達(dá)50萬(wàn)人以上(一說(shuō)300萬(wàn))。僅當(dāng)時(shí)的陸豐地區(qū)就有10余萬(wàn)人餓死。旱情所及的其他省份,諸如河北、山西、山東、陜西、甘肅等均苦于旱荒,饑民遍野。
在此次大早荒中,除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抗日邊區(qū)開(kāi)展了較為有效的群眾性自救運(yùn)動(dòng)外,國(guó)統(tǒng)區(qū)未有切實(shí)的救荒行動(dòng)。國(guó)民政府賑災(zāi)不力的情況,曾被當(dāng)時(shí)在重慶美國(guó)新聞處工作的美國(guó)人格蘭姆·貝克委婉地指出:“這樣一場(chǎng)大災(zāi)難可能不完全是人為的;但很明顯,如果不是人為因素的話,可能不會(huì)死那么多人。”就我觀察到的國(guó)民黨的所作所為而言,盡管他們說(shuō)得動(dòng)聽(tīng),但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表面文章。不少救災(zāi)行動(dòng),往往“爭(zhēng)執(zhí)數(shù)月,完全擱淺”。而從政府官員到軍界人士、商人和貪官則做著大發(fā)旱荒財(cái)?shù)摹⒐串?dāng)。日偽占領(lǐng)區(qū)的民眾更是愁云慘淡,無(wú)休止地?zé)龤ⅰ⒔俾印⒗账髋c破壞,無(wú)疑是雪上加霜。
據(jù)相關(guān)機(jī)構(gòu)統(tǒng)計(jì),20世紀(jì)內(nèi)世界發(fā)生的“十大災(zāi)害”中,旱災(zāi)高居首位,有5次,其中近代中國(guó)的大早荒上榜3次。這就是上述所及的1920年的華北大旱荒,1928~1929年的陜西大旱荒和1943年的廣東大旱荒。
迄今為止,還沒(méi)有任何一個(gè)國(guó)家、一種社會(huì)制度能夠完全抵御災(zāi)荒,然而天災(zāi)又是同特定的政治、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互為因果的。天災(zāi)對(duì)社會(huì)的破壞程度和社會(huì)抗災(zāi)能力的強(qiáng)弱,常常要受到一個(gè)國(guó)家的社會(huì)性質(zhì)和綜合國(guó)力的影響。近代以來(lái)的中國(guó),自然環(huán)境的日益破壞,落后的生產(chǎn)力,腐敗不已的政治狀況,接連不斷的軍閥混戰(zhàn)等等,人為地加劇了歷次災(zāi)荒的嚴(yán)重性。誠(chéng)如1930年5月16日天津《大公報(bào)》評(píng)論當(dāng)時(shí)災(zāi)荒情形時(shí)所說(shuō):“夷考之故,則近年來(lái)中國(guó)之惡劣的政治,實(shí)為厲階也。”從這個(gè)意義上講,這幾場(chǎng)極為嚴(yán)重的大旱荒。是苦難的近代史的一次次光影。美國(guó)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說(shuō)過(guò),1949年以前,中國(guó)平均每年有300萬(wàn)~700萬(wàn)人死于饑餓,所言并非全無(wú)根據(jù)。今天,我們回顧這些大早荒,不應(yīng)只有哀嘆,更需深思其中況味。
責(zé)任編輯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