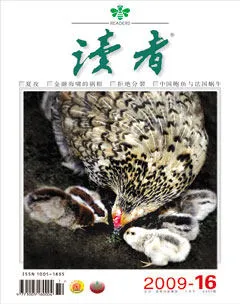順其自然的人
李青松
他的名字好記,“巴勒斯坦”去掉最后一個字,就是他的名字。
北京的書店,我只去“三聯(lián)”。巴勒斯的那本小書,我是從“三聯(lián)”地下一層的書架上意外淘來的。
巴勒斯是19世紀美國的生態(tài)文學(自然文學)作家,以寫鳥著名。他的作品多是以美國東部的卡茨基爾山脈為背景,代表作《醒來的森林》被譽為生態(tài)文學的經(jīng)典之作。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說,他自己是看著巴勒斯的書長大的,他的生態(tài)思想源于巴勒斯。
那就對了——巴勒斯說,他的使命就是把人們送往大自然。
2003年,我訪問美國猶他大學,接觸過的一些美國人中,知道巴勒斯及其作品的卻并不多。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不過,細想想也不奇怪。20世紀70年代,浩然和他的小說《艷陽天》對中國的影響多么巨大呀,可問問那些“80后”和“90后”,知道浩然的沒有幾個。這不要緊,雖然人們忘記了巴勒斯的名字,但他的思想?yún)s在深刻影響著美國,乃至世界。
我在“三聯(lián)”書店淘到的那本小書,正是《醒來的森林》。書中有一節(jié)對鷹的描述:“鷹的飛翔是一幅動中之靜的完美圖畫。它比鴿子和燕子的飛翔給人以更大的刺激。它翱翔時所付出的努力,人的肉眼很難觀察到。那是力量的自然流動,而不是它有意在利用力量。”我曾在電話中,把這段話讀給一位心緒不佳的好友聽。過了一會兒,他回電話說,他決定了——明天要去野外觀鳥。
過去我一直認為,蜂蜜是蜜蜂從花蕊中采集的。讀了巴勒斯的書,才知道并非如此。蜜蜂從花中采集的只是甘露,由甘露到蜂蜜需要一個轉化的過程。蜜蜂通過減少甘露的水分和加入一小滴蟻酸,釀出美妙的蜂蜜。
蜂蜜是蜜蜂的產物,不是花的產物。但是,蜂蜜能反映蜜蜂所處的環(huán)境以及超越其環(huán)境的某些東西——我不知道,我這樣的表述是否準確。
巴勒斯說,蜜蜂是真正的詩人,真正的藝術家。
巴勒斯外表粗獷,如同森林中裸露的老樹根,久經(jīng)風霜。1837年,巴勒斯生于紐約卡茨基爾山區(qū)的一個農場,當過農民、教師、專欄作家。他一生的著作有25部,大都是描述自然、描述鳥類的。巴勒斯還做過多年金庫保管員,工作是寂寞而枯燥的。在漫長而無所事事的歲月里,他面對鐵墻寫作,并在寫作中尋求慰藉。他說,他書中的陽光要比紐約和英格蘭的陽光燦爛得多。
1873年,離開金庫的鐵墻之后,他來到了哈得孫河的西岸。他說:“那滿架的葡萄要比金庫的美鈔更令我滿足。”巴勒斯在哈得孫河西岸購置了一個果園農場,并在那里親手設計和建造了一幢石屋,被稱為“山間石屋”。在那里他過著農夫與作家的雙重生活,他手中的工具除了鋤頭、望遠鏡,就是筆了。詩人惠特曼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巴勒斯掌握了一門真正的藝術——那種不去刻意追求、順其自然的成功藝術。”
巴勒斯的“山間石屋”,吸引了眾多熱愛自然的人們。當時的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發(fā)明家愛迪生、汽車大王福特、詩人惠特曼均來過他的“山間石屋”做客。
“山間石屋”幾乎成了19世紀美國生態(tài)文學的象征符號。
巴勒斯去世后,美國成立了“巴勒斯紀念協(xié)會”,“山間石屋”被作為國家歷史遺產受到保護。在美國,有11所學校以巴勒斯的名字命名。“他把自己像種子一樣播撒在那片土地上,他的心境和感情與那片土地息息相關。砍那些樹,他會流血;損壞那些山,他會痛苦。”
《醒來的森林》的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它不僅描述了眾鳥歸來的情景,更多的是喚醒了人們對自然的愛和善待自然的態(tài)度。巴勒斯不是自然之外的旁觀者,而是把自己融入了自然,使其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在寫作的過程中,巴勒斯實現(xiàn)了心靈與自然的溝通。
(曹可欣摘自《光明日報》2009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