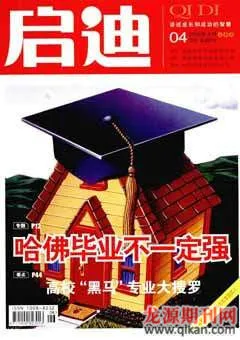愛因斯坦的煩惱
王櫟鈞
愛因斯坦五十壽辰時,弗洛伊德給他發來了賀信,稱之為“幸運兒”。弗洛伊德解釋說,他之所以把愛因斯坦看成一個幸運兒,是因為沒有哪個不精通物理學的人膽敢評判他的理論,而男女老少都可以評判弗洛伊德的理論,不管他們是否懂得心理學。
我不懂物理學,看到商務版《愛因斯坦文集》,只是瀏覽一下,沒有興趣。事實上,我也是還沒有接近他的中心思想就過早失去耐心與勇氣的讀者之一。很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愛因斯坦的書信,竟異常喜歡:條理清晰,感情真摯,就像老友面晤,或是聆聽老人正直的負責任的忠告或引導。他對你的提問娓娓作答,很親切很睿智,甚至有股機警的幽默。周有光回憶起見到的那個愛因斯坦,外表粗疏,不修邊幅,但說話始終帶著平和的態度。這跟他的行文如出一轍,或許,這一點深深打動了我。
在蘇黎世求學期間,愛因斯坦的家境不寬裕。在1898年寫給妹妹的信中,他坦露了對家人的憂慮與歉疚:“我已長大成人,可是仍然無所作為,一點忙也幫不上,這真使人肝腸欲斷。我只能加重家庭的負擔……確實,如果當初根本沒有生我,情況也許會好一些。唯一使我堅持下來免于絕望的,就是我自始至終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竭盡全力,從沒有荒廢任何時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除了讀書之樂外,我從不允許自己把一分一秒浪費在娛樂消遣上。”
1915年,愛因斯坦在柏林完成了廣義相對論。在1919年的一次日蝕觀察中,一些英國科學家證實了愛因斯坦的論斷。這消息一經宣布,愛因斯坦一夜之間成了名揚全球的人物,但他一直沒弄清楚這榮譽是怎么回事。他在給蘇黎世朋友粲格爾的信中寫道:“自從出名以來,我變得越來越笨,當然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在一個人同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間,至少在他人所說的他們心目中的形象之間,確實有著天壤之別,但他卻不得不以一種詼諧幽默的心情來接受這一事實。”
愛因斯坦成名之后,無數人給他寄來信件,這些信件無奇不有。例如,有一小姑娘問他地球什么時候會毀滅。愛因斯坦的答復極為簡潔,不乏風趣:“地球已經存在了十億年有余。至于它何時終了的問題,我的意見是:等等看吧!”有一位自稱為政治家和阿德勒學派心理分析家的人,寫信問他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分析。他回信很短,只有一句:“非常遺憾我無法滿足你的要求,因為我只希望自己能留在沒有經過分析的黑暗之中。”很自然,愛因斯坦也不可避免地收到了那些自以為其見解頗有重大科學意義的人們的來信,有時這讓他簡直忍無可忍。1952年,他在給紐約一位藝術家的信中說:“謝謝你7月7日的來信。看來你肚子里塞滿了這個國家知識分子中時髦一時的空洞言詞與觀點。如果我能成為一個獨裁者,那我一定要禁止使用這些莫名其妙的蠢話。”這話就嚴厲多了。
讀著愛因斯坦的書信,也是感受一個社會人煩惱與喜悅交替的成長過程。他的言語不僅用來表達科學理論,也是闡述其思想的有力工具。1947年他給一個愛達荷州農民剛出生的兒子寫了一段話:“雄心壯志或單純的責任感不會產生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對于人類和對于客觀事物的熱愛與獻身精神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那農民后來寄了一大袋土豆感謝他。而愛因斯坦也用一段簡短明了的定義,幫我區別清了藝術與科學,使我受益匪淺:“如果用邏輯的語言來描繪所見所聞的身心感受,那么我們所從事的就是科學;如果傳達給我們的印象不能為理智所接受,而只能為直覺所領悟,那么我們所從事的便是藝術。”
風如摘自《青島日報》
編輯/靜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