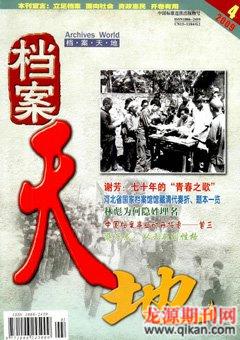“小沈陽”為什么走紅
張頤武
2009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最為引人矚目的角色似乎就是“小沈陽”。他真正通過“春晚”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迅速成為社會的焦點。在互聯網和紙媒中形成了熱議的浪潮,他的形象和語言方式,也成為了模仿和挪用的資源。“小沈陽”在這個經濟面臨挑戰的春節期間成為了快樂的證明,既成為電視臺和演出市場最歡迎的人物,當然,也引起了見仁見智的討論和分歧的意見。這股“小沈陽旋風”在春節過后很久,還沒有衰減的趨勢,其實,也反映出了社會和文化變革的一些方面,值得反思和探討。
“小沈陽”的走紅當然還是春晚這個平臺在26年的發展所具有的巨大的影響力的證明。經過了這些年的發展,雖然有眾說紛紜的討論,但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仍然具有高度的影響力和無可爭議的關注度。在“春晚”舞臺上的成功,仍然具有相當巨大的作用。人們常常說小沈陽可謂“一夜成名”,這其實不可能是說他從前沒有積累,只要有這樣的舞臺就可以成名,而是說沒有這個平臺,其實就是身懷絕技,也難有被全國觀眾乃至全球華人觀眾了解的機會。這說明,中央電視臺的“春晚”所具有的文化效應,仍然是異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
今年,“春晚”嘗試找回過去“聯歡”的互動性和小節目的活潑生動的氣韻的努力,也獲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春晚依然是社會生活中的“最大公約數”,仍然是大年三十晚上的“新民俗”。在這個舞臺上演出是巨大的機遇和考驗,在這個舞臺上的成功,就意味著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觀眾群體的肯定。這一點,其實在“小沈陽”這里再度得到了證明。
“小沈陽”的成功,也說明以著名小品演員趙本山為標志、來自于東北“二人轉”文化的傳奇,仍然在延續和發展。這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舞臺上發展起來的獨特現象,近年來已經持續地擴展和延伸。在這里,東北“二人轉”文化,一方面通過“劉老根大舞臺”等演出場所成功地保持并發展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傳統技藝,同時也保留了它和觀眾之間直接的、面對面互動的傳統。另一方面,通過喜劇小品、電視劇等形態使得“二人轉”所培養的各方面的人才得到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使得“二人轉”超越了自己的地域性,而在新的形式中得到發展。在這些形態中,“二人轉”不再以傳統的方式存在,而是其許多重要的基本元素通過諸如編劇、導演和演員的努力,滲透到其他的藝術形式之中。這既是一種傳統農耕時代所流傳的文化形態的延續,又是新的文化產業的展開。
可以說,“二人轉”已經不再僅僅是東北的一種傳統民間藝術,而已經轉化為一種具有全國性影響和通過電視、網絡等各種媒介輻射的、獨特的文化產業資源。比如,今年“春節聯歡晚會”的小品《不差錢》,其劇本未必完全盡如人意,但趙本山和“小沈陽”的表演功力和“二人轉”文化中的獨特的營造喜劇氛圍的技巧的運用,仍然使得這個小品能夠取得成功。這就是“二人轉”文化具有的獨特魅力。
這種魅力其實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在長期的演出市場中磨練所造就的獨特的“絕活兒”。由于傳統的劇場演出存在著劇烈的競爭和票房的現實壓力,演員如果沒有“絕活兒”的“一招鮮”,就很難吸引現場的觀眾。這既是傳統“二人轉”技藝的傳承,又是需要和新的時代和觀眾的趣味相適應的發展和變化。比如,趙本山的出色的模仿能力,往往用在模仿鄉村老人等方面。“小沈陽”則更加時尚化,比如,他更多地演唱當下流行的歌曲等。這種模仿的能力也是“絕活兒”,但模仿的對象則可以與時俱進。這種經過長期演出磨練的“絕活兒”,一旦有了更大的平臺和機遇,就會有淋漓盡致的表現。
二是由于長期市場化的演出,像趙本山和“小沈陽”這樣的演員,都有在現場充分地把握觀眾情緒的超凡能力,對于人情世故和生活情態有深入的理解。因此,能夠讓臺上臺下充分互動,能夠讓全場的氣氛飆到最高。觀眾也會完全沉浸在表演所創造的戲劇性的快樂之中。這種魅力的核心當然是以觀眾為中心的,“絕活兒”是為了能夠更好地表現基本功。“互動”環節,則可以抓住觀眾的注意力。而“二人轉”師徒相傳的傳統,在這里也成為培養人才和凝聚力量的一種路徑。現在看來,趙本山巨大的影響力,和對于徒弟的幫助,實際上非常有利于人才的脫穎而出。正是這樣的背景下,“小沈陽旋風”才有可能出現。
當然,“二人轉”的文化也存在著未必完全脫離低俗的弱點。往往會限制它在大平臺上發展和表現的深度,這也會成為它發展的“瓶頸”。這也是需要加以提高和轉化的,但它和觀眾直接互動的能力和始終關切觀眾反應的能力,卻是它最寶貴的東西,也值得繼續發揚。同時,人們往往經常要求文藝有更深遠的社會和文化的意義,這當然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讓人們能夠有輕松的、無重負的歡笑,其實也對于人們減輕面對生活的壓力,促進社會的和諧和健康發展有積極的意義,也不宜給以輕易的否定和簡單的抹殺。“小沈陽旋風”在這方面對于當代文藝也有很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