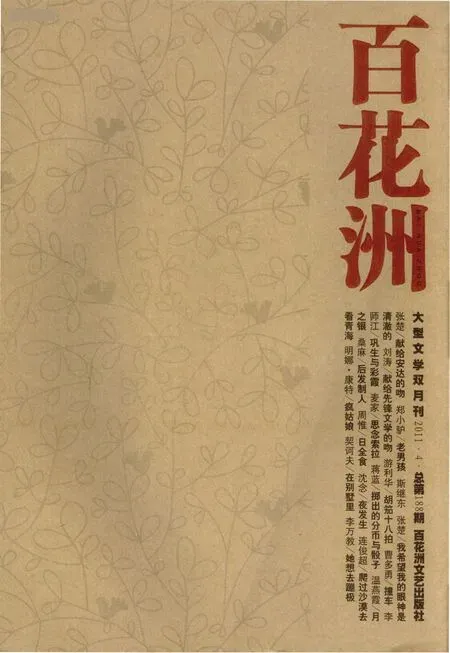京都記
于 堅
我從東京乘10點50分的新干線前往京都。有座位號的票是13200日圓,將在下午1點10分到達。東京的朋友說,在京都停車的時間只有兩分鐘,我便有些忐忑。中國生活的經驗,那時候車廂里全是慌忙取過行李奪路而去的人,也許就因為互不相讓而擠在過道上耽誤了下車。我帶著一只箱子、一個提包、一個背包,如何了得啊!但上了車,發現行李架并不能放大型的箱子,而大家也不把箱子放在自己的座位旁邊,死死守著,而是集中放在車廂口,那里有一個專門放大型行李的架子。下車的時候再去取,車停的時候也不會有人跑去看是不是有人帶走自己的箱子,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放在那里的箱子并不多,兩三個而已,很少有人進行我這樣大輜重的旅行,乘客大多只是帶著一只公文包,提一個紙盒子而已。起初我不知道那紙盒子是什么,后來才知道那是便當,就是日式快餐。便當打開,幾個格子里裝著米飯團、生魚片、雞蛋羹、生菜。大部分人西裝筆挺,吃便當的方式也差不多,滴水不漏,低頭各自吃盡,然后將盒子收進塑料袋,送到垃圾箱去。絕沒有杯盤狼藉的情況,也沒有人說話。列車奔馳,只聽得見列車撕開空氣時產生的巨大摩擦聲。我已經是第二次乘坐新干線,從來沒有聽到誰高談闊論,或者躺倒歪斜徹底放松,大家最多就是彬彬有禮地小寐一下或者看書看手機短信看電腦,風景是沒法欣賞的,速度太快,一閃即逝。一眼看去,車廂就像一個大公司的工作間,新干線完全是一趟工作快車,沒有絲毫的旅游氣氛。列車的滾動條屏里精確地告訴乘客這是開向某地的某次列車,途經哪幾個站,洗手間在第幾個車廂。之后就滾動簡要新聞,我看得懂這些漢字:物流、億、販、技術、知、住友銀行、逮捕,以及一個調查:中學生可以在0.7秒內記住9個數字。坐在我旁邊的男子已經吃完便當,看了一眼手機,很禮貌地睡去。他看起來三十歲左右,禿頂,西裝,黑色領帶,戴眼鏡,黑皮鞋擦得雪亮,就像兩輛拴在腳髁上的微型豐田轎車。
在公元794年到1869年之間,京都是日本的首都,叫做“平安京”。持續了1110年的首都,夠平安的了,這是日本歷史的特征,很少曲折,不像中國歷史這樣巨大的動蕩,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許多人給我說,京都如何地古老,如何地就是唐代中國長安的縮影。一路上我總是想著長安的樣子,許多詩句涌現出來,“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播音器里響起了日語,那是報道一個車站就要到了,已經1點鐘了。從時間上看,這個要到的站應該就是京都,但我看見窗子外面只是一片原始的水泥森林,一直排開到遙遠天空的盡頭,哪有半點長安的影子。遲疑片刻,飛快地收拾,然后向著車廂口奔去,拖出箱子,我奇怪地以為全車人都是到京都去的,并沒有其他人下車,唯我而已,我肯定已經成為這一路下車者中動靜最大的一位。是不是長安先不管了,我必須在這個叫京都的站下車。
我立即進入了一個超現實的車間之類的地方,幻覺中這建筑還在進行電焊,弧光閃閃,其實它已經完成了十多年,依然是煥然一新,就像昨天剛剛落成。巨大的弧形臺階和銀白色的金屬電梯從高處像瀑布一樣流下,上面站著木偶般的人類,令我頭暈目眩,驚愕不已。京都車站是一個巨大的電鍍過的閃著微光的鋼材交錯的建筑。內部有峽谷般的空間,似乎是一只恐龍的骨骼,它的肚子捅了幾個大窟窿,可以看見天空。或者橫著的埃菲爾鐵塔,結構就像M.C.埃維舍爾畫的迷宮。我立即被帶進一架電梯,在鋼鐵的捆綁中升向高處,出來的時候穿過不銹鋼編織成的隧道,推開一道道玻璃門,仿佛是在世界最高級的礦井中工作的礦工。隧道附近的玻璃門后面是百貨公司、商店、美容廳、咖啡室,塑膠制造的模特兒在櫥窗里微笑著。最后,一系列玻璃門在身后晃著,我被帶進一個叫做拉面小路的館子里坐下。少頃,一大碗熱騰騰的日式拉面就端過來了,相當好吃。這鋼鐵恐龍的內部居然藏著一碗拉面。窗子外面,有座高舉著一個圓球的塔,那是全日本都知道的京都塔。
京都車站是日本規模最大的車站,設計者是原廣司。京都被譽為通向日本歷史的大門。當年,車站設計方案的招標活動非常隆重,舉行了國際競賽。1991年5月,競賽結果發布,原廣司的方案被評為最優秀方案并實施。原廣司認為,今日的京都依然清晰地保留著1200年前平安京時代的城市形態,其歷史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城市地理特征。他的方案意圖表達地理上的、作為城市通向“歷史之門”的聚集場所。車站的建筑設計,如果僅僅滿足基本交通功能是不夠的,它更應該與城市設計緊密結合,以它為載體,創造出城市公共空間,具有影響、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能量。
車站占地38076平方米,總建筑面積237689平方米,地上16層,地下3層,除了地鐵車站和火車站外還包含了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文化中心、博物館、旅館、地區政府辦事處以及一座大型立體停車庫。用于車站的面積僅占總面積的1/20。此外,還有大量室外、半室外的公共活動空間。整個建筑內各類電梯就有148臺,相當于京都每年申請設置電梯總數的30%。
車站的大廳進深27米,最高處達60米,橫向寬470米,呈兩端高、中間低的谷狀,頂部覆以曲面的金屬網架和玻璃,進入大廳,人們會看到玻璃上面京都的天空。建筑師意圖表現“境界存在,同時也不存在”的日本傳統美學理念。這個車站建成后的調查顯示,多數京都人對車站的設計持有異議,認為車站太巨大了,尺度和形式不適合京都。日本著名的城市設計專家西村幸夫說:“我個人不喜歡這個車站,可是如果制造出一個傳統的樓閣,也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在古時候,沒有這么大的車站,用傳統的材料不可能做這么大的一個車站。如果我們假裝材料是木頭的,其實還是假的。所以你如果只是想復制傳統的建筑樣式,這好像并不是一個正確的答案。”車站如今成了日本著名的旅游觀光景點,受到年輕人的喜愛。車站內坡型的樓梯成為京都年輕人聚集約會的場所。人們在車站內看不到列車,有些不知情者進來購物,吃喝玩耍一天,還不知道這是一個車站。
剛到京都,就撞上這樣一個鋼鐵工廠般的龐然大物,令我暈頭轉向,很是失落。我本以為我將擺脫物質主義的東京,以一種古代的方式進入古老的日本。后來稍事休息,我再次參觀了京都車站,它確實有強烈的震撼力,它給我的感受是空間上的勃勃野心而缺乏時間的深度,這是未來主義的建筑,與古老溫和的京都格格不入。也許原廣司的寓意是整體上的,但玻璃、鋼材、冰冷的大理石組成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幾何型結構以及密密麻麻的線條將其深刻的寓意解構了,一個不知情的日本朋友竟告訴我說車站可能是法國人設計的。京都車站給我一種被捆綁在飛向未來的宇宙飛船中的感覺,尤其是它的上半部,那些通向天空的線條、尺寸精確的大門、孤獨運轉著的電梯、光滑的平臺、抽象呆板的塑鋼雕塑,灰冷、荒涼、冷漠、杳無人跡,人類的未來。我走了一個上午,只碰到穿著工作服正在擦洗電梯的清潔工和一兩個幽靈般的過客。
離開京都車站,才發現京都并沒有那么夸張,氣氛溫和安靜,高樓大廈之間也夾雜著古老的街道和寺院,有些地方還是成片的。古老的街道,但說不上那是日本式的還是西方式的,風格含糊。一條河自南向北穿過城市,那是著名的鴨川。看起來水是清澈的,一些鳥在洗澡。河岸上有寬闊的大堤,日本朋友告訴我,這里每年都要搞“鴨川川床”的活動。“鴨川川床”就是在鴨川河岸上的納涼平臺。夏天開始的時候,在鴨川西岸上,臨川的先斗町的各家餐館就向河面搭起納涼床,點起古式的提燈。人們躺在岸上,眺望東山,飲酒唱歌睡覺。
我住在花見小道的家庭式旅館,紫旅館。這是半個月前在日本的朋友通過互聯網幫我預定的,只有兩天的空位,兩天后,我得搬到另一個旅館。這一代是老街區,歌舞伎聚集的地區,旅游熱點,旅館價格比較貴,一個房間每天9000日圓,包早餐。雖然是9000日圓,但是一個房間,你可以一個人住,也可以一家子住。順著四條向東,這是一條兩旁都是回廊的商業大街,有19世紀的氛圍,只是街上的人很少有穿和服的。轉進花見小路,就進入了京都傳統的街區,都是深色的兩層木樓房,一樓大都是酒吧、餐館、咖啡店的門面。下午,所有的門都關著,像是休息日,其實都在營業。后來我發現,日本的街道上沒有中國那種街道上的生活。在中國,生活從房屋里蔓延到街道上,人們在那里聊天、吃飯、洗衣服、養花,玩麻將,尤其是在次要的街道,街道只是家俱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過道。冷清無人關著門的街道是很不吉利的,沒有人氣。在日本,街道只是用來交通,生活在屋內進行,因此街道總是很安靜、冷清。從第三個小巷進去,遠遠地就看見了掛在木閣樓上的“紫”字,寫得龍飛鳳舞。也是兩層的樓房,按了門鈴,拉門猶豫不決地被撕開了,就像日語,這種語言的一句話只在最后的時刻你才知道它的意思是要肯定還是否定。一個笑容滿面的老婆婆彎腰垂手站在門口,她就是旅店的女主人吉田綾子,也是唯一的服務生。進門是一個兩平米的小天井,角落里擺著一盆植物。天井邊是一個鋪著席子的臺,客人在這里就要脫鞋,換了拖鞋再進去。一樓是浴室、廚房和主人的臥室,后面還有個稍大的天井,里面有水缸和一個神龕,一點植物,盆景般的小天井。主要的客房在二樓,三個房間和一個衛生間。有的房間門口放著拖鞋,這意味著里面有人。我的房間大約七八平米,床是榻榻米式的,干凈的被單上放著一套和服。榻榻米的功能就是睡覺,這樣的貼著地面是否意味著不安全感?榻榻米沒有上床下床這樣的含義。住這樣的房間,你得學會整日盤腿,站著是很不方便的。有兩處窗子,一處向著別家的瓦,一處向著街道。吉田綾子66歲,有兩個兒子,嫁到這家后就一直跟著丈夫開旅館,算起來也是三四十年了。她的聽覺已經非常靈敏,只要聽就知道客人需要什么,在做什么。她為我放好了洗澡水,請我去沐浴。浴室是公用的,總是吉田綾子放好洗澡水,再請客人去沐浴。晚上回來的時候綾子問我,早餐幾點用,我猶豫了一下,說7點到8點之間吧。她說,那就折中一下,7點半吧。我后來發現,明治維新以來以德國為榜樣的日本,時間觀念已經非常精確,看日頭估計時間,不戴手表已經無法生活了。我看到公共汽車站的時刻表,每趟車的抵達時間精確到分。奔波一天,我本來準備睡到自然醒,然后睡眼惺忪地迷糊一下再吃早餐的,現在卻緊張起來,想到7點半必須吃早餐,竟有點難以入寐了。7點25,房間里已經飄起煎魚的香味,電話響了,綾子咕嚕一陣,我猜意思是吃早餐的時間到了。還來不及衣冠楚楚,她已經敲敲拉門,抬著一盤食物,跪著進來了,將一碟碟食物擺好在比榻榻米略高的矮桌子上。每樣食物都是一小碟或者一小盅,剛好可以擺滿一只盤子,這樣的配置決不是讓你大吃大喝鋪張浪費,吃飽而已。食物包括,一罐米飯,一碟漬物(泡菜),一塊煎魚——旁邊配了一片紅葉,好看而已,不可吃的,一只冷雞蛋,一盅豆腐湯,一壺茶。擺好,吉田綾子悄然退去。次日的早餐,只有米飯不變,其他都換了。旅館周圍很安靜,街道的盡頭是一個禪寺,偶爾有汽車猛烈發動,然后一切歸于寂靜。我打開向著小巷的窗子,從來沒有看到人。有鄰居來拜訪綾子,是來向她借被子的,看來也是開旅店的。有一天出門時看見吉田綾子的丈夫,老人家,鞠躬,然后就不見了。拉門鎖起來,房間就消失了,看起來只是沒有房間的過道。知道那是房間,是因為房間的門口有時候放著拖鞋,兩雙的,三雙的。有時候一雙都不見了。拉門將房間隱匿起來,每個人都藏在自己的格子中。放在門口的拖鞋是一個符號,表示里面有人,但里面是誰是不知道的,拖鞋都是一樣的。而在中國,門就意味著住在里面的人的地位、尊卑。現代的兵營式建筑弱化了這一點,但只要可能,門一定會有暗示性。家庭旅舍并沒有供客人交流的客廳之類的地方,在中國,家庭旅館的話,大家可以在客廳里看電視,一起聊天,并參與店主人的家庭活動,比如幫他做飯。就是大賓館,也給人似乎知道別的房間里在做什么的感覺。有些旅客的門大開著,電視的聲音傳到過道上。開會的時候就更熱鬧了,那一段的過道上的門都開著,男女同志彼此在房間里串來串去。紫,溫暖,舒適,但是很隔絕,孤獨,神秘,互不相干。
京都從公元794年成為日本的首都,最初名為“平安京”。古代京都仿造的是長安和洛陽的模式,以朱雀大路為中心(寬度約85米)分為左京、右京兩區。南北約5.2千米,東西約4.7千米。那時候曾經擁有15萬人口。現在已經有1469472人(2005年的數據。如此精確的人口數據,在中國是永遠統計不出來的)。天皇居住在京都的北部,那里也是政府機關。京都是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政治中心。以天皇為首,貴族、官員、武士等都生活在這里。周邊地區是政府官員的官邸,宅院井然有序,形成官邸街。古代的記載說,京都“柳樹與櫻花交錯種植,如錦如緞”。到11世紀至12世紀之間,平安京才被稱為京都。中世紀的京都,市民社會非常發達,已經作為商業都市發展成日本最大的都市。在17世紀末,東京的西陣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知名的紡織業中心之一。明治時代由于政治原因,日本首都遷往東京,京都市民的抗議游行也沒能阻止天皇的遷移。皇室貴族,有經濟實力的市民,也陸續遷離了東京。
1944年夏天,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擔任中國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盟軍司令部請他提供了中國日占區需要保護的文物清單和地圖。梁思成同時建議盟軍對日本的兩個城市——京都和奈良也加以保護。由于梁思成的囑托,盟軍沒有轟炸京都和奈良。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法案,將京都歷史風土區和景觀地區加以保護,并對建筑物高度進行限制,除市中心區域外,大部分地區都控制在20米以下。許多區域保留著傳統木結構房屋,只是全部進行了防火防震的改造。京都沒有機場,地下鐵路也只有兩條。京都的建筑混雜著歷史上的各種風格,看起來已經不那么渾然統一了。從花見小道一帶的木結構的傳統民居到京都車站的鋼結構后現代建筑,京都給人一種魔幻的感受。
據說京都有4000多個神社,寺院有2000家以上。在日本總共有8.2萬多個神社,平均每1500個人就有一座神社。據日本文部省前些年的調查統計,日本信仰各種宗教的人近2.2億,超過了總人口數,因為日本民眾中有不少具有雙重或多重的宗教信仰,其中神道教信仰者有1億多人,佛教信仰者有9000多萬人。在公元5世紀的時候,中國已經盛行儒教,而日本依然是一個許多氏族和部落組成的原始社會,沒有文字,部落由酋長統治。神道教起源于氏族社會對自然力量的崇拜,以萬物有靈論為基礎,崇拜的是神靈化的萬物。古代日本人相信天上的神明會降落在大木、巨巖或高山上,并鎮守著它們。從高山、大樹、奇石、瀑布、海洋、田地、太陽、火、雷、各種動物到祖先的魂靈,都可以成為祭祀崇拜的對象,日本有“八百萬神”之說。很多神社供奉的是土地神。泛神崇拜是任何地方古代社會的特征,但日本卻保存到今天。公元五至八世紀日本吸收中國儒家與佛教學說后,佛教漸漸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明治維新(公元1868年)前佛教盛行,神道教只處于依附地位。明治維新后日本政府為了鞏固王權,興起廢佛毀釋運動,許多原始宗教也遭到鎮壓,將神道教加以體系化的改造,尊為國教,成為國家神道。神道教是日本獨有的宗教。神道教成為國家工具的同時,許多原始信仰依然保存下來。但今天在日本,神靈崇拜已經有著很現實的唯物的目的,商業的,職業的,升學什么的。在清水寺的時候,我花一百日圓求了一個簽,這個簽是與某月某日生的人有關,上面的簽語明確具體直接,而且分類,希望如何、結婚如何、健康如何、出入如何、訴訟如何、旅行如何、生孩子如何、考試如何、就業如何等等。例如生孩子,直接就說如果生的話就是男孩。在中國,簽語如果很具體明確的話,是不被信任的。寺院里的簽上寫著的都是朦朧詩,意義晦澀,求簽者就是抽到上上吉的簽,也不意味著吉祥如意的事就會很明確地告訴你,個人的領悟領會是很重要的。在京都,最魔幻的感受莫過于,在用高科技產品裝飾起來的現代化大公司旁邊,藏著矮小寒磣的神社,里面供奉著穿古代衣服的神靈,祭祀的方法也是千年延續下來的古法。西裝革履前往公司履職的職員目不斜視地匆匆走過,它們之間沒有絲毫歷史聯系性,時間不存在,只是些并列著的空間。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其實已經成為迷信科學的社會,東京大學的博士佐藤告訴我,迷信鬼神的人通常會被視為怪人。雖然有那么多宗教信仰者,但大多數人都受過西方科學知識的高等教育,真正迷信鬼神的人并不多,宗教并非生活的支配性力量,只是文化和習俗而已。
花見小道是京都藝伎較集中的地區,街上經常可以碰到。她們引人注目,濃妝艷抹,穿著木屐,姍姍而行,看起來就像唐朝的美人,害羞似的穿過街心,消失在某扇拉門后面。日本藝伎(Geisha)產生于17世紀的東京和大阪。最初的藝妓都是男子,他們在妓院和娛樂場所以表演舞蹈和樂器為生。18世紀中葉,藝伎職業漸漸被女性取代。藝伎的服務并沒有什么色情內容,服侍客人餐飲,陪客人聊天,也在宴席上以舞蹈、樂曲、樂器等表演助興。她們并非公然的妓女,但角色曖昧也是難免的,這種曖昧是男權社會造成的,賣唱賣笑賣藝被男子們想當然地認為也賣身。在江戶時代,花見小路一帶有藝伎服務的茶室多達700間,藝伎有3000人。現在沒那么多了,只有100名左右。日本全國現有的藝伎也不過數百人,相當稀奇,一出現在街頭就有許多旅游者指指點點,像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稀有動物。在京都,找一名藝妓陪一個小時的費用是每名客人500美元。有個叫巖崎峰子的藝伎曾在花見小路上生活過二十多年,2002年,她在美國出版了《藝伎:一種生活》,此書現已暢銷17個國家。她說,寫這本書是想告訴人們:藝伎是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女性自立的職業,而不是外界有人誤解的“娼婦”。
花見小道不遠就是東山。那山上有神社、寺院和古老的街區,是京都的旅游熱點之一。時值深秋,日本南方正是萬山紅遍的時候,許多人專程趕到京都來看紅葉。遠遠望去,紅色的山岡確實很美,但不太自然,樹種好像是搭配過的,顏色美麗的樹木被有選擇地成片種植,形成了強烈的效果。日本歷史上曾經大量砍伐森林,后來又重新種植,生態恢復得很好,但在恢復的時候,也許就有了許多人為的因素,根據審美和利用對植物進行了選擇。從前看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的畫,感覺日本的風景很整齊,也許就是自然被人為地設計過的原因吧。
八坂神社非常醒目,山門是橘紅色的,有一種卡通的效果。里面的廟宇密集地掛著許多白色的燈籠。祈愿的時候拉動一根連接著神龕的繩子。這是日本著名的神社之一,已經不知道它是哪一年建起來的,只知道在公元877年的時候,這個神社因為顯靈驅除了京都流行的瘟疫而名聲大振。從那時起,八坂神社就被奉為能除瘟祛病的寶地。許多人來到京都,都要參拜八坂神社,環繞著八坂神社,附近形成一個熱鬧的商業區。八坂神社最著名的,是每年一度的祇園節,當年瘟疫流行的時候,人們舉行祈求驅逐瘟疫的儀式,從八坂神社抬出66座神轎送往神泉苑。一千多年過去了,人們仍保留了這個古老的儀式。每年7月祭神儀式開始,要持續一個月左右才結束,是京都一大節日。作家川端康成小說《古都》中,描寫過祇園節的活動。
在京都,許多古老的節日持續到今天,每個月都有節日。1月4日,在下鴨神社舉辦初蹴鞠,表演者互踢鹿皮制作的球使其不落地。蹴鞠在中國唐宋之際十分流行,就是杜甫詩中說過的:“十年瞰鞠將雛遠,萬里秋千風俗同。”1月8日至12日,在惠美須神社祭祀惠美須,惠美須被日本人奉為商神。2月25日,在北野天滿宮舉辦梅花節。4月,春舞,以歌舞來慶祝春天。5月3日,流鏑馬神事,是祈求天下太平、五谷豐登的祭神活動。5月15日,葵節,葵葉裝飾衣服,游行,祈禱農作物的好收成。5月的第三個星期日,三船節,追憶古時王朝公卿以詩、歌、管弦等三船游樂的雅興。6月1日至2日,京都薪能,薪能就是在篝火映照之下,表演日本傳統能劇、狂言劇。7月1日至31日,祗園節。8月7日至10日,陶器節,節日期間,有陶器展銷會,在五條大街上擺滿了全國各地500多家陶器商店的攤位。8月16日,五山送火節,紀念阿彌陀如來佛。9月在大覺寺舉辦“觀月黃昏”,在大覺寺的大澤池上,乘船飲茶、吹笛、賞月,游吟俳句。10月22日,在平安神宮舉辦時代節。大約兩千人身穿著京都1100年中各時代的服裝,從京都御所出發,行走3小時抵達平安神宮。10月22日,鞍馬火節,意味著送走了秋天,迎來了冬天。11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嵐山紅葉節。12月1日,獻茶節。等等。
各神社與居民區是相通的,穿過八坂神社,就是古老的街區,青石板的道路,高矮參差的兩層木屋,被洗得干干凈凈。日本是個有潔癖的國家。我曾經看到有人搞自家門前的衛生,那不只是掃地而已,而是把大門兩邊墻上的每一條磚縫都抹得干干凈凈。這種情況,我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是第一次見到。日本到處都是非常干凈,散發著消毒液的氣味,體現出對物的愛惜崇拜,偶爾看到衣著可疑的人,那必是流浪漢。我在東京上野公園曾經經過一個流浪者的露天營地,他們也是收拾得整整齊齊。現代化是一種非常深刻的對人性的改造、對生活方式的規范。日本已經見不到中國普遍的那種自由隨便鮮活的臟亂差的現象,現代化的一個方面就是衛生化。但還是看得出來,過去的時代是不規范的,與四方盒子的現代房屋不同,過去的房屋蓋得歪歪斜斜,高高低低,順從著地勢,如同書法。底層大都是鋪子,上著門板,卸下來就是鋪面,很像云南麗江的大研鎮,或者拆遷以前的昆明。掛著各式各樣的燈籠,鋪子出售的都是旅游商品,店員熱情地向行人招徠著,請你品嘗他店里做的點心。旅游工藝品做得相當精致,色彩艷麗。有許多可以信任的百年老店,那就是一直都在從事某一行的老店。當然,許多店都是全國連鎖了。這令人有點失望,如果任何地方都有連鎖店,也就不那么珍貴了。游客摩肩接踵。驀然回首,歌舞伎們濃如櫻花,旋即逝去,坐著人力車走了。主道上游客摩肩接踵,但一拐進旁邊的支路,就即刻杳無人跡,風在吹。這種熱鬧有一種刻意的放松,似乎是集體的沒有靈魂的假面舞會。一離開旅游區,日本就回復到西裝筆挺,彼此彬彬有禮的氛圍中。
在古老街區的盡頭,是依山而建的清水寺。清水寺是公元798年由將軍坂上田村麻呂和延鎮和尚主持建造的。現存的大部分建筑始建于公元1633年。深黑色的圓木,將廟宇支撐在一處懸崖的邊上,被紅葉密集的樹林簇擁著。正殿前面是一個由139根木柱支撐的平臺,離地面有五十米,京都人將它叫做“清水之舞臺”。傳說如果從這個舞臺上跳下,沒有受傷,就能實現自己的愿望;如果死去,亦能成佛。因此來這里跳崖的情人絡繹不絕。為此,京都政府在1872年就頒布了跳崖禁令。本堂正殿供奉著十一面千手觀音立像,每隔33年才開放參觀一次,最近一次開放是在2000年。懸崖下有泉水流出,被人為地分為三股。飲泉水是游覽清水寺的重要項目,隨時都有人排著隊在飲水。據說這三股泉水分別代表愛情、生命、財富,想求什么就喝對應的一股。飲水是用帶長柄的金屬瓢,伸到巖石下去接來飲。每個人飲畢,就將瓢放到旁邊的金屬消毒柜里,這機器一兩秒鐘就可以將細菌消滅了。在這樣神圣的泉水邊上,使用高科技設備,看起來很是怪異,不自然,人們是信任那神圣泉水的力量呢,還是信任那科技產品的魔力?大殿里立著巨大的圓柱,看上去它們要生長幾百年才能長到這么粗。佛像被放置在房間的深處,都是小型的造像,看不太清楚。工作人員在不斷地抹拭著神龕、地板,使圣地產生了很高的光潔度,令人幾乎不敢投足。正殿門邊立著小牌子,寫著:土足禁入。土足就是赤腳。在日本,進入寺院一般都要脫鞋,脫鞋不是小事,它令進入寺院這件事情在身體上體驗著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和神圣感。如果平時不注意衛生的人,現在就很自卑,要么不敢進去,為自己氣味濃烈的腳而深懷內疚,也許回去后就下了決心,養成每天認真洗腳的習慣了。多年前在《外國文藝》上看過一篇日本小說,詳細地描寫穢物的排泄,當時很是不能理解,現在想起來,大約是被普遍的潔癖壓抑所致吧。站在清水舞臺上,可以看見京都,白花花的一片,就像正在熔解的銀子。
京都已經相當旅游化,似乎一切方面都很在乎旅游者的感受。在著名的商業大街四條通的東段,有著名的先斗町,就是飲食一條街,相當長,恐怕有一公里。叫做街,其實只是一條小巷,兩邊全是酒吧、飯館、咖啡店……一家挨著一家,每一家都精心設計櫥窗、門簾、招牌,美學風格看得出都是來自古代的詩歌、書法、繪畫的靈感。這條街在晚上看起來就像一個接一個的燈籠。精致而別出心裁的設計給人相當昂貴的印象,并沒有中國飲食排檔那樣的混亂熱鬧,便宜而不講衛生,鋪面會沿街渙漫出來,伙計們吆五喝六食客成群結隊。在這里,一切都在拉門后面靜謐地進行;街上看起來很冷清,其實正是生意紅火的街道,食客到了這里,立即被裝到各式各樣的格子里去。與中國飲食的熱鬧渲染、大吃大喝比起來,日本的飲食給人低語的感覺,飲食好像很不好意思,含著羞恥似的。日本有無數的格子,這是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份普通的便當,也是分為幾格。
先斗町過去不遠是京都著名的新京極市場,一個城市最能看出它的真相的地方,莫過于菜市場。日常生活的許多部分都可以包裝起來,但菜市場太日常了,與大地的關系太直接了,是很難包裝的。令我驚訝的是,我看不出新京極市場有菜市場這樣的地方,一切都被包裝好了,洗得干干凈凈,沒有一點泥巴,這是完全與大地斷絕了關系的市場,什么都被透明的塑料包裹著,就像無數的避孕套。像昆明那樣,許多蔬菜還帶著泥巴,在這里簡直不可思議。很多攤子都在賣漬物(泡菜)。泡菜在中國,大多數來自外祖母的瓦罐,這是私人家庭的秘方,但這里的漬物,統一包裝、有商標,我估計是大批量在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我想,這樣的菜市場恐怕已經沒有“新鮮菜”。在昆明,人們并不信任包裹在塑料袋里的食品,人們喜歡活著的魚、帶著露水的白菜、糊著泥巴的蔥和藕。如果你把泥巴完全去掉洗得干干凈凈的話,人們反而會懷疑你的藕是否已經死去多日,質量出現問題。在新京極市場的后面,是日本的農業,那是一條自動的流水作業線,大地的產物與私人的種植無關,一切都是工業化的,沒有什么直接來自自然,一切都經過工業的設計、洗禮。新京極市場的蔬菜水產部給我一種隔膜感。但你不必擔心小偷,人們可以把錢包放在外衣兜里。新京極市場最精彩的商店是賣刀具的店,各式各樣的刀具,發出灰暗的光,打制得非常精美,令人產生購買的欲望。但冷靜一想,買了干什么呢?在中國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專業的刀具店。
旅游是全球化的良藥,對治療舊世界的臟亂差,自然隨便,不講衛生相當有效。旅游被當做了標準,永不撤銷的檢查團,居民普遍自覺地討好游客,這其中當然有商業的動機,年積月累,是否會令城市完全喪失自己黑暗的私人生活?一切都很光明,彬彬有禮,熱情好客,干凈衛生,整個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旅游紀念品,一覽無遺,一切都為旅游而設計,節日、工藝品、宗教活動、飲食、旅館、交通、藝術,也許還包括做愛……在這一點上,我以為東京比較自然,好像并不怎么在乎旅游者,有許多黑暗、不適合觀光的地方,愛看不看,就這么的。
南禪寺建于1289年。門樓很大氣,渾厚,據說那就是唐的風格。但頂很沉,像是重量過度的帽子,我發現這是因為建筑的下部沒有中國建筑那種隱約的楔型。土木結構和楔型使建筑穩如泰山。南禪寺的門樓給我頭重腳輕、搖搖欲墜的感覺,其實它已經挺立了幾百年。黑烏鴉在古老的屋頂上盤旋,很像宋徽宗的一幅畫。它們已經非常熟悉這個頂。黯淡的建筑,被時間磨出細膩的光。購票,每個人發一個塑料袋,脫了鞋裝進去,各人自己拎著,像是兜著自己的不良紀錄似的。登樓遠眺,正是日落時分。大地蒼茫。蒼茫是沒有國界的,這就是詩歌可以隨便越境的原因,頗有回到長安的感覺,就想起那兩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不會是脫掉鞋寫出來的吧。我對進門就要脫鞋很不適應,這個行為使生活忽然中斷,進入了一個正式場合似的,隨便自然的生活忽然結束,它們很不衛生。古代中國的建筑被日本學習模仿,學習總是容易將對象升華、拔高、模式化、楷模化。原來的東西就離開了它的日常氛圍和基礎,較為神圣了。在日本,古代的建筑物總是給人拔地而出的感覺,缺乏那種日常親和扎根于大地的東西,也許因為當時就是在頂禮膜拜的心態下建造的。但日本學習西洋的建筑并沒有這種感覺,西洋建筑的基本功能是實用,美只是裝飾性的。而中國建筑的基本結構不僅僅在于實用,也暗示著中國人對宇宙人生的理解,具有象征性的含義。例如飛檐、斗拱、柱子,不僅僅是建筑結構的需要,有許多精神性的“多余”,暗示著世界觀。什么事情都是天人合一的,既要有實用的天,也要有文化的人。中國建筑到了日本,也許其文化的部分被夸張做作了,所以在日本,那些學自中國古代的建筑,更有壇的感覺。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瓦,燒制得厚大、堅固,泛著青光,用瓦釘鉚接起來,就像是德國人的鋼盔。蓋在屋頂,不會長一根草。已經不是漢語中所謂的“片瓦”,而是工藝品。瓦其實有著大地的含義,依賴、扒著大地。棲身其下的感覺被取消了,瓦成為升起來的,成為向上的東西。有的瓦重達13公斤。在高處看,日本的頂相當荒涼,太光滑了,沒有灰塵,不生苔蘚,更沒有墻頭草。中國的瓦表面很粗糙,接縫用的是泥巴,所以幾個雨季過去,屋頂就長出草來。尤其是在南方,屋頂四季開著花,蝴蝶飛出飛進。當然,這個景象已經是長河落日了,中國現在連瓦都不要,水泥平頂,那就更荒涼了。
南禪寺旁邊有著名的哲學小路,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曾經住在這一帶,散步,思考東方式的存在主義。他是日本著名的哲學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曾經影響日本。普通的散步小路像馬克思的那條地毯一樣被升華了,成為熱鬧的旅游點。到京都旅游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去參觀這條哲學小路。被楓樹簇擁的碎石路,順著一條溪流。路上的某一段出現了一個小寺,這個寺是構思的結果。寺中間圍著一棵楓樹,看上去這個小寺的主持或許所供奉的就是這棵樹。這是一個創意,也許暗示著楓樹就是已經得道的高僧吧。樹冠已經撐得比小天井更大,紅葉在墻外面落了一攤,美麗凄涼。很是動了腦筋的設計。日本的園林一般都是這樣,設計的痕跡很明顯,似乎并不在意“道法自然”,而是升華于自然。而在中國,園林中不自然的痕跡一定是要想辦法遮掩掉的。一切都要看起來自然天成的樣子,所謂師法造化,鬼斧神工。游客不敢碰那些神圣的落葉,這場景就像楓樹被培養成了模特兒,正在走臺呢,大家只是嘩嘩地拍照,嘆息。
我在紫旅館住了兩個晚上,第三天搬到另一旅館去住。這個旅館在熱鬧的四條通大街北端的一條小街上,日本普通的街區,沒有旅游色彩,冷漠,行人目標明確匆匆而過,走路也像是坐在汽車里,握著方向盤似的。慢吞吞、東張西望的人沒有,有,那就是我獨一個,中國來的野蠻人。旅館是一棟水泥和玻璃組合的大樓,我想描述它的樣子,很難啊,已經想不起來了,也許會亮燈的集裝箱比較形象吧。住店的大多是西裝革履者。在日本,西裝主要是工作服,沒有中國那么當回事情,許多會議通知上寫著,這是正式場合,要求一律穿西裝。旅館每晚6000日圓,包括早餐。房間基本上是一個模壓的白色塑料便當盒。分成幾格,床、桌子、電視機、冰箱、衛生間和過道兼更衣處。幾個電器說明上醒目地寫著“警告”字樣。日本人在設計利用空間上真是一流的,如果你習慣分類而不是自由散漫,那么這個睡覺的小盒子依據設想的身體健康,非侏儒、非巨人的理想人及其工作后休息的需要設計得相當合理,小衛生間甚至可以坐在浴缸里泡澡。把門關好,一滴水都漏不到房間里去。床很寬,一米八的大床,不是榻榻米。如此彈丸之地,竟有三個鏡子,可見儀表對于工作是多么重要。但這樣的房間對于我實在太小了,幾乎無法打開箱子。住這種房間,你最好只帶了公文包。科技含量很高,全面消毒,雪白,一塵不染的衛生間,一塵不染的床單,干凈得你就像是爬在鏡子上的一只蒼蠅。這房間就像一些配件,人是這些配件的主體,住在里面,人就像安裝好的機器,嚴絲合縫,進入了一個人類車間的巨型傳輸帶。早餐非常簡單,羊角面包,生菜,咖啡,冰水,完全的西式,排隊去取,住這個店都是奔那杯咖啡來的,是作為旅店的廣告的名牌咖啡。用早餐的人都像是正在工作,有人頭頂墻壁埋頭吞咽。每個人都是西裝筆挺,里面的淺色襯衣漿洗得很硬,把柔韌的人體襯托出精神百倍的樣子。西裝是為工作設計的,在中國,人們其實以為它與工作無關,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吃罷,大家自覺收拾干凈,把杯碟放回去。這樣的吃法,你不能吃得太狼藉,否則很難收拾,很難看,就像進了寺廟的大堂而沒有脫鞋。集體的講究、衛生使自由散漫的行為看起來就是一雙臭腳。
早晨9點準備離開京都,前往大阪機場回中國。京都到大阪機場,得從京都車站乘高速列車,行程約一個小時。朋友說好10點來接我,過了10點一刻還沒有來,很焦慮,擔心乘不上車,還有一堆行李。后來知道他病了,不能來了。我只好自己去機場,比手勢,寫繁體的漢字,很容易就打的士到了京都車站,很容易就買到一張前往大阪機場的直達票,很容易就上了車,很容易就到了飛機場。現代化其實就是讓生活越來越方便、容易,最后只要嵌個按鈕就萬事大吉。我原來以為這樣重大的事故,在外國,時間有限,語言不通,越過那么多錯綜復雜的線路在某次航班的機艙中找到座位,其細節夠我寫個中篇小說,卻無話可說,很快搞定。唯一的記憶是,在買票的時候,售票小姐寫個字條給我看,兩組詞,自由席,指定席。意思是問我要買哪個,我想都不想,就指著自由席。自由席,在中國不就是隨便亂坐么?指定席是領導和要人坐的。自由席!OK!2300日圓。拿到票一想不對啊,朋友說到機場只需要1830日圓啊,怎么貴了那么多?進到車站,才發現自由席只有一節車廂,里面空空如也,連我就兩個乘客。其他車廂都滿了。指定席就是必須對號入座,一人一格,自由席你可以想坐哪里坐哪里。自由其實是很貴的東西。
于堅:1954年生。1984年畢業于云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獲魯迅文學獎。主要作品有:長詩《0檔案》《飛行》;詩集:《詩六十首》《對一只烏鴉的命名》《于堅的詩》《便條集》《詩集與圖像》《只有大海蒼茫如幕》《在漫長的旅途中》;散文集:《棕皮手記》《人間筆記》《棕皮手記·活頁夾》《麗江后面》《云南這邊》《老昆明》《暗盒筆記》《火車記》《相遇了幾分鐘》等。
責任編輯 王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