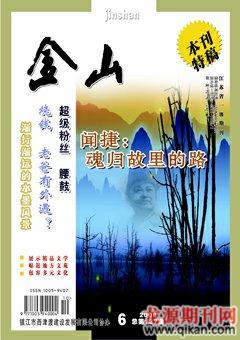獻(xiàn)給話劇百年的一瓣馨香
蘇 民
編者按:
話劇藝術(shù)家戴涯先生,1909年6月30日生于鎮(zhèn)江,原名戴忠勳。大學(xué)開始熱愛話劇,從1933年和唐槐秋創(chuàng)建中國(guó)旅行劇團(tuán),任副團(tuán)長(zhǎng),兼導(dǎo)演、演員,到1973年逝世,四十年對(duì)話劇藝術(shù)矢志不渝。戴涯一生,名副其實(shí)是話劇人生。
中國(guó)國(guó)電集團(tuán)諫壁發(fā)電廠原廠史編輯,鎮(zhèn)江市雜文學(xué)會(huì)會(huì)員朱志新先生,曾在2007年創(chuàng)作并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劇魂歸天涯》一書,詳盡記錄了戴涯一生。
今年是戴涯先生誕辰100周年,為懷念這位中國(guó)話劇開拓者、表演藝術(shù)家,本刊特轉(zhuǎn)載《劇魂歸天涯》一書的序言和書中丁尼的《亦師亦友憶戴公》,既慰前人,又勵(lì)后人。
戴涯先生長(zhǎng)我十七歲,倘若他仍然在世的話應(yīng)該是九十七歲高齡了。今天,對(duì)于不熟悉中國(guó)近代話劇歷史的中青年來說,戴涯這個(gè)名字大約是陌生的。因?yàn)樵缭谏蟼€(gè)世紀(jì)的1957年,他在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演完郭老的名劇《虎符》以后,因被錯(cuò)劃為“右派”,就從此被迫離開了他難以割舍的話劇舞臺(tái)。“文革”浩劫以后,1980年北京人藝為他平反昭雪時(shí),他已于1973年含冤病逝于家鄉(xiāng)江蘇鎮(zhèn)江。
戴涯在北京人藝工作的時(shí)間雖然只有五年,但北京人藝院史上肯定要記上他的名字。因?yàn)樗松詈笠淮蔚奈枧_(tái)創(chuàng)作實(shí)踐,就是參加了重要?jiǎng)∧俊痘⒎返难莩觥_@出戲是北京人藝在話劇民族化的試驗(yàn)探索方面取得輝煌成就的第一臺(tái)奠基劇目,戴涯在演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魏安王。導(dǎo)演焦菊隱對(duì)他的表演很滿意,并向大家傳達(dá)了劇作者郭沫若的評(píng)價(jià)——“戴涯演的魏王是郭老所看到的幾次《虎符》演出中最好的魏王。”
戴涯還有件寫劇本的事,留給我的印象很深。那是六十年代初,他被解除勞動(dòng)教養(yǎng),從農(nóng)場(chǎng)回到了北京人藝宿舍的家里。沒有工作,沒有朋友,在“左傾思潮”仍然風(fēng)行的年月,他也不便和朋友們交往,其處境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下,他竟然獨(dú)自關(guān)門寫出一個(gè)劇本《鄭成功》。他設(shè)法請(qǐng)人轉(zhuǎn)告北京人藝黨委書記趙起揚(yáng),請(qǐng)求面談。趙聽到后就來看他,他十分激動(dòng)地拿出劇本說:“我一不能忘情戲劇,二不能忘情劇院,這才下決心獨(dú)自寫成這個(gè)劇本。不能找別人,只能找你來談?wù)勎倚睦锏脑挕┱?qǐng)你抽時(shí)間看看,能不能多給我提些批評(píng)意見。”趙答應(yīng)了。過了幾天,趙認(rèn)真讀了劇本,來找戴涯談自己的意見,戴在興奮感激之余按捺不住地試探著問了一句:“有沒有可能修改好了由劇院上演?”趙也很實(shí)在地回答說:“看劇本、提意見,是我個(gè)人的行為,我可以負(fù)責(zé)。而劇院能否上演,必須經(jīng)過黨委、藝委討論,我無權(quán)個(gè)人作出答復(fù)。但我可以對(duì)你說一個(gè)想法,即或有上演可能,你也要為劇院著想,作者署名恐怕不能寫你的名字。”戴涯聽后激動(dòng)不已地說:“沒關(guān)系,要是能上演,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我對(duì)戴涯先生了解不多。知道戴涯出生于江蘇鎮(zhèn)江的一個(gè)大戶人家,四歲喪父,十二歲喪母,是祖父祖母將其撫養(yǎng)長(zhǎng)大。上大學(xué)時(shí)曾組織過金陵大學(xué)劇社。大學(xué)畢業(yè)后,經(jīng)田漢先生引薦結(jié)識(shí)了長(zhǎng)自己十一歲的中國(guó)早期戲劇活動(dòng)家唐槐秋。由于志同道合,于1933年10月4日中秋節(jié)那天,他們二入在戴的家里徹夜飲酒長(zhǎng)談,共同謀劃,取“讓人生在戲劇中旅行,讓戲劇在人生中旅行”之意,決定組織“中國(guó)旅行劇團(tuán)”,由唐槐秋任團(tuán)長(zhǎng),戴涯任副團(tuán)長(zhǎng)。從此誕生了中國(guó)話劇史上第一個(gè)民間職業(yè)劇團(tuán),推動(dòng)了中國(guó)話劇藝術(shù)的職業(yè)化,并在中國(guó)舞臺(tái)上首演了曹禺先生的《雷雨》。他們旅行演出的方式使話劇在中國(guó)各地傳播,擴(kuò)大了對(duì)青年學(xué)生的影響,當(dāng)然也包括了話劇在觀眾中的普及。1936年,戴涯與曹禺、馬彥祥一起創(chuàng)辦了“中國(guó)戲劇學(xué)會(huì)”劇團(tuán)。十余年間,他帶領(lǐng)這個(gè)劇團(tuán)轉(zhuǎn)徙各地演出,其中一段時(shí)間在西安,大家在生活上幾乎陷入到朝不保夕的地步。為了攏住人心,保住劇團(tuán)不散,戴涯變賣了隨身攜帶的私產(chǎn)以維持劇團(tuán)的生存。當(dāng)時(sh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臺(tái)下醬菜稀飯,臺(tái)上英雄好漢。”戴涯曾經(jīng)這樣回憶:“演戲再難,還是要演,我這輩子注定就是話劇人。畢生獻(xiàn)身話劇,雖九死而不悔,縱再難,不言退。”
這樣一位把自已的青春全部奉獻(xiàn)給話劇舞臺(tái)的藝術(shù)家,這樣一位為了話劇事業(yè)、為了保住劇團(tuán)生存慷慨捐出自己家產(chǎn)的藝術(shù)家,卻于1957年,正值他藝術(shù)人生趨于成熟、生命力也最旺盛的48歲好年華的時(shí)候,被一頂“右派”帽子剝奪了他上臺(tái)演戲的權(quán)力,使這位自誓要做話劇人的好演員只有借寫劇本以抒解自己不言退的殘志。令人悲憤的事情還在繼續(xù),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惡浪又兜頭把戴涯強(qiáng)令遣回鎮(zhèn)江老家,由當(dāng)?shù)卣右怨苤啤S诌^了告天天不應(yīng)、問地地?zé)o語的七年,戴涯對(duì)他的兒女們說:“我的苦,你不懂。”1973年3月1日,這位老藝術(shù)家走完他的人生苦旅,享年不過64歲。
本書作者朱志新先生是鎮(zhèn)江諫壁發(fā)電廠的一名職工(現(xiàn)已退休),業(yè)余喜歡寫作,酷愛話劇,尤愛北京人藝的戲。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他得知了戴涯與他同是鎮(zhèn)江人,進(jìn)而又得知戴涯的悲慘遭遇以及他對(duì)中國(guó)早期話劇的貢獻(xiàn)。出于鄉(xiāng)誼、出于對(duì)話劇藝術(shù)的鐘愛、出于對(duì)戴涯先生的無限同情和惋惜,朱志新產(chǎn)生了為戴涯著書立傳的決心。為此,他利用業(yè)余時(shí)間采訪戴涯先生的子女、親屬和能找到的了解戴涯(哪怕一點(diǎn)一滴)的所有人,翻閱了大量的文字資料,甚至自己掏錢召開關(guān)于戴涯的座談會(huì)……總之,讀罷他的書稿,我為他迎難而上的毅力而佩服,為他鍥而不舍的執(zhí)著而贊嘆,為他與戴涯傾心的鄉(xiāng)誼之情而感動(dòng)。
2007年是中國(guó)話劇百年,這本書能夠問世,是對(duì)中國(guó)話劇百年奉上中國(guó)話劇人的一瓣馨香,也是對(duì)戴涯先生在天之靈的莫大告慰。
(作者簡(jiǎn)介:蘇民,原北京人藝副院長(z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