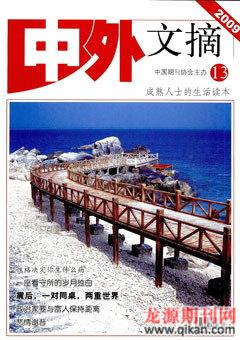芒然的命運
2009-08-13 09:47:48邊芹
中外文摘
2009年13期
關鍵詞:記憶
邊 芹
他站在里昂火車站的月臺上,沒有行李,沒有名字,沒有軍人身份牌。一輛從德國開來的戰俘車剛剛經過,那是1918年2月1日。
有人在空蕩蕩的月臺上發現游魂似的他,像沒人要的包裹,不知從哪里來,也無處投遞。他一言不發,顯然對過去已無記憶。
他就這樣進了瘋人院,在反復追問下,他嘴里吐出一個姓:芒然,又吐出一個地址:維希市的一條街。于是他被轉到維希市瘋人院。但人家去找了,維希沒有叫芒然的,也沒有這條街。
在一戰的末日屠戮中,很多人連懼怕死亡的時間都沒有,就數以百萬奔赴黃泉;還有不知去向的,幾十萬尸首難尋;更多的是殘廢,一個村用兩條腿走路的青壯男人所剩無幾;最諱莫如深的則是無以數計發了瘋的,跨越“界河”遠比人們想象的容易。多少無名戰士的尸體沒人認領,同時幾十萬家庭不知親人的歸宿。但他非同一般,他是活著的無名戰士。究竟什么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讓他奔逃得連記憶都放棄?
瘋人院在報上登照片讓人認領,最后只剩下他沒被認走。沒有人認嗎?不是。認的人太多了,失去兒子的母親、喪失丈夫的女人,都想在他身上找到安慰。殘廢軍人撫恤金,在那個年代,是很多孤寡女人的生存保障。但核對下來,沒有一家對得上。
最后剩下五十來家無論如何不肯放棄。一個漫長的核對過程開始了,醫生對他做7各種測試。不說話的他,變成了一連串可供核對的數據。而他躲進那個我們永遠沒有答案的世界,并不明白外面的喧鬧是為了什么。……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現代裝飾(2021年6期)2021-12-31 05:29:04
小學生優秀作文(高年級)(2021年10期)2021-11-02 03:05:24
華人時刊(2020年15期)2020-12-14 08:10:44
學苑創造·A版(2020年10期)2020-11-06 05:21:26
華人時刊(2017年13期)2017-11-09 05:38:52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6年27期)2017-06-03 23:21:17
絲綢之路(2016年9期)2016-05-14 14:36:33
新湘評論·下半月(2016年4期)2016-05-05 22:12:41
新湘評論·下半月(2016年4期)2016-05-05 22:12:41
海外文摘(2016年4期)2016-04-15 22:2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