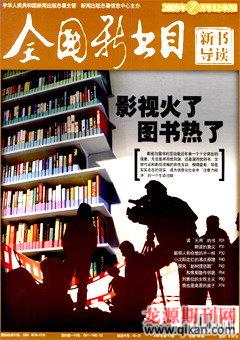陳誠與林彪的較量
王曉華 張慶軍
黃埔軍校是中國現代軍事的搖籃,為民國時期的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杰出的軍事人才與高級將領。本書生動記述了黃埔軍校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所留下的深深烙印。作者還以文學手筆記述了黃埔將領的一些經典戰役,展示了國民黨和我軍高級將領中出身黃埔的將領的指揮作戰特色和輝煌戰績。
陳誠與林彪,同為黃埔軍校出身,分屬國共兩黨,其結局雖然有所不同,但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在各自的陣營中資歷不深,相貌不出眾,個頭很矮小,卻都做到了高位,沒有出色的才能和特殊的功績是不可想象的。
兩人都是南方人,陳誠為保定軍校八期畢業,林彪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在軍校的學習中,成績平平,絲毫沒有表現出有什么驚人的才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更無法讓人預測出其飛黃騰達的命運。對比他們后來的巨大成功,以至于我們不能相信他們在學生時代竟如此默默無聞的度過。
北伐結束后,兩人開始分道揚鑣。在兩三年之內,陳誠由營長晉升為十一師師長,在新軍閥的內戰中,為國民黨屢建功勛,林彪也在三年左右的時間里,從南昌起義時的連長晉升為紅軍主力軍軍長。火箭般的躥升還遠沒有結束,隨后,陳誠晉升為王牌軍十八軍軍長,自此,土木系初建規模(十一師與十八軍合稱土木系),林彪在同一時期晉升為紅軍第一主力,紅一軍團總指揮,成為年輕的“紅軍之鷹”。
陳誠的部隊兵精馬壯
1933年2月,蔣介石出動50萬大軍,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陳誠率12個師為中路,朱紹良率8個師為右翼,蔣鼎文、蔡廷鍇率8個師為左翼,采用“分進合擊”戰術,氣勢洶洶,向根據地撲來。
戰前蔣介石召開軍事會議,本來也是為了勸將不如激將,有意識夸贊了林彪幾句:
“我是要特別提醒在座諸位,要重視那個林彪,不要以為他在黃埔默默無聞,不顯山不露水的。當年我是與他有過接觸的,讓人覺得胸有丘壑,這幾年交戰,更讓我有這個感覺,是當代韓信。諸位此行出戰,萬萬慎重,不要打虎不成反被虎傷。”
陳誠忍不住地站了起來,“校長提醒的是,不過據學生以往與林彪作戰的體會,那林彪也并非如何了得,總是避戰、怯戰,不敢與我軍正面交鋒。學生不才,愿為此次剿共先鋒,將那林彪捆于馬前,綁著來見校長。”
蔣介石就喜歡陳誠這股沖勁。大戰之前,要的就是這種必勝的信念。
在對紅色根據地第三次“圍剿”中,陳誠的部隊未受損失,并乘機收編了第五十二、第五十九、第十四、第四十三等4個師,加上原有的第十一師,共是5個師、29個團。
他與已故行政院長譚延愷的女兒譚祥結婚大媒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齡。陳誠和蔣介石的關系更加密切,志高氣昂,不可一世,企圖包辦“圍剿”任務。
陳誠指揮的中路軍12個整師,16萬人,其中包括后來名列國民黨“五大主力”的第18軍,它下轄三個基干師,分別為十一師、五十二師、五十九師,其中又以第十一師為全軍之冠。這支隊伍實力不同凡響,兵精馬壯,器械精良,那時候機關槍剛進中國,而該部已經普遍配備上了。
紅軍剛經過整編,林彪升任為紅一軍團軍團長,成為紅軍最年輕的軍團長,與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構成了紅一方面軍的兩大主力。為了加強這支紅軍主力的領導力量,中央又調聶榮臻為政委,陳奇涵為參謀長,這兩人都是從黃埔出來的,聶榮臻與林彪有師生之誼,而未來的共和國上將陳奇涵則擔任過黃埔軍校少校中隊長,后轉到地方上工作,蔣介石一直沒有忘記他,大革命失敗后還從南京專門寫信給陳奇涵,邀他擔任侍從室主任,這可是非同小可的誘惑,但陳奇涵卻不為所動,冷冷地拒絕了。
紅一軍團下轄的兩個軍分別是紅四軍和紅十五軍,主要領導人也大都是黃埔同學,紅四軍軍長王良是黃埔六期生,參加過秋收起義,只是不久前在漳州戰役中犧牲。而該軍政委羅瑞卿則是王良同班同學。
紅十五軍軍長黃中岳雖不是黃埔出身,但該軍的政委卻是正宗地道的黃埔一期生左權。
他們也盼望著和陳誠交手,試一試孰高孰低。
林彪這一仗打得好
“風煙滾滾來天半”。敵三個縱隊向中央蘇區壓了過來,且相互靠的很近,過于集中,難以各個殲滅。
林彪卻很謹慎,保持著低調。兩道濃眉緊鎖,滿臉陰云密布。林彪的老部下黃永勝回憶打陳誠時說:
“那時部隊求戰熱情很高,但林總卻常說他下不了決心,因為我們過去對付的都是國民黨雜牌軍,十一師才是蔣介石精銳中的精銳,是王中王。許多人都不服氣,爭著要打十一師。后來我們才懂得,林總用的是激將法。”
把部隊的火氣扇旺了,林彪這才吐口,說是先拿五十二、五十九師祭旗,打贏了才有資格打十一師,此語一出,紅一軍團上下摩掌擦拳,恨不得立刻開打。
兩軍對壘,各展手段,陳誠也不是浪得虛名,行軍布陣極具章法,部隊首尾呼應,左右照顧,紅軍竟一時無懈可擊,尋不出破敵良策。
時任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與紅軍總司令朱德,密切注視敵軍動向。于是決定佯攻南豐,吸引敵主力增援南豐;紅軍主力埋伏于黃陂、登仙橋一帶的高山密林中,待機破敵。
周恩來故意將一封假敵情電報落到敵人手里。電報內稱:
我工農紅軍正圍攻南豐,旦夕可下,唯樂安之兩師白軍,若向河口、黃陂前進,則我紅軍不特無法攻下南豐,本身亦感至大危險。萬望派人監視此兩師敵人,果其南來,即迅速報告,予當率兩團竭力抵抗之。
這一手果然奏效,陳誠急電第五十二、五十九師,讓其速奔黃陂,先吃掉紅軍掩護部隊,然后相機解南豐之圍,里應外合,形成夾擊紅軍之勢。
敵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得知紅軍只有“兩團”兵力打阻擊,求戰心切,令第五十二、五十九兩師由樂安地區取道永豐、樂安向宜黃南部前進,自己率第十一師從宜黃南下,兩軍在黃陂回合后,一起向廣昌、寧都進攻,企圖堵擊我主力紅軍撤回中央根據地的歸路。2月26日拂曉,敵兩個師,在李明統一指揮下,兵分兩路,中隔大山,相距10余里,向東南開進。
敵人終于露出破綻。周恩來、朱德立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在黃陂以西、登仙橋以東地帶側擊并消滅來敵。當晚,林彪、聶榮臻、羅瑞卿、徐彥剛率領4萬多紅軍,冒雨分別向伏擊地點開進。經過強行軍,部隊在天亮前,都潛伏到預定地點。
中午時分,山間晨霧彌漫,峰巒皆隱。雨停了,太陽在濃厚的云層里時隱時現。派出去的偵察員回來報告:“敵五十二師按正常速度進入我陣地!”
指揮部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林彪命令:“告訴部隊,注意隱蔽,沉住氣,讓敵人往里走!”
這時,溝口人喊馬嘶。敵第五十二師4個團在師長李明的帶領下,大搖大擺地進入伏擊圈。這時只聽見“砰砰”幾聲槍聲,軍團指揮部發出總攻的信號。霎時間,幽靜的山谷像天崩地裂一般,爆發了震動山岳的槍炮聲。迫擊炮彈和機關槍像狂風一樣卷下山去。激動人心的沖鋒號響徹山谷,伏兵吶喊著如山洪爆發一樣,向山下狂瀉。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擠在狹窄的山谷中,亂成一團,自相踐踏;敵師長李明受了重傷,做了俘虜,不久斃命;一個師就這樣被報銷了。
敵第五十九師也陷入絕境,被紅軍分割包圍,后隊已被截斷。師長陳時驥見勢不妙,急忙寫信向李明求援,信稱:文獻兄(李明字):弟無能,欲本日午后一時失利,現部隊已潰散,弟僅率士兵數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許之山莊中,請迅速援助為盼。弟陳時驥。
29日晨,陳時驥企圖突圍回樂安,因迷失方向,抓來一個農民為向導,不料此農民將其引致登仙橋附近,為紅軍圍殲,陳時驥被俘。
李默庵奉令率所部趕往登仙橋救援,當他到達登仙橋時,第五十二、第五十二兩個師已被紅軍消滅。
大戰在即,林彪表現了他那特有的細心和審慎,靜如山岳聳峙,動如雷霆奔涌,這是他的作戰風格。他再一次親自檢查后將偵察員放了出去,并一再叮囑部下膽子要大,動作要猛。這種大局著眼,小事著手的工作作風,是一名出色的指揮員必須具備的素質素養。
接到五十二、五十九師相繼被殲的消息,陳誠抱頭痛哭。蔣介石也很不滿,“陳辭修太輕敵了,我早提醒過他,林彪很狡猾,不易對付,如今果然付出了代價。”于是口授了一封電報,不免有幾份責備的口氣,其中有語云:“接誦噩耗,悲憤填膺。”一向與陳誠不和的黃埔一期生,軍中驍將陳明仁落得看笑話,私下里和人開心地道:
“那陳小鬼的能耐就是如何討得校長喜歡,眼高手低,輕視天下英雄,林彪這一仗打得好,好歹殺一殺陳小鬼的傲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