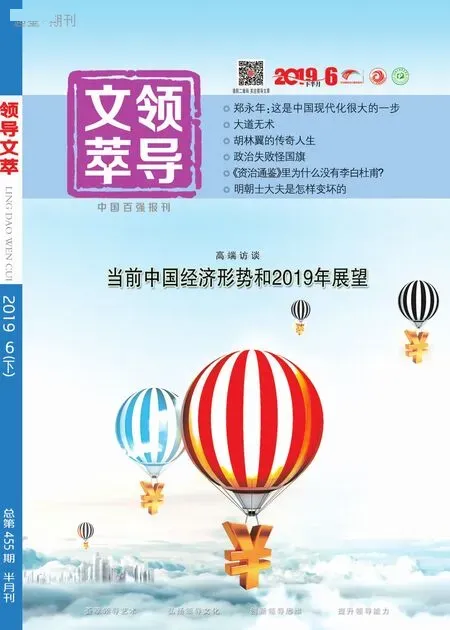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
張 彥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花園城市”萬隆舉行了劃時代的亞非會議。事情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我作為這一重大國際事件的親歷者之一,昔日重溫,感慨萬千。
“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前后
當時正值“二戰”結束后,亞非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殖民主義勢力則力圖恢復舊有秩序。形勢嚴峻,新興國家越來越認識到,大家必須彼此團結互助,一致對外,才能維護自己的勝利果實,維持地區的和平穩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代表近三分之二世界人口的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首次在沒有殖民主義國家代表參加的情況下聚會于萬隆。
新中國這時才誕生六年,又處于世界兩大陣營“冷戰”的氛圍中。來自美國的封鎖制裁接踵不斷,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圖謀“反攻大陸”。很顯然,亞非會議勢必成為兩大陣營角逐的一個特殊舞臺。在收到錫蘭(今斯里蘭卡)、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五個發起國的邀請后,中國政府立即決定積極參與這個重大的國際會議,爭取改變自身的國際環境,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中國派出了以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為首的大型代表團。我當時是中國對外宣傳刊物《人民中國》的記者,也被派前往報道這一會議。本來我應該隨記者團一起,乘印度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經香港前往印尼首都雅加達。印尼駐華大使還特別在北京萃華樓飯莊設宴,為我們記者餞行。頻頻舉杯的歡樂盛況,至今仍歷歷在目。但是,臨行前,周恩來總理接到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訪緬,商談兩國之間的一些問題;此外,還要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于是,代表團決定,與記者團分成兩路,改經仰光前往雅加達。我和新華社記者李慎之同時兼任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參與一些文件的起草和翻譯工作,也就跟著周總理隨代表團走了。在記者們離京赴港之前,我們彼此相約:“雅加達見!”
不料,4月11日,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民航機在沙撈越上空爆炸事件。中國代表團成員和中外記者共11人及五名機組人員遇難。
消息報到昆明,周總理立即指示:外交部要將這一情況火速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中國赴萬隆會議代表團工作人員,要他們立即向港英當局提出交涉,請香港方面一定要保證有關人員的安全。他還指示外交部,立即召見英國駐華代辦,請英方采取措施。
此前,4月10日,鄧穎超即已寫信提醒周恩來,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事件發生后第二天清晨,周總理復信:“來信收閱,感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之仗,一切從多方面考慮,經過集體商決后行。”
也正因為隨代表團臨時改道,我才躲過了此劫。但當時紀律嚴格規定,代表團的行蹤絕對保密,除了夫妻,不得告訴任何人。因此,飛機爆炸的消息一出來,在遇難者名單公布前,知道我參會的親友無不捏了一把汗。當時中國民航還沒有遠程飛機,我們另租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飛機“空中霸王號”。中緬之間還沒有正式航線,是試飛以后才啟用的。一出國境,緬甸政府就派來兩架戰斗機于左右護航。在仰光期間,為了確保安全,代表團有人輪流值班守護飛機,不許任何人接近。
在由仰光飛往雅加達途經新加坡時,因氣象問題必須降落歇息。當時新加坡與中國尚無外交關系,而是延續著與臺灣的關系。怎么辦?機長與地面聯系后,對方終于同意降落,并在機場等候。
落地以后,代表團一行引來機場眾多群眾的驚訝和觀望。沒想到,機場當局派人前來,表示歡迎周總理到貴賓室休息。此時,周總理毫不猶豫地帶領幾名隨員,在主人的陪同下,面帶笑容,大步向貴賓室走去。我們這些留在機上的人,不免為可能出現的危險十分擔憂。直到一小時后,周總理安全歸來重新起飛,我們懸著的心才落下來。
從激烈交鋒到求同存異
我們到達雅加達以后,到處都可以看到迎接亞非會議召開的“AA”標志,熱烈的氣氛籠罩全城。中國代表團受到了特別的關注和歡迎。我們的車隊來到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時,門前馬路上已經擠滿了歡呼的人群,都想一睹周恩來的風采。第二天到達萬隆以后,這種氛圍就更加濃烈了。
4月18日上午,亞非會議在萬隆的獨立大廈隆重開幕。印尼總統蘇加諾熱情洋溢地發表了開幕詞“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下午,大會發言開始。各國首席代表按英文字母順序發表演說。輪到中國時,周恩來為了多聽一些不同意見,主動延后了發言。大多數代表在發言中譴責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表示了促進亞非團結合作的良好愿望。但是,“雜音”很快就出現了,例如將共產主義指為“新殖民主義”,要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甚至懷疑中國對鄰國搞“顛覆”活動。
人們的目光聚焦到周恩來身上,以為他一定會拍案而起,予以反擊;于是就會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樣,大會必然爭論不休,最后陷于僵局,不歡而散。但是,周恩來一直耐心地傾聽各種不同的意見,不時在紙上記錄些什么。
直到4月19日上午大會結束,周恩來還沒有發言。但當天中午回到住地后,突然展開了一場準備下午發言稿的“突擊戰”。周總理在屋里口述,由他的貼身秘書、翻譯浦壽昌用鉛筆記錄。我們幾個翻譯都坐在打字機前等候,送出一頁,就立即翻譯。當時誰都沒有想到,總理出口成章的這個短短的“補充發言”,在亞非會議上發揮了扭轉乾坤的作用。
大會開始以后,泰國外長在發言中還點名攻擊中國,土耳其副總理也為其國家參加北約軍事同盟辯護。然后,會議主席宣布:“我現在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發言!”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健步走上講壇。這時候會場已經座無虛席,不少人只能站著聽。我注意到,與我一起坐在記者席上的各國記者尤其緊張,顯然他們都在期待著爆炸性的新聞。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周恩來心平氣和地告訴大家,他的大會正式發言稿已經分發給各位代表,現在只作一個簡短的“補充發言”。會場一片寂靜,大家都豎起耳朵聽他會“補充”些什么。周恩來的第一句話竟是,“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接著,他又直截了當地告訴大家:“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
周恩來進一步坦率地說明:“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到共同基礎,我們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整個補充發言不過20分鐘,除了中間由浦壽昌念的譯稿,一頭一尾都是周恩來用洪鐘般的聲音講的。講話結束后,會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空氣陡然變了。好心的人們無不欣慰地意識到,面臨分裂危機的亞非會議因此得救了。
在隨后幾天大大小小的會議中,各種交鋒仍然不斷出現,有時甚至如同風暴,總讓人感到有一股勢力在起作用,其目的是使會議達不成一致協議。同時人們也看到,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總是以折沖樽俎、協和萬邦的外交藝術,將會議一步一步引向以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為核心的“萬隆精神”的勝利。
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過人的精力是令人吃驚的。他和代表團工作人員同住在一座別墅里,他屋里的燈光經常徹夜通明。有人統計過,平均每天夜里他只睡三個小時,而白天除了參加會議與活動,就是在別墅不斷接待客人。他有一條原則:不論什么國家的代表來做客,都同樣尊重。他的法語翻譯陳定民教授曾告訴我,有一次他漏譯了“親王閣下”四個字,周總理立刻讓他糾正,就是這么嚴謹。許多在會議上與周恩來交鋒過的人,后來非常尊敬這位杰出的中國外交家,并且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摘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