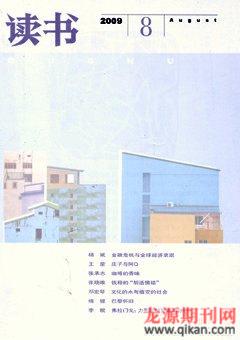革命酒吧
董炳月
東京有許多酒吧,也有許多從事社會運動的革命者,因此革命者進酒吧是正常的也是平常的。不過,我明確意識到革命酒吧的存在,是在滯留東京期間隨小森陽一先生參加一次活動之后。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周二,下午是讀書會。三點四十分開始小森先生為我與島村輝、林少陽三人講日俄戰爭中的“橫死”問題,五點剛過讀書會即提前結束,因為小森先生要趕往永田町的國會大廈。那正是日本和平運動者與教育界人士為保衛《教育基本法》舉行抗議集會的關鍵時期。基于日本和平憲法(一九四六年)制訂的《教育基本法》從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始實施,被視為教育憲法。但是,近年對該法的修改成為保守化的日本政府修憲的第一步,十二月十五日將在參議院對修正案舉行最后表決。每到周二傍晚,數百名和平主義者、護憲人士便聚集到國會大廈與議員會館之間的馬路邊,散發宣傳材料,喊口號,唱歌。小森先生是核心人物,必須到場給大家鼓勁。匆匆離開教室之際他說,晚上七點還要在新宿的一個酒吧講憲法問題,我們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參加。興趣大家都有,我更想知道新宿這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地方怎么會有對政治問題感興趣的酒吧。
那個酒吧名叫“紅布”,在東新宿明治大道東側一座大樓的地下一層。面積很小,去掉舞臺、柜臺,觀眾席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放著普通的折疊椅,坐三十個人已經滿滿當當。舞臺后墻上掛著一塊黑色長方木匾,上面刻著兩個清秀的漢字“紅布”,描金。漢字下面是英文的“red cloth”。在酒吧這種休閑場所講護憲這種嚴肅的政治問題是一種嘗試,所以老板特意請一位名叫真田曉子的年輕女士當主持人。真田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對政治話題相對熟悉。講演會七點開始,真田拿出小森先生剛出版的文學政治學著作《詞匯之力,和平之力——現代日本文學與日本憲法》(鴨川出版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對小森先生的研究經歷和學術成就進行了簡單介紹,接著小森先生以“何謂改憲”為題,用大概一個小時講解和平憲法的基本精神、改憲派主張的要點與目的等等。講演之后是音樂表演,歌手名叫大木溫之,演唱的第一首歌是《和平》。曲目顯然是與講演主題搭配的。演唱結束之后進入自由交流階段,真田得知在場的有我這樣一位中國人,便過來打招呼,說是對中國感興趣,讀過藤井省三撰寫的有關魯迅的書。我問她一個酒吧何以舉辦這種政治性的講演,真田便喊來了酒吧老板豬狩剛敏先生。問豬狩先生店名何以叫“紅布”,他回答說紅布就是戰旗,紅色表示革命。他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這個店本來是中國人開的,好像是經營飲食業,他接手之后改裝成現在的樣子,做酒吧。柜臺下面,確有紅布做的圍簾一樣的裝飾。大家喝著啤酒、葡萄酒、飲料,吃著三明治、比薩餅、炒面條之類,談論日本憲法以及海外派兵、防衛廳改防衛省(國防部)等現實問題。地下室的隱秘性和昏暗燈光造成的朦朧效果,與政治話題的現實性、尖銳性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反差。比起平時在會館、教室等公共場所進行的政治集會,那種活動中的政治性似乎浸透到了生活的更深處。小森先生因為同一政治問題從永田町的國會大廈走到新宿的酒吧,用自己的腳步建構了一個更有層次感和縱深感的政治空間。就像他在《詞匯之力,和平之力》中從和平憲法的角度對日本現代文學進行重新發現,建構了一個“文學政治學”的空間。
遺憾的是,護憲派的斗爭最終未能阻止日本政府的行動,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和防衛廳升格防衛省法案同時在參議院表決中通過。
去“紅布”五個月之后,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的讀書會,小森先生為我們講“現代讀者的成立”。晚餐之后他匆忙乘新干線去八百里外的滋賀縣,準備參加次日一大早將在那里舉行的民眾集會,島村則領我與林少陽來到新宿,見識一家主要演唱老歌和革命歌曲的酒吧。
酒吧名叫“ともしび”(tomoshibi),這是漢字“燈”的日語平假名寫法。有光明、指引方向的意思。“燈”在新宿車站東口靖國大街南側一座臨街商業樓的六層,我們到那里的時候演唱尚未開始,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大廳里坐滿了客人。客人多為中老年,還有穿工作服的。演出開始,有單人表演,有手風琴伴奏的演唱,有手牽手、肩并肩的合唱。曲目以《卡秋莎》等蘇俄歌曲以及《北上夜曲》之類的日本老歌為主,主題多為懷舊、革命、和平、愛等等。演唱者很投入,聽眾或拍手或隨著唱,臺上臺下融為一體。其實臺上與臺下本無明確的界限。表演形式與表演內容、氣氛,把我帶回上個世紀中國的七八十年代。“燈”的老板名叫大野幸則,一位六十歲左右的先生,清瘦,戴著眼鏡,文質彬彬。島村把我介紹給他,他過來交談,很熱情。島村和幾位客人合唱了幾首歌,十一點左右我們離開的時候,還有客人進店。
兩天之后,一疊關于“燈”和“歌聲吃茶”的材料寄到我手里。有報刊的采訪報道,有“燈”的活動介紹。那是大野先生寄來的,因為我對他說自己對“燈”和“歌聲吃茶”感興趣。大野先生在信中說,五年前《北京周報》特派員曾與他商量是否有可能在北京推行“歌聲吃茶”活動,所以他到北京去了兩次,與北京市民進行交流,在景山公園一起唱歌。二○○七年是市民交流年,“燈”的同人們將與中國兒童劇院進行交流,年底會邀請中國的四個劇團到日本演出,并打算去中國拜訪戰后撫養日本殘留孤兒的中國養父母們等等。后來沒再與大野聯系,我不知道“燈”的計劃是否都已順利實施。
大野先生寄來的材料中有他本人與藤澤義男為紀念“歌聲吃茶”五十周年合寫的長文《歌聲吃茶五十年·“燈”的歷史》。文章連載于《燈》月刊二○○三年一月號至二○○五年三月號,對“歌聲吃茶”的歷史脈絡有清晰的解說。關于“歌聲吃茶”的起源,通行的說法是:戰后初期,新宿區歌舞伎町的西武新宿線車站前有一家叫做“燈”的大眾飯館,經營者為柴田伸。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某一天,看到就餐的客人隨著店內播放的俄羅斯民謠唱起來,柴田一拍腦袋計上心來,于是請來主持人和樂手,把寫著歌詞的紙貼在墻上,大家一起演唱。——那就是“歌聲吃茶·燈”的起點。當時的店名是直接用漢字“燈”。一九八四年,“燈”從西武新宿車站前遷到現在的地方,店名改用日語平假名書寫。從一九五四年算起,二○○四年為五十周年。柴田伸的故事還有另一種版本:那家店本是旅日白俄在簡易房中經營的俄國料理店,因經營不善,無奈之下盤給了剛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柴田,柴田將其改造為專賣炸豬排、雞蛋飯之類份飯的平民食堂,五十日元一份,適合平民消費。某日,藝術學院的一群女孩子來到店里,用美妙的歌聲唱起來,客人們也隨著唱,店內的氣氛變得熱烈優雅,于是柴田來了靈感。不過,“歌聲吃茶”的起源還有不同的說法。一九五一年國際勞動節,新宿要町的小酒館“底層”曾大聲播放歌曲,并被雜志報道,因此被視為“歌聲吃茶”的起點。另一家名為“卡秋莎”的茶館也自稱“歌聲吃茶”的鼻祖。但是,經大野等人調查,一九五四年之前并沒有使用“歌聲吃茶”的名稱。我注意到,關于“歌聲吃茶”起源的不同說法中有兩個共通之處:第一,起源地都是新宿。第二,都與蘇俄歌曲有關。
一九五九年七月西武新宿車站前“燈”的新店開張,樓上、樓下兩層,據說能夠容納三百至四百人。進城謀生的年輕人、游行集會歸來的市民大眾聚集于此,放聲歌唱,“歌聲吃茶”的影響力日漸擴大,與日本社會的“歌聲運動”合流,“燈”也在東京都內開了二十多家分店。五六十年代的許多影片如《我拋棄的女人》、《巨人與玩具》、《絕對多數》中,都有“歌聲吃茶”的場面。當時的日本媒體甚至將廣泛開展的“歌聲吃茶”運動稱為“國民熱”。這種“國民熱”的產生,有戰后日本民主主義的大背景。不妨翻譯大野文章中的一段:
在戰后“民眾是主人!”“發揚民主主義!”這個背景上,美國爵士樂、流行音樂隨著美軍的進駐被帶進來,并隨著收音機和電視廣泛傳播,與此同時俄羅斯民謠、蘇聯歌曲也引導著這個時代的文化,“歌聲運動”高揚“歌聲乃和平之力”的大旗廣泛開展,從中誕生了《加油!》、《反對核試驗》等歌曲。進而,“歌聲運動”又創造出了敘事抒情性的《北上夜曲》、《給你一枝勿忘草》。
戰斗的歌聲激勵著人們,產生出創造光明未來的勇氣,通過同聲歌唱達到對于人類感動的共有,——“歌聲吃茶”漸漸被建設成這樣一個地方。
但是,一九六○年戰后民主派的安保斗爭受挫,電視機的普及、游戲機的出現導致大眾娛樂形式的多樣化,“歌聲吃茶”亦隨之陷入衰退,“燈”的多家分店相繼關門。現在只剩下新宿這一家。
島村是日本現代文學特別是現代左翼文學研究的名家,相識有年,但他的音樂才能我是那晚在“燈”聽了他的演唱之后才有所了解。他青年時代在音樂方面下過工夫,大學畢業后甚至一度考慮以音樂事業為生。盡管最后在大學執教、研究文學,但他對日本的音樂文化一直抱有關心。在“燈”聽歌大概一周后的五月四日(恰值中國的青年節),他送給我一本《歌之世界·533》和他的一篇舊論文《歌聲吃茶的文法——某種“戰后民主主義”的形式》。這是為了幫助我理解日本的“歌聲吃茶”。
《歌之世界·533》是“燈”印行的歌曲集,嫩綠色的亞光塑料封面,燙金的字和圖案,樸素、簡潔、清新。歌曲集第一次印刷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島村送給我的是二○○三年七月三十日印行的第十四版。可見該歌曲集的“長銷”(雖然未必是“暢銷”)。顯然,這本歌曲集是“歌聲吃茶”的符號。看了歌曲集我才知道,《底層之歌》、《燈》均為俄羅斯民謠。書名中的“533”是集中所收曲目的數量,“日本的歌”、“俄羅斯的歌”都專列了欄目,但中國歌曲是放在“亞洲的歌”一欄中。數了一下,一共只有《草原情歌》、《對花》等六首,多為抒情性的民歌,革命歌曲一首都沒有入選。造成這種隔膜情形的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中國的革命歌曲大多誕生在抗日戰爭中,與日本有一種天然的隔絕;二是在戰后的很長時間里中共與日共因意識形態的分歧長期處于絕緣狀態(恢復正常關系是一九九八年)。不過,盡管如此,中日兩國的革命歌曲都受到蘇俄同類歌曲的影響,并且具有革命美學風格的一致性。因此我進了“燈”才有回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感覺。
《歌聲吃茶的文法——某種“戰后民主主義”的形式》發表在二○○三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的《語文》第一一六輯,是“聲音·身體·媒體——共同體驅動語言”專欄中的一篇。在此文中,島村是結合戰后日本的勞工運動、日本左翼文學史以及小說家五木寬之(一九三二——)的長篇名作《青春之門》(一九六九——一九七五)中的相關描寫對“歌聲運動”進行探討,一直上溯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日本無產階級文學興盛時期《國際歌》、《華沙勞動歌》在日本的介紹。在一九四六年戰后第一個國際勞動節,“歌聲運動”指導者關鑒子(一八九九——一九七三)指揮集會民眾演唱《國際歌》、《紅旗》、《聽吧!全世界的勞動者》等歌曲,一九四七年的國際勞動節集會者又演唱《從鄉村到工廠》、《連接世界的花環》等新歌。島村論文描述的情形與新中國工農兵時代的場景十分相似。根據島村論文的介紹,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紀念日本青年共產同盟成立兩周年的集會上,關鑒子擔任指揮的青共中央合唱隊演唱《國際歌》、《芝浦》(工人運動歌),這一天合唱隊正式定名為“青共中央合唱團”(一九五一年簡化為“中央合唱團”),這一天也被視為戰后日本“歌聲運動”的創立原點。六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正式開始的“歌聲吃茶”運動,以生活化、具有休閑色彩的形式匯入了日本的“歌聲運動”。但是,如前所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隨著左翼政治運動的衰退和經濟變革導致的勞工運動的畏縮,“歌聲運動”和“歌聲吃茶”都衰退了。島村在文章結尾處說:“‘歌聲運動與‘歌聲吃茶現在究竟還有沒有意義?總體說來,冷戰結構解體,從前那種以蘇維埃為中心的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與其具有關聯性的亞非民族主義,以及日本國內的勞工運動、民眾運動,——由此構成的戰后民主主義圖景已經消失,因此,曾經存在過的‘歌聲吃茶這出拿手戲大概不可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而且,有關‘和平、‘民族的理解,在現在所謂的后殖民理論被引入的情況下,對于‘戰后式和平、‘戰后式民族主義也不得不進行重新思考。”確實如此。作為戰后日本文化諸相之一的“歌聲運動”和“歌聲吃茶”,在二十世紀末葉的日本幾乎被年輕一代遺忘。
不過,近幾年“歌聲吃茶”似乎在漸漸恢復活力。不僅有我在“燈”看到的熱烈場面,“燈”的演出小組(主持人、指揮、伴奏、領唱)應邀到地方城鎮活動,甚至能組織起千人規模的歌唱表演。此外,“燈”還與劇團合作演出輕型歌劇。“歌聲吃茶”活力的恢復與“新昭和懷舊階層”的出現直接相關。二○○五年十月號的《日經消費·開掘》月刊,即對“新昭和懷舊階層”的出現進行了專題報道。這個階層的出現其實是“團塊一代”大量退休的結果。“團塊一代”指“二戰”結束后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數百萬日本人,是他們創造了戰后日本的繁榮。從二○○六年開始,“團塊一代”到了花甲之年,開始退休,其生活方式的改變直接影響到日本社會的消費結構。根據《日經消費·開掘》的調查,最受中老年歡迎的公共設施的前三名,依次為公共浴室、歌聲吃茶、點心店。《朝日新聞》、《產經新聞》、《月刊卡拉OK粉絲》、《日經商業》等報刊也有類似的報道。在歌聲吃茶店這種具有特殊歷史積淀的場所,與同齡人一起聽老歌,回憶青年時代的革命體驗,對于許多人來說無疑是懷舊性的享受。《The music therapy》二○○六年九月號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我的青春之燈!》。此外,對于卡拉OK這種演唱形式的反動,也使一些青年人走進“歌聲吃茶”。相對于卡拉OK這種演唱形式中的孤獨性(自我陶醉性)以及屏幕風景的虛擬性而言,“歌聲吃茶”的演唱是真實的伴奏,演唱過程中有人與人的交流。“燈”就有一位年僅二十三歲(當時)的美麗女店員,名叫永井康子。她大學畢業之后到“燈”來工作,主要是因為在“歌聲吃茶”的演唱形式中能夠感受到心與心的交流。《讀賣新聞》和《東京新聞》都曾刊載過有關她的報道,《東京新聞》那篇報道的題目就是《超越年齡層的“歌聲文化”》。在此意義上,“歌聲吃茶”已經獲得了新生,完成了從“政治”向“美學”的轉變。
無論是“紅布”還是“燈”,與其革命并存的都是平民性。這主要是指消費價格。小森先生講演那晚,“紅布”入場券的價格是一千五百日元(東京大學生打工的小時工資在八百日元以上),另免費送一瓶啤酒或飲料。“燈”的點歌費是七百三十五日元,個人平均消費額是兩千七百日元。而東京稍微好一點的酒吧,單人消費每晚總也要五千日元以上。
行文至此,忽然覺得將“紅布”、“燈”這種消費設施稱為“革命酒吧”也許不那么合適。因為“革命”畢竟是其一部分而非全部,客人喝的也并非都是酒,還有其他軟飲料,還有飯吃。不過,暫時好像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適的名稱。應當說明的是,本文所謂的“革命”不能完全在中國的意義上來理解。這涉及“革命者”的身份以及“革命”的背景等問題。“革命酒吧”作為日本資本主義多元文化中的一種而存在,被同樣包容在“新宿”這個文化熔爐中的麥當勞文化、日本傳統文化、色情文化等等相對化,意識形態色彩不是那么鮮明。不過,唯其如此,日本的革命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比如日本共產黨的黨員們以及信仰共產主義的“紅布”老板豬狩剛敏)才表現出高度的純粹性。
八十年前魯迅寫過一篇《革命咖啡店》(一九二八,收入《三閑集》),似乎是調侃“革命”與“咖啡店”二者之間的反諷關系。但是,在“紅布”和“燈”這里,“革命”和“酒吧”卻完成了和諧的統一。這顯然是因為“革命”和“酒吧”存在的環境以及革命者本身都發生了變化。
二○○八年三月十五至十七日寫于寒蟬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