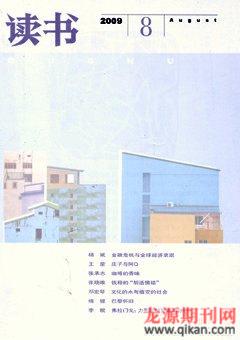弗拉門戈:力圖駛向靈魂的旅行
李 皖
一、引子與問題
藝術(shù)有一種奇怪的秉性:你知道得越多,你越失去了直視它靈魂的能力。對于弗拉門戈,我就是這樣一個無所不知的傻子、通曉一切的渾蛋。當聽完一場弗拉門戈歌舞,我不能假裝還告訴你說,我的感動、我的領(lǐng)悟。我可以告訴你很多很多,但都是知識,如同繞城狂走,一圈又一圈,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
現(xiàn)在,我只要聽一小節(jié)吉他,就可以叫出,弗拉門戈;只要聽聽那擊掌,就可以叫出,弗拉門戈;只需要一秒鐘的歌唱,就可以叫出,弗拉門戈;連一秒鐘都不需要,只需要把歌手的聲音讓我聽到,就可以叫出,弗拉門戈。看也是一樣,那就看吧,三秒鐘,我就知道,弗拉門戈;以釘鞋擊地,擊出拍子,弗拉門戈,并能與美國踢踏舞、凱爾特“大河之戀”截然相區(qū)分;手勢,對的,手勢,以及服飾、姿態(tài)、表情,就算是定住,我也能告訴你,這是弗拉門戈。
有時候想想,這真可恥。你不可能不想起弗拉門戈,而想起別的,想起它想表達的?但這實在太難。弗拉門戈是一種太有特色的藝術(shù),那么濃艷,你不可能不讓它的一個個特征在你的意識層面激起回響,并讓它最終占據(jù)你的全部印象。
吉他,世界上的吉他有四種(此處專指原聲吉他),古典吉他,夏威夷吉他,桑巴吉他;弗拉門戈吉他跟它們?nèi)灰粯?連一小節(jié)都不一樣: 重重地擊下去,一記強音;然后,靜止,留一段空白;然后,傾瀉出一長串十六分三十二分六十四分音符,沖破小節(jié)線,踩不準每個音的強弱拍甚至精確時值,因為太快了,一切都來不及;突然急停,定住,又一段空白……這是一種動靜如此之大、對比如此強悍、速度如此劇變的演奏,像顛簸的、昏厥又奮起的、腳步踉蹌的奔跑。
呵,歌聲,往往在死寂的那一刻躍起,粗糲喑啞,滄桑落寞,在狂暴邊緣表現(xiàn)著疼痛。最經(jīng)典的弗拉門戈歌聲,帶著沙漠的熱氣,帶著漫漫旅途的孤寂和焦渴,帶著忍受命運的悲苦,最關(guān)鍵的,有一股子熱,熱戀、熱愛、熱火,分不清是抱怨還是擁抱,決絕還是纏繞,哭泣還是呼喊,絕望還是熱望,或許,是合在一起的東西,一種憂郁哀傷與狂熱奔放的纏縛,緊緊相擁又猛然將對方推開。領(lǐng)略過世界的人,比如我,馬上分辨出,這里有阿拉伯;有游牧民族——沒有故鄉(xiāng)的吉卜賽人,從中國新疆橫跨整個歐亞大陸;有印度的神秘宗; 有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夜歌和露水。
是的,的確如此。弗拉門戈是所有這一切的綜合——阿拉伯音樂、印度音樂、中亞音樂、茨岡音樂,是一個游牧民族在遷徙流亡途中,帶著沿途的風景、泥土和風塵,然后,在歐洲音樂的框架內(nèi),合成;一個歐洲巴洛克風格的阿拉伯宏偉建筑,就像阿爾罕布拉宮。有人說弗拉門戈就是吉卜賽流浪藝術(shù),但是沒有人說得清,為什么是在安達盧西亞才有弗拉門戈,而俄羅斯的、捷克的、塞黑的吉卜賽人的歌唱,為什么顯露的是另外一種?
二、 呈示部與答案,或許不是答案
今日世界的中心是美國。所謂的中心,不是指領(lǐng)袖的居住地,而是指世界的一個集市,出于復雜的、可能是這個也可能是那個的什么原因,世界各個種族的人流,匯聚到了一處,不同文化快速地攪拌起來,形成了一種/多種新的文化——混合型的、世界樣式的文化。
時間往前推,世界上曾有兩個更顯著的中心。一個在新疆,以庫車為圓心。東亞的、西亞的、歐洲的,南方的、北方的、中部的,當時世界的所有人種,除了非洲黑人和北美印第安人,全都匯聚于此,使這里成為歷史上延續(xù)時間最久的“世界之都”。另一個在西班牙,這是我猜測的,我是從這里的音樂、建筑、文學、神話,感覺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時期”。很可能,因為帝國的擴張,因為三大洲之間陸路和水路的通商——歐洲、亞洲、非洲——西班牙正處在一個三角地、樞紐、路口和港口;而一直在中國北方游牧,在歐亞大陸北緯四十度至五十度這個寬闊通道間往來流徙的一部分游牧民和吉卜賽人,漸漸在這大陸的最西端定居,于是,安達盧西亞的弗拉門戈,成為這個“世界時期”最顯著的一個成果,按生物學分類法,它是一個歐—亞—非多人種的、世界樣式的混種。
弗拉門戈的根須生長在這樣的多種基養(yǎng)之中:摩洛哥、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希臘、廣大的阿拉伯以及中亞甚至東亞文化,雖然仍有眾多的爭議和不解,但許多權(quán)威專家堅持認為,它跟吉卜賽人有關(guān),隨著十五世紀吉卜賽人到達這片土地,弗拉門戈的歷史就開始了。在接下來的幾世紀,先是吉卜賽部族音樂,然后在地中海邊、安達盧西亞的山脈中,與阿拉伯音樂、猶太音樂結(jié)合起來;當時,穆斯林、猶太人和“異教徒”吉卜賽人,被迫向當?shù)氐奶熘鹘烫眯靖淖?從而在這里獲得了長久的居留權(quán)。今天我們發(fā)現(xiàn),弗拉門戈的著名家族和文化中心,莫不置身于吉卜賽人的聚居地,家族中一定有流亡者血統(tǒng),像阿爾卡拉濱河(Alcala del Rio)地區(qū)、烏特萊拉(Utrera)鎮(zhèn)、赫雷斯(Jerez)市、卡第斯(Cádiz)省、塞維利亞的特里安納貧民區(qū)(Triana)……都是如此。
弗拉門戈(flamenco)是什么意思?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只剩下了猜測。關(guān)于這個詞的起源,有兩種理論。一種是,西班牙的猶太人因為貿(mào)易而去了佛蘭德斯(今法國北部),在那里他們被允許唱自己的宗教圣歌而沒有什么麻煩,后來,對這種圣歌的稱呼即變音為弗拉門戈(與佛蘭德斯發(fā)音相近),用以指稱定居在西班牙的猶太人圣歌。另一種理論似乎更有道理,它說,弗拉門戈是阿拉伯詞語felag和mengu的誤傳,這兩個詞合在一起,就是flamenco,意思是“流亡農(nóng)民”,確實,可作為佐證的是,在弗拉門戈誕生的那個年代,阿拉伯語在西班牙這片土地上是非常常用和廣為通行的。
吉卜賽人,有時也包括其他西班牙人,會熱切地關(guān)注和爭論弗拉門戈的純粹性,他們往往會急切地分辨出,這是吉卜賽的弗拉門戈,這是非吉卜賽的弗拉門戈,這是西班牙的弗拉門戈,這不是西班牙的弗拉門戈。自六十年代以來,又一輪世界融合發(fā)生在這片土地上,沖擊來自美國。由于搖滾樂和世界流行音樂的影響,弗拉門戈在沉寂了四十年后再度火爆起來,并快速地與歐美的搖滾樂、爵士樂、布魯斯、古典交響,拉丁美洲的薩爾薩、探戈、倫巴、桑巴,甚至世界潮流的戲劇和電影,互相勾連、交互、纏繞、融合。民粹主義者驚呼,這不是弗拉門戈,弗拉門戈正在弗拉門戈的熱潮中消亡!
在這場新的混合大戰(zhàn)中,眾多新穎的、精巧的、高明的技藝被發(fā)明出來,同時,確實,它也在迅速地遠離原有的形態(tài)。但是這樣想,回望五個世紀以前,不是有一個近似的侵犯、交融和混合發(fā)生在這個叫弗拉門戈的事物之上,并成就了今天稱之為“純粹的弗拉門戈”這個玩意兒嗎?但是你也不能不發(fā)現(xiàn),在此過程中確有一種頑固,吉卜賽人的頑固:一個動蕩不安、備受歧視因而敏感脆弱的部族,艱難地在國家和社會的邊緣延續(xù)一己之存在,他們一方面在融入,一方面又始終有一種急切的渴望,去得到對自身的身份認定,以此來保護自己的自尊和種姓。
三、 展開部:從音樂到舞蹈到文學到電影
同樣是源于沒有家園、沒有祖國的苦痛,猶太民歌飽含漂泊、流浪的悠遠憂傷,懷抱隱忍的巨大苦楚;而吉卜賽音樂——弗拉門戈,卻是烈火一般的灼熱和倔強。弗拉門戈處處顯露著侵犯,顯露著嚴陣以待、決不低頭忍受的反侵犯,他們好像并不在乎有沒有祖國,而擁抱著熱愛著這么一種流亡、踉蹌的飛旋,飛旋的生活,飛旋的自由;一種激情與激情的交戰(zhàn)旋舞,糾結(jié)在每一曲、每一唱、每一舞之中。以此為核心,構(gòu)筑成關(guān)于弗拉門戈吉他、歌曲、舞蹈的全部美學。
弗拉門戈藝術(shù)的三大件——吉他、歌曲、舞蹈——往往會共同出現(xiàn)在同一個舞臺上。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既是相互配合,又是相互競爭、相互激蕩、互不服輸?shù)摹T诮倌隁v史上,關(guān)于究竟是吉他還是歌曲應充當弗拉門戈的一號角色,有過有趣的起伏、顛覆甚至打斗、戰(zhàn)爭。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歌曲是弗拉門戈的主角,吉他是配角;但在近五十年,這種情況被反轉(zhuǎn)過來。
在最近半個世紀的風潮中,作為視覺和直觀的藝術(shù),弗拉門戈歌舞或舞劇,比吉他和歌曲獲得了更廣泛的世界印象。弗拉門戈舞蹈的特征是,雙腳踢踏出激烈的、暴風雨般的節(jié)拍,而舞者的上身巋然肅立,始終端穩(wěn)某種姿勢,保持著儀態(tài)、尊嚴和氣派。民間舞有交際的性質(zhì),弗拉門戈也是,對舞,或者群舞,但是你發(fā)現(xiàn)異樣了嗎?世界各種民間舞、交際舞都是兩情相悅,而弗拉門戈不是交際,而是交戰(zhàn),是雙方爭雄、互斗、競技,是一方向著另一方挑戰(zhàn)和炫耀。緊張,你感到緊張了嗎?舞者上下都是緊張的,身體、姿態(tài)、手,即使圓滑地繞、旋,也都是緊張的繞、旋。臉,你在別處的舞蹈里發(fā)現(xiàn)不了這樣的臉,那么隆重的、苦大仇深的表情,緊繃著,不是幾分鐘,而是幾十分鐘,從頭至尾,像是把心里面的火山壓緊,在臉部,這最后的防線上,關(guān)上那最后的一道閘!
我還發(fā)現(xiàn),弗拉門戈舞沒有象形的意義,這太不一樣了。楊麗萍的孔雀舞,象形到了極致,表現(xiàn)別種事物,以仿擬的形式。芭蕾舞,現(xiàn)代舞,都有大量的象形表演,表現(xiàn)人物行為、場景、自然外物。而弗拉門戈沒有這些。它的舞步劇烈,為了踩出鼓點。而這種下肢的劇烈運動不是解放而是禁錮了身體,舞者的上身只能不動,端緊了姿態(tài),只剩下臉和手。于是手,擺出了各種姿態(tài),是臉的另一張臉,配合著那凝重的表情;表現(xiàn)的東西無它,全是心理,全是激情與沖突,全是從那臉部,最后的防線,壓制、拼命地往下壓制,壓制那全身都在竄流不息,醞釀、鼓脹、即將爆發(fā)的攝氏一千度的高溫。弗拉門戈舞的全部,都只是那一個人,侵犯,反侵犯;爭斗,反爭斗;愛恨,反愛恨;人的心理,人的內(nèi)心和人的表情!
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早期,被公認為弗拉門戈的“黃金時代”。在這傳奇時代的尾端,上世紀三十年代,弗拉門戈音樂灌制成了最早一批錄音。此時,弗拉門戈的歌舞聚會通過城市角落的小酒吧,迅速擴散到新的人群。正是在此時,此地,加西亞·洛爾加遇到了他一生迷戀的“深歌”。
據(jù)說,弗拉門戈有大約六十種相對固定的樣式,每個樣式都代表特定的情緒,搭配這種情緒,詞人們寫出形式相近、情緒相近、內(nèi)容千變?nèi)f化的歌詞。其中,solea曲式,孤調(diào),也就是深歌,是構(gòu)成弗拉門戈音樂的基石,它表達悲劇情緒,描寫黑暗事物。
弗拉門戈常見的節(jié)奏循環(huán)有十二小節(jié),這一點正與布魯斯民謠相似。它的特色在于,每一首樂曲,都由一組各自比較完整的音樂單位拼合而成,這些單位的數(shù)量依現(xiàn)場的情緒氣氛、樂手期望達到的感情色調(diào)不同而不同,并有著不同的組合發(fā)展可能。深歌采用我們熟悉的3/4節(jié)拍,每個樂句四小節(jié)或八小節(jié),然后再將之進一步碎化細分,在頂端加上裝飾音。這樣一來,相似的樂句之間,復雜的交疊和變化不斷實施著暗中的破壞,在重復中破壞,又在破壞中重復,結(jié)果形成跌宕起伏又傾瀉而下的強烈抒情效果(參見簡·費萊的文章《弗拉門戈,一種狂野、兇猛的激情》,出自《世界音樂概要指南第一卷》。Jan Fairley: Flamenco, a Wild, Savage Feeling; from World Music: The Rough Guide, p.284, edited by Simon Broughton, Mark Ellingham and Richard Trillo)。
一九二二年,幾個來歷不同的著名名字聚到了一起。當然,著名是后來的事,他們此時只是幾個經(jīng)常在深歌聚會中碰面的小幫派:熱愛詩歌的洛爾加、作曲家法雅(Manuel de Falla)、吉他演奏者塞戈維亞(Andrés Segovia),后來,這三個名字成為西班牙詩歌、古典音樂和吉他演奏這三個領(lǐng)域里各自最響亮的名字。
弗拉門戈的影響有多大?看看洛爾加的詩歌便可以瞅個端詳。在詩作《下午五點鐘》里,這位年輕的詩人以暗示的筆法宣示:弗拉門戈與斗牛有關(guān),二者不僅在根源上分享同一種情緒、激情、飄忽不定的天才閃光,而且,它們共同提供了可能的方式,去突破社會的和經(jīng)濟的邊界。
在領(lǐng)略過深歌的魅力后不久,洛爾加就開始采用與深歌相類似的可能方式,去突破西班牙詩歌的邊界。看看洛爾加長短錯落的詩句,潛行在長短詩句下復雜多變的音步,熟悉弗拉門戈的人不難猜測發(fā)生了什么。如同前文所述,弗拉門戈節(jié)奏的奧秘,除了短促、綿長、停頓與急進的復雜交織、交戰(zhàn)、相克相生,還有在每一個大節(jié)奏里維持平穩(wěn)、造就大氣莊嚴的特質(zhì)。這也正是洛爾加的詩節(jié)魅力。而洛爾加的詩情,純凈、透明,仿佛如自然之子的天真,對抗著曖昧的、莫名所以的狂暴不安與不詳,這是不是也很弗拉門戈?弗拉門戈美學中有一個極特別的詞叫duende,當表演到極致時,欣賞者就說它有了duende,而你表演得再怎么嚴絲合縫字正腔圓卻來不了duende,你依然是個最末流的演員。在英語中,duende只有一個意思,惡鬼;而在西班牙語中,這個詞不只指惡鬼,還指弗拉門戈的靈魂,這duende,只能在“靈魂里最后一個鮮血四濺的地方”(洛爾加語)出現(xiàn)。無疑,洛爾加也有這樣的duende。
奇怪的是,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弗拉門戈的專業(yè)演員,都深信duende不是一種技藝,無法通過訓練獲得,更多時候它是一種神秘,一種魔力。在初次聆聽弗拉門戈并為之深深震動之后,洛爾加僅用二十一天就寫下了他的傳世之作《深歌集》,一口氣三十一首,深歌的力量之大出乎意料,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為一種歌唱而“戰(zhàn)栗不止”。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說:“我天生是個詩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或者美男子一樣。”《深歌集》第二首《吉他》,以與音樂近乎相同的音步表現(xiàn)和象形弗拉門戈的吉他演奏。看吧,它那與弗拉門戈吉他近乎相同的形式,那重復與重復中變化、突變的張力:
吉他的嗚咽
開始了。
黎明的酒杯
碎了。
吉他的嗚咽
開始了。
要止住它
沒有用,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單調(diào)地哭泣,
像水在哭泣,
像風在雪上
哭泣。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哭泣,是為了
遠方的東西。
南方的熱沙
渴望白色山茶花。
哭泣,沒有鵠的箭,
沒有早晨的夜晚,
于是第一只鳥
死在枝上。
啊,吉他!
心里插進
五柄利劍。
(戴望舒、北島譯)
洛爾加還有一個秘密,非關(guān)技術(shù)也非關(guān)內(nèi)容,這是詩人赫爾南德茲——洛爾加的后繼者——呈示的,它也同時呈現(xiàn)了屬于弗拉門戈的秘密,他說:“我憎恨那些只用大腦的詩歌游戲。我要的是血的表達,而不是以思想之冰的姿態(tài)摧毀一切的理由。”
血的表達,憎惡大腦。而音樂不只是音樂,還有鮮血。對于西班牙藝術(shù)來說,血的音樂一直是終極的秘密,至深的靈魂,不僅音樂中有音樂,還有詩歌后面的音樂,舞蹈動作里的音樂,生活生命中的音樂。各種介質(zhì)不同的奇妙韻律,后面卻都有著近似的血的奔突和潮涌。
“黃金時代”的弗拉門戈,洛爾加的深歌,漸漸中斷。上世紀七十年代,弗拉門戈熱風再起,在掃蕩五大洲的地中海風情中,詩歌的聲與影已經(jīng)不再是顯著角色,只能淡淡地在幕后時起時伏。新的弗拉門戈熱,是憑借著搖滾樂、流行音樂、商業(yè)演出、全球時尚的新力量而迸發(fā)的,是一種三分之一藝術(shù)、三分之一商業(yè)、三分之一時尚的當今世界藝術(shù)的新的三位一體現(xiàn)象。
豪華大片當然首推視覺藝術(shù),將吉他、歌唱、舞蹈合為一體的弗拉門戈歌舞劇,近幾年巡演了五大洲的各個中心城市。法國小說家梅里美、法國作曲家比才,仿佛化名成了西班牙姓氏;圣經(jīng)故事、英國唯美主義劇作家王爾德,也變身為弗拉門戈做了腳本。弗拉門戈舞劇《卡門》和《莎樂美》,無疑,已經(jīng)成為西班牙—弗拉門戈的兩個最響亮、最鮮艷的世紀品牌。
更有趣的是電影。這兩個弗拉門戈著名舞劇,同時也負載出西班牙兩部同名電影。電影以舞劇為題材,卻不僅僅是舞臺的再現(xiàn),一個叫卡洛斯·紹拉的天才導演,以奇特的方式肢離、解析、再造著《卡門》和《莎樂美》。
紹拉的奇特結(jié)構(gòu)方式,可稱為弗拉門戈方式。就像弗拉門戈的音樂一樣,對這兩部電影,僅僅是轉(zhuǎn)述,文字也將不能勝任。紹拉的電影,在形式的運用上,我想一定不是偶然的,它相當、相當?shù)母ダT戈——在眾多的目的中,紹拉有個目的,向世界推介這兩個西班牙歌舞,但他采用了切碎,即興,再與其他素材接合的方式。片斷化的劇外現(xiàn)實和劇內(nèi)彩排,和或短或長的歌舞場景相互交叉;主演的真實個人故事,與劇中角色的虛構(gòu)故事,交替著發(fā)展;由此形成路徑重合、分離又或彼此交叉的兩個故事、兩個卡門,一個現(xiàn)實與一個超現(xiàn)實相互錯合的影像迷宮。再現(xiàn)舞臺上的場景似乎不再是電影的重點,而劇情,呵,劇情,這可是非常弗拉門戈的劇情:
——卡門,吉卜賽姑娘卡門或弗拉門戈舞者卡門,純樸與淫蕩、愛情與利用交織難辨。她挑逗、俘獲了那個他,不管他是叫何賽的西班牙軍官,還是叫安東尼奧的歌舞領(lǐng)班,總之,她讓他瘋狂地愛上了她并不可自拔,而她卻移情別戀不受約束地愛上別人。在男人的指責中,卡門聲稱更愛自由,誰也無權(quán)阻止她的自由。如此的沖突,只有死。她明知道死亡,還是要這樣做。卡門,她不是逃,而是撲向了死亡的刀鋒,全無畏懼。
——莎樂美,巴比倫艷麗的公主,愛上了被希律王囚禁的圣徒約翰,但她的示愛被約翰拒絕。在愛與恨的雙重火焰煎炙下,莎樂美用妖媚的舞蹈和放蕩的胴體討得希律王的歡心。希律王就起愿說:“你想要什么?我都滿足你。”莎爾美說:“我要約翰的頭。”《圣經(jīng)·馬太福音之14》是這樣敘述的:
王便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給她。
于是打發(fā)人去,在監(jiān)里斬了約翰,
把頭放在盤子里,拿來給了女子,女子拿去給她母親。
愛與死,如此緊張對立,如此極端狂暴,震撼人心,不可思議,難于解釋。弗拉門戈熱愛著激烈的沖突,尖銳暴烈的對比,激蕩人的鮮血,蒸騰起熱力、熱情,轉(zhuǎn)瞬之間躍上巔峰跌入深淵,令日月忽滅,山河破碎。
四、 結(jié)句或未完成,關(guān)于愛與死的主題
弗拉門戈音樂大師是這樣幾派人物:
傳統(tǒng)弗拉門戈的大師,吉他圣手拉蒙·蒙托亞(Ramón Montoya)、帕克·德·盧西亞(Paco de Lucía);偉大的歌手“半島蝦”(El Camarón De La Isla)、“烏特萊拉的菲爾南達”(Fernanda de Utrera)。
傳統(tǒng)的革新者,將大量新舊詩歌改編成歌唱的安力克·莫然泰(Enrique Morente);歌喉中演進著復雜情緒的卡門·里納萊斯(Carmen Linares)。
“新西班牙”的明星,焊接起弗拉門戈、歐美搖滾樂與拉丁薩爾薩的卡塔瑪(Ketama);融會了弗拉門戈、歐美搖滾樂與美洲新舊黑人布魯斯的“黑腿”樂隊(Pata Negra)。
商業(yè)弗拉門戈明星提懷瑞塔斯(Tijeritas)。獲得全球成功的弗拉門戈倫巴樂隊Gipsy Kings;“吉卜賽王”是一幫吉卜賽后裔,籍貫卻屬于法國南部。
關(guān)于舞,行家們常說,最好的弗拉門戈不是專業(yè)演員,最好的舞者不是年輕姑娘。你要看的不是他們姣好的面容,曼妙的身段。就像在耳際,你最終要驚艷的也不是燦爛的技藝,飛一般的音粒。
想起西班牙,有時候我們會想起弗拉門戈歌舞,想起死亡、月亮、馬、公牛,想起風、土地、大海,想起紫羅蘭和迷迭香的氣味,想起鳥鳴和兇兆。
想起弗拉門戈歌舞,我們會想起痛苦與歡樂相抱的矛盾,想起拉扯而繃緊的愛與恨、純潔與妖邪、放縱與約束,以及在這種相反相成的糾結(jié)中生長出的一枝神秘、高傲、不可言喻的玫瑰。它是血紅的,恍惚中又是黑色的。
紅,平常;黑,平常;紅與黑在一起,就不平常。
炫耀,平常;壓抑,平常;炫耀與壓抑在一起,就不平常。
疾奔,平常;靜默,平常;疾奔與靜默在一起,就不平常。
淫蕩,平常;圣潔,平常,淫蕩與圣潔在一起,就不平常。
享樂,平常;宗教,平常;享樂與宗教在一起,就不平常。
愛,平常;死,平常;愛與死在一起,就不平常。
弗拉門戈,就是這樣吧。
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