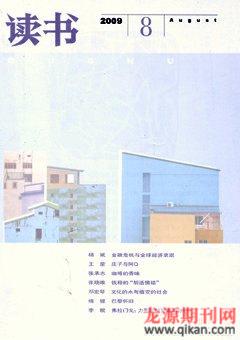海外華人移民的現代篇
李明歡
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中國學界享有盛名。眾所周知,孔教授經年耕耘于中國近代史領域,先后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叫魂》等專著,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并被翻譯成中文而廣泛傳習。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從業已駕輕就熟的清史領域轉而致力于海外華人史研究,并在歷經十余年潛心研究后,于二○○八年推出了新作:《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以下簡稱《他者中的華人》)。
根據孔教授的界定,本書在時段上囊括的是中國海外移民歷史的“現代篇”(modern times):其上限,始于一五六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其截至,終于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后的跨國跨境“移民潮”。筆者以為,該書之特點可以簡要歸納為:以大歷史的宏觀視野重新解讀中國“安土重遷”之傳統文化,以“他者”的眼光深入剖析華人與移入地社會的多重互動,高屋建瓴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移民“通道—圈”理論模型。
“安土重遷”的新解讀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歷朝統治者以各種手段將人口固著于土地之上,令其納糧當差,永做順民,因此,“安土重遷”長期被公認為中華民族的本性,許多外國學者亦接受這一說法。然而,孔教授從分析中國歷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會后果入手,對“安土重遷”提出質疑,并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實指出,雖然明清時期曾多次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實施“海禁”,但從來就沒有完全成功過。無論當時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導致其失敗的根本原因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險破戒者需要從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中獲取實際利益。由此可見,“移民”或曰“流動”實際上一直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戰略,民眾的基本需求從來就不可能通過政令完全阻止。的確,縱觀中國社會發展的漫漫歷程,普通民眾為謀生存、求發展而離鄉背井,游走遷移,史不絕書。無論是闖關東、走西口,還是下南洋,赴金山;無論是國內著名的徽商、晉商,還是名震南洋的華商僑領,無不形成于流動遷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對“安土重遷”做出了新的解讀。其一,中國文化中的“安土重遷”并不意味著固守鄉土,而是表現為即便遠離家鄉千萬里仍然保持著與故鄉故土從情感到物質的關聯。無論是為逃避迫害的被動性遷移,或是出于經濟目的的自愿遷移,無論是長久性的移居他鄉,或是季節性的往返流動,遷移者背負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興期待,他們的“家”始終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上。中國人所說的“一家人”,可能分別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萬里的不同地方,但通過經濟上的互惠仍互視為“一家人”。因此,中國人的遷移,不是與出生地和與生俱來之血緣群體的分離,而是既有聯系的地域擴展。
其二,正因為中華文化所具有的以上深刻內涵,“安土重遷”的另一面,就是“衣錦還鄉”。絕大多數從故土家鄉向異域他國遷移的中國人,其意愿多為在國外打拼一段時間后,就衣錦還鄉。而且,歷史上數以百萬計的“移民”也正是這么做的,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殊的“僑居”文化。孔教授指出,在中文當中,找不到一個能夠與英文emigrant完全對應的詞。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從自己的所在地遷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個地方”;但中文傳統“移民”的語義雖然指人的流動,卻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離與情感和經濟上的相連并存,這就是中國遷移文化的基本特征。傳統中國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緣高于一切,其價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終生歸依的那個集團之中。尤其對于從傳統鄉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無論立足于何處,其生命之根總是聯系著故鄉那個與生俱來的群體,而他的人生價值也總是希望在那個群體中得到確認。由此,“安土重遷”與“移民發展”一雙看似對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國人對于“家”和“家鄉”之濃厚情感與執著認同的基礎上,獲得了統一。
與“他者”的互動
始終將中國海外移民的大歷史,置于和“他者”的互動中進行解讀,是本書的又一特色。
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享有盛名但本人并不具華裔血統的杰出學者,屈指可數,僅就此而言,孔教授研究本身所展現的,就是以族群意義上“他者”的眼光解讀海外華人社會。恰如孔教授指出的:如果不了解海外華人身邊那些非華人的文化傳統,就難以理解他們對華人的態度,也難以理解海外華人的所作所為,因此,研究海外華人,務必關注華人周邊的“他者”,并公正反映他們的聲音。
在《他者中的華人》一書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練運用的社會心理剖析法,對華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條分縷析:從殖民統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從獨立后民族國家執掌大權的統治集團到洋溢民族主義激情的知識精英;從頤指氣使的大富豪到埋頭養家糊口的升斗小民,“華人”與周邊“他者”之間呈現出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作為外來者,海外華人需要認識了解“他者”并與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樣也時時刻刻審視著這些遠道而來的異鄉人:他們是可以和平相處、共謀發展的新朋友,還是居心叵測的異類?他們究竟是帶來新的利益和機會,還是潛在的麻煩制造者,或者簡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敵人?漫漫數百年,移民與本地人互為“他者”,彼此之間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競爭有對抗。
且以該書對東南亞華人歷史的剖析為例。
在當今大約四千萬海外華僑華人中,至少80%生活在東南亞地區。換言之,東南亞華人一直是海外華人的主體,而且,近百年來在東南亞國家屢屢出現的各類抑華政策乃至排華事件,一直是各國學人的研究熱點。孔教授的大作,同樣對東南亞華人社會投以特別關注,雖然沒有揭示新鮮史料,卻以宏觀大視野下凝練出的觀點而耐人尋味。
在孔教授的筆下,歷史上西方殖民者東來與大批中國移民下南洋之間的碰撞,是當時世界兩大文明在東南亞的因緣際會。雖然中國移民與西方殖民者同為東南亞的“外來者”,但歐洲殖民勢力的海上擴張與中華文明的海外拓展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中世紀歐洲國家在連年征戰中業已形成了對武力拓荒的制度性支持,因此,當歐洲殖民者“發現”東南亞的香料、中國的絲綢瓷器能夠在歐洲市場上獲取暴利時,當歐洲的傳教士們自認為肩負神圣使命東來傳播基督文明時,無不得到充斥著貪婪欲望之祖國政府無保留的支持,甚至不惜動用艦船槍炮掃除障礙。
反之,歷史上中國底層民眾跨洋謀生,篳路藍縷,卻因為有悖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而難以得到當朝封建政權的認可,更遑論支持。在中華封建帝國晚期,中國內部經濟、社會的系列變遷,雖迫使封建王朝不得不從務實性的角度,重新審視曾經長期處于自生自滅狀態下的中華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問題,但一直在意識形態、國家安全、經濟利益三大因素的制約下,左右躊躇。因此,當權者以國家利益為基準的考量和政策實施,與海外移民所具有的社會能動性之間的博弈,貫穿中國人五百年海外移民歷程之始終。
在東南亞殖民地時期,大量中國移民進入東南亞,與西方殖民者“開發”東南亞的需求相關。一方面,殖民者雇傭了大量華人勞工為其在東南亞各地開礦拓荒建立種植園;另一方面,殖民者還在以下三個領域顯現出對當地華人的“特殊需求”或曰“特殊利用”: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充當殖民當局向當地人斂財的代理;成為殖民時代城市化發展的人力資源。據孔教授的分析,東南亞華人如此特殊“功能”的形成,一是在殖民者眼中,華人和西方人一樣都是在“他者”的社會中生活,既與當地人無直接瓜葛,亦無鄉土根基,具有相對獨立性;二是與西方殖民者相比,華人就群體而言,在東南亞生活歷史較長,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比殖民者深廣得多,而且,華人從相貌到文化均與當地人更有相近相通之處。因此,當殖民者以武力成為東南亞的主宰后,為了固化其統治,就利用華人充當統治者與當地人之間的中介,華人因而成為殖民者雇傭承包商、收稅人的首選。
雖然真正成為殖民者御用工具的華人并不多,通過此道而得以被接納入殖民體系并大富大貴者更少,但是,由于華人處于殖民統治當局與當地民眾之間,在社會矛盾激化時作為代理人而首當其沖,因此,殖民者基于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選擇,導致當地民眾形成了“華人乃殖民同伙”的刻板印象。在東南亞獨立后尤其是民族主義高漲之際,基于族群基礎而建構的此類社會刻板印象的延伸與擴散,就成為排華事件此伏彼起的潛在動因。
以史為鑒,孔教授進而指出,東南亞獨立后當地社會反反復復出現的各種“華人問題”,就本質而言,是東南亞國家的本土問題。由于獨立后東南亞民族國家滿懷民族主義理想的社會精英們,內心深處仍然不自覺地用前殖民者的眼光去審視本國華人,認為那是一個曾經推動了殖民社會經濟車輪運行的族群,由此,在弘揚本國民族利益至上的時代,對曾為殖民幫兇之華人族群的排斥、擠壓乃至打擊,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對普通民眾所具有的煽動性,不容低估。
“通道—圈”的理論建構
倘若將本書與孔教授享譽學術圈的《叫魂》一書相比較,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手法上的改變。前者以小見大,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原始檔案中挖掘資料,從深入剖析個案入手,解讀大歷史;而《他者中的華人》則是在對前人資料成果進行重新梳理比較的基礎上,精煉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論構架,即中國移民的“通道—圈”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
孔教授指出,縱觀中國人海外移民的數百年歷程,可以看到在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長期延續著條條“通道”。此類“通道”并非如絲綢之路那樣顯現于現實的地理空間,而是經由潛在的親緣鄉緣之關系網絡編織而成。“通道”的構成元素一是實質性的,即人員、資金、信息的雙向流通;二是虛擬性的,即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靈信仰的相互交織。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穿梭來往于移入地與移出地,為移民傳遞家書錢款的個體“水客”和體制性的“僑批局”,是通道的實際載體;而到了信息發達的今日,從電報、電話、傳真到電子網絡等無所不在的通訊體系,再加上現代交通發達便捷,使得通道運作更為通暢,功能也更加多元。
與“通道”相輔相成的,是在通道兩端,即特定移民群體的移入和移出地雙雙形成的“生態圈”。在移入地,那是一個保持中國移民群體文化特色的小環境:可能是相對集中的商貿經營區或行業圈,也可能是在血緣地緣基礎上建立的廟堂宗祠、社團學校等;可能是實體性的,即形成于現實空間的“唐人街”,也可能是潛在的,即可以在需要時組織動員群體力量以采取共同行動的社會網絡。
“生態圈”在移出地的體現就是獨具特色的“僑鄉”。背井離鄉者的鄉土情懷及現實利益導向,促使他們在異鄉謀生時,謹守寄錢回家建房購地、贍養家人之天職。而且,一旦有所積蓄,往往就通過向家鄉捐贈善款,扶危濟貧,建廟立祠以提高自己的聲名,歷史上還不乏海外僑親資助家鄉地方武裝以“保衛家園”的記載。在政治上,謀生他鄉的“成功者”,更是通過買官鬻爵,與故鄉之文人、官僚匯聚一起,形成享譽一方的精英群體,參與到地方治理當中。由此,僑民、僑親、僑眷、僑匯、僑房、僑官、僑務、僑委乃至當代社團組織如“僑聯”等,構成僑鄉生態圈的基本元素,潛移默化地融入當地普通百姓的行為舉止習俗之中。
孔教授認為,在本書所探討的中國現代史時期,以“通道—圈”為標志的移民文化在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業已呈現出制度性建構,其表征主要有四。其一,移民實際上已經成為當地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只要條件允許,勞動力就會通過空間流動以尋求更高回報。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員、金錢、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間經民間通道循環往復,移民共同體業已成形。其三,移民社群深受商業文化熏陶,經商意識超越社會階級界限傳播,并且自然而然地轉化為移民謀生異域的技能。其四,移民在異地建立的鄉緣親緣會館,業緣行會,從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廟宇、宗祠等,成為移民制度構成的文化元素,由此在中國國內南下移民聚居的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形成如馬賽克般的方言習俗、民間信仰和人口結構,凸顯了這一地區成為主要移民地的特殊性,隨之,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進一步向國外流動的主要發源地。當如此移民“通道—圈”發展成為一種地域性文化后,移民就不再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是一種文化生態,因此,必須始終將通道的兩端作為相互關聯的部分結合進行研究,才能理解移民的動力、機制及認同特征,理解僑鄉社會的經濟文化取向。
孔教授的分析還指出,當客觀環境有利于移民流動時,移民通道兩端的人員、資金、文化相互交流,不斷強化移民群體從原居地帶到移入地的文化族群認同。然而,一些不利因素也可能制約乃至破壞“通道—圈”模式,例如,當原居國或目的國政府建立限制貿易和人員流動的人為障礙時,就可能阻隔通道的正常流通;又如,如果沒有新移民進入,而在移居地出生成長之新一代又因為完全融入當地社會文化當中而對祖籍地一無所知,那么,“通道—圈”就無以為繼。
可是,盡管上述不利因素在歷史上曾反復出現過,中國移民的“通道—圈”模式卻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其原因何在?對此,孔教授援引香港大學柯群英(Khun Eng Kuah)的研究進行剖析。柯群英在《重建僑鄉:新加坡人在中國》(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一書中,以從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的柯氏宗親群體為例,為我們生動描述了一個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海外移民重建僑鄉認同的典型事例。從戰后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中國與東南亞之間敏感的政治關系,在新加坡成長的新一代華裔已經淡漠了對于祖籍地的認知。然而,當中國改革開放打開與東南亞正常交往的大門之后,新加坡老一代柯氏移民即刻行動起來,推動并引領柯氏新一代踏上了返鄉尋根問祖的歸途。在與家鄉實現互助共贏的利益導向下,僑鄉記憶被喚醒,僑鄉紐帶被延續,僑鄉認同也在新形勢下被重構。據此,孔教授指出:“通道—圈”模式并不僅僅是中國第一代移民的權宜之計,而是沉淀為一種代代傳承的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跨時代的韌性,具有通過內在動力實現重生與自我完善的特性,并且在當今時代更彰顯其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博弈中的特殊意義。
《他者中的華人》以大歷史、大敘事的手筆,將中國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歷史,融會貫通于同期世界格局發展變化的大框架中,讀來令人領悟深遠。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華人移民五百年歷史精彩畫卷的基礎上,有力論證了其重要觀點: 海外華人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題中應有之意,是研究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是,海外華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Singapore: NUS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