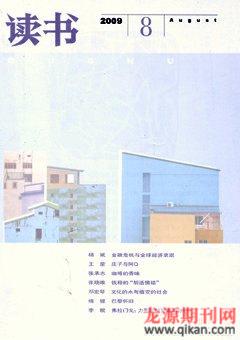視角轉換·概念建構·方法選擇
郝亞光
一九四八年生于中國上海的裴宜理,是二○○七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一八四五——一九四五年)》(以下簡稱《華北》)一書的作者。作為少有的女性學者,她以嶄新的研究視角、新穎的概念建構和恰當?shù)难芯糠椒?對中國的一個關鍵區(qū)域為什么經(jīng)常發(fā)生農(nóng)民叛亂這個問題,給予了清新、嚴密、合理的解釋。
《華北》以發(fā)生在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中期淮北地區(qū)的農(nóng)民反抗運動——捻軍、紅槍會和共產(chǎn)主義革命——為研究對象,在國家—地主—農(nóng)民的分析框架下,采用“結構—事件”的研究方法,把全書安排得非常緊湊。本書不但敘事流暢清爽、結構渾然一體,而且嶄新的研究視角、新穎的概念建構、恰當?shù)难芯糠椒ňo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往的農(nóng)民叛亂理論對現(xiàn)代革命的出現(xiàn)給予了合理的解釋,卻無法解釋傳統(tǒng)叛亂發(fā)生的原因。而裴宜理從社會生態(tài)學和環(huán)境學這一嶄新視角,發(fā)現(xiàn)在淮河流域,由于連年不斷的旱澇之災的影響,農(nóng)民的生存環(huán)境艱難而不穩(wěn)定,生活條件也異常惡劣,一種攻擊性生存策略隨之產(chǎn)生。從陳勝起義到元末紅巾起義,到明清兩代連綿不斷的社會動亂,叛亂和抵抗的傳統(tǒng)一代代地傳遞下來,地方性農(nóng)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釋成在一個特定的環(huán)境下,為了生活和生存而開展競爭活動的延伸。裴宜理正是從生態(tài)學的視角,解釋了淮北地理生態(tài)環(huán)境與農(nóng)民叛亂的關系,為傳統(tǒng)叛亂發(fā)生的原因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徑。
農(nóng)民的叛亂理論,大多數(shù)均假設農(nóng)民是馬克思所生動描繪的“口袋里的馬鈴薯”,孤立分散、軟弱無力,認為傳統(tǒng)的農(nóng)民既軟弱又缺乏組織,它們自然傾向于強調外來的人與力量在革命發(fā)生時所起到的作用。而裴宜理通過對十九世紀的捻軍叛亂和民國初期的紅槍會叛亂兩個案例的分析,發(fā)現(xiàn)在淮北生態(tài)和政治雙重危機的影響下,當?shù)剞r(nóng)民無論是采取掠奪性生存策略(如在統(tǒng)治薄弱的邊遠地帶肆無忌憚從事走私、盜匪、仇殺等活動),還是采取防御性生存策略(如絕大部分紅槍會在富農(nóng)和地主的領導下進行村莊防衛(wèi)),都反映了農(nóng)民的叛亂是一種持久的、有組織的、合理的集體行動。
國內外學者一直認為造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革命間存在“明確聯(lián)系”,如戴維斯認為,秘密會社是跨越“傳統(tǒng)”農(nóng)民反抗和“現(xiàn)代”農(nóng)民反抗的一座橋梁;摩爾、司考波爾等認為,在前現(xiàn)代化時期,造成地方反抗的結構性缺陷促成了革命的爆發(fā);一些中國學者認為,農(nóng)民叛亂的遺產(chǎn)是共產(chǎn)主義者在農(nóng)民的成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而《華北》在社會結構、生態(tài)結構的背景下,基于前文對捻軍、紅槍會叛亂的研究,歷史性地分析了淮北地區(qū)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作者發(fā)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在淮北地區(qū)遭遇了不少挫折,而當革命者適應環(huán)境以滿足當?shù)剞r(nóng)民的實際需求之后,便得到掠奪者和防御者的接納。這種接納也隨著共產(chǎn)主義運動本身的變化而發(fā)生了變化。這一變化過程證明了,現(xiàn)代革命的方法與早些時候的農(nóng)民叛亂傳統(tǒng)確實沒有多少共同之處。盡管土匪和秘密會社的支持是必要的,但兩者的聯(lián)合被證明是脆弱的,而且經(jīng)常是適得其反的。
通過對淮北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了解,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淮北農(nóng)民生活的自然環(huán)境極其不穩(wěn)定。這種不穩(wěn)定性給該地區(qū)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罩上了濃重的陰影。發(fā)展生產(chǎn)的機會受到嚴重限制,農(nóng)民要么力爭改善他們的生存條件,要么力保他們目前所用的東西。許多家庭采取了諸如控制家庭人口(如溺嬰)、借貸,或從軍、舉家遷移他處等方式,以求獲得或保持貧乏的生活資料。當這些通常的“定居式”或“流動式”治家策略失效時,淮北農(nóng)民便采取了一種特殊的、帶有更多掠奪性行為的方式。裴宜理通過對淮北捻軍和紅槍會運動的考察,把這些適用于敵對環(huán)境下的暴力建構為兩類概念:掠奪性策略和防衛(wèi)性策略。
掠奪性策略,就是以本地區(qū)其他人為代價,非法攫取資源,其表現(xiàn)形式有走私、偷竊、綁架和仇殺等。具體如:以親屬關系為紐帶的農(nóng)民,季節(jié)性流動到其他地區(qū)從事走私食鹽的非法活動,以補充農(nóng)業(yè)收入的不足;以親戚網(wǎng)絡的匪幫,常常進行小規(guī)模的盜竊活動,如盜墓、乘夜搶劫獨門獨戶的人家、在無人看管的田里偷割莊稼等,也常通過勒索、綁票獲取巨額財富,有時甚至會攻占城市;發(fā)生在家族之間和村莊之間的暴力行為——仇殺,則使農(nóng)民在群體沖突的實踐中得到訓練,獲得技能,他們的行動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更可能走向叛亂。盡管這一暴力行為具有內在的分裂性,在造反的過程中,可能會影響他們?yōu)楦鼜V泛的政治目的而進行有效的合作。
防御性策略,即面對強盜式的搶劫而采取的保護個人財產(chǎn)的行動,是作為對劫掠的一種反應。如旨在保護村莊外莊稼的看青會;為保護村莊內財產(chǎn),由富戶(紳士、地主或富農(nóng))出資、領導的民團;以及為便于地方防御,村民環(huán)村筑以圍墻,豎以柵欄而形成的堡壘式圩寨等。與掠奪式策略一樣,防衛(wèi)性的形式、強度和政治色彩都與較大的團體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正像外力可以離合土匪一樣,外力也能對防衛(wèi)團體的忠誠產(chǎn)生強大的影響力。官方的支持、提倡是地方防衛(wèi)振興與否的關鍵。當政府以苛捐雜稅的方式攫取更多資源的時候,同樣是這些防衛(wèi)性組織,也會掉轉矛頭,公開造反。
裴宜理建構的掠奪性策略和防御性策略這對概念,對淮北廣泛而持久的叛亂給予了合理、有說服力的解釋。
歷史文本研究逼近事實。本文雖是個案實證研究,但寫作時囿于中美關系還未進入正常化,裴宜理無法進入淮北地區(qū)的現(xiàn)場獲得第一手資料,而不得不完全依賴于臺灣地區(qū)、日本和美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文獻進行研究。盡管作者承認:若在研究與寫作的過程中能夠進入現(xiàn)場,自己的觀點會有很大的不同,但她從生態(tài)學、環(huán)境學這一視角對淮北地區(qū)的歷史文本進行分析,結合社會經(jīng)濟結構的演變與歷史事件去探討中國的農(nóng)民運動的研究,仍不影響其對農(nóng)民革命的深刻分析。她在若干年后進入淮北現(xiàn)場,仍為自己的正確判斷表示滿意。
社會生態(tài)研究視角別致。絕大多數(shù)研究農(nóng)民叛亂的理論都把注意力集中于農(nóng)民與統(tǒng)治者的關系上,而把生態(tài)因素放在遙遠的第二位置。如馬克思主義者多從階級的角度,認為農(nóng)民所受的壓迫達到極限時,必然爆發(fā)農(nóng)民叛亂或戰(zhàn)爭;斯科特認為農(nóng)業(yè)商品化和官僚國家的發(fā)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制,侵犯了農(nóng)民生產(chǎn)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感,迫使東南亞農(nóng)民鋌而走險,奮起反抗;也有學者從文化的角度尋找某些地區(qū)(如湖湘)多出現(xiàn)土匪的原因;還有西方學者在研究近代中國時,把農(nóng)民叛亂的原因歸結于“沖擊—回應”論等等。而作者從長時段考察淮北歷史時,把環(huán)境生態(tài)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認為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是導致叛亂頻頻出現(xiàn)在該地區(qū)的重要原因。正是作者從生態(tài)學、環(huán)境學視角,對淮北農(nóng)民叛亂原因進行長時段的成功分析,成為本書的最大看點之一。
區(qū)域史研究結論普適。區(qū)域史,又稱地方史,作為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或方法論,不但使田野調查成為可能,而且數(shù)據(jù)的種類和來源也大為拓廣。裴宜理運用此方法,把研究視野擴展到淮北一大塊區(qū)域,通過消化豐富的文本資料,把捻軍、紅槍會、共產(chǎn)主義革命三大事件置于具體的時空坐標上,即把它們放回到它們產(chǎn)生的區(qū)域(空間)脈絡中加以審視,掌握該地區(qū)域范圍內歷史現(xiàn)象的歷史性、共時性縱橫交織而成的各種具體關系之后,再逐步深入細致地探討相互扣連的歷史現(xiàn)象,與問題的形成過程、機制和意義,進而提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更具普適性。另外,我們注意到在較多的中國近代區(qū)域史研究成果中,所得出的重要概念,如施堅雅的“區(qū)域經(jīng)濟系統(tǒng)”、黃宗智的“過密化模式”、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wǎng)絡”或秦暉的“關中模式”等,大多立足于“區(qū)域”所獲的成果。
“結構—事件”論證嚴密。黃宗智說:裴著的主要特點是注重從社會經(jīng)濟結構演變和歷史事件的結合來探討中國的農(nóng)民運動,一方面是在農(nóng)民運動的歷史事件中去探討社會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在結構的變動之中去尋找民眾運動的來源和推動力。《華北》著眼于淮北地區(qū)發(fā)生在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中期的農(nóng)民反抗運動,以這一地區(qū)看似孤立,卻又有機聯(lián)系的三大事件——捻軍、紅槍會和共產(chǎn)主義革命——為研究對象,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下,裴宜理運用“結構—事件”的研究,分析了社會經(jīng)濟結構對集體暴力的模式產(chǎn)生了重要而復雜的影響,認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疏離是動亂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護使得抵御盜賊的自我防護手段成為必須一樣,匪患蔓延是因為國家控制能力的不斷削弱;同樣,在社會結構的影響下,集體暴力的模式也產(chǎn)生了復雜的變化: 不是所有的貧農(nóng)都是掠奪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樣;采取群體生存策略的成員身份以及經(jīng)常使用的意識形態(tài)理由取決于組織性的集體。正是通過“結構—事件”研究,讓讀者看清了歷史事件與社會經(jīng)濟結構演變的關系,以其存在于三大事件間的內在邏輯,給讀者留下強烈的渾然一體之感。
然而,本書最大的特點也成了最大不足。裴宜理考察了社會經(jīng)濟結構、生態(tài)結構的演變與三大事件的關系,為研究農(nóng)民叛亂提出了新的視角,證偽了傳統(tǒng)的觀點。但作者過于重視社會結構、生態(tài)結構對歷史事件的決定作用,而忽視了淮北地區(qū)的文化結構對農(nóng)民運動的影響,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跳入了“結構決定論”。正如孔飛力教授在該書出版后指出的那樣:該書不失為一部杰出的社會史著作,但必須批評其過于理性、過于功能化地探討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作者應該更多地注意紅槍會的文化因素,例如他們的信仰體現(xiàn),而非僅僅是這些體系所發(fā)揮的功能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