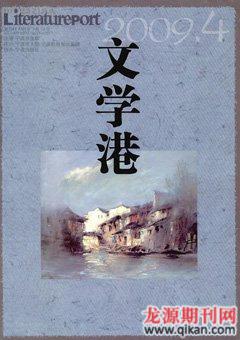長篇小說《溫暖》《三北碧血魂》研討會綜述
王 晨
《溫暖》和《三北碧血魂》是近年來我市長篇小說的新收獲。兩部小說分別由新華出版社和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在讀者中引起了較大的反響。為進一步提高長篇小說創作水平,4月22日,慈溪市文聯組織召開了“長篇小說《溫暖》《三北碧血魂》研討會”。寧波市文聯黨組書記李浙杭出席并講話。著名作家陳祖芬作了精彩點評。寧波作家、評論家楊東標、夏真、榮榮、蔡康、謝志強、趙柏田、王毅、梁旭東等出席,和慈溪作家們一起圍繞兩部小說展開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會上,慈溪市文聯主席方向明首先致辭。他說,新世紀以來,慈溪共出版了13部長篇小說,《浙東》雜志刊登了75篇中短篇小說,但還缺少有影響力的作品,需要進一步打磨,需要文學批評,以提升創作水平。“有針對性的批評,面對面的切磋,有價值的思想碰撞,對文學創作大有裨益。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批評是對文學作品優缺點的評論,批評的使命在于表達優秀讀者的意見,促使這種意見在人群中繼續傳布,就像生產需要消費一樣,文學創作也需要文學閱讀,更需要成熟和深刻意義上的閱讀——文學批評。我們正需要這樣的批評。”
會上,兩位作者分別介紹了創作情況。《溫暖》小說作者吳珍艷是慈溪龍山鎮一家電器企業的女企業主。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吳珍艷有機會接觸到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創作《溫暖》,是緣于我看到身邊眾多的兄弟姐妹,看到他們的孩子那一雙雙渴望的眼睛。”小說花7個月的時間進行醞釀,為了對農民工以及他們子女的生活、情感有更細致的描寫,吳珍艷經常跟著員工去他們的出租房,并通過他們結交了很多農民工朋友,獲得了大量的寫作素材。“一位女工向我打聽附近的民工子女學校,她說她實在受不了見不到孩子的苦,想多掙點錢把孩子從老家接到身邊來;有些夫妻倆帶著孩子出來打工,但他們的孩子往往得不到與城里孩子相同的待遇……”這些所見所聞,使吳珍艷迸發了創作這部小說的激情。
《溫暖》的封面上這樣概括全書主題:“全景式描寫留守兒童的長篇小說”。對此,有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該小說所表達的主題并不局限于此。作家蔡康說:“我覺得,其實這本書寫的不僅僅是留守兒童的故事,他們父母的人生遭遇和命運更讓人牽掛。”《文學港》主編榮榮發言認為,該小說的主題具有多樣性。“從表面上看,這是又一出當代版的紅顏薄命的故事。但圍繞著這個故事的展開,作者卻帶給了我們幾點較沉重的思索或啟示:一是當代農村女性普遍的生活境遇和命運;二是留守兒童問題;三是城里人對待打工者的態度問題。這些令人思索的問題,讓這本書有了思想的份量。”多維的主題,使當代中國社會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人性矛盾更充分地展現出來,小說從而具有了深刻的現實意義。
作為網絡誕生的小說,《溫暖》卻自覺地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進城務工人員。不僅如此,作者還通過對主人公楊春蓮的刻畫,從文化心理的角度上精確還原了這一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的精神狀態。對此,作家夏真在發言中分析道:“本書作者的高明之處,正是在于不僅書寫一個農民工進城后的困難——那樣的作品已經有很多——她更多的則是書寫了兩種文化的差異與沖突;不僅書寫了女主人公生活的艱難,更書寫了女主人公的愛虛榮的致命弱點,在她的身上,追求虛榮與割舍不下的母愛是如此畸形又如此真實地交織在一起。也正因此,她與余啟明的‘地下愛情,從一開始就是悲劇的溫床。這種弱點,不是楊春蓮一個人的,而是一個群體的。……作者似乎并不是著意描寫那種外部的沖突,而是希望通過男女主人公的命運變換與無常,寫出人物內心深處的沖突,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沖突,這種內在的沖突顯然要比外部的沖突更為深刻。”這種通過內部沖突表現人物的手法,使小說的人物塑造呈現動態性。《文學港》主編榮榮這樣評價小說的人物塑造:“作者讓這些主要人物隨著生活場景的變化,他們的性情和為人處事的態度都有所改變,這顯出了作者阿杰的寫作能力。長篇小說最忌諱的是人物不成長,而阿杰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好。”
小說還對進城務工群體的衍生——留守兒童的生存現狀做了透視:“留守兒童問題。這也是作者寫這部書的出發點和動力。她主要寫了乖巧聽話的劉立夏和任性刁蠻的余婷婷,一個非常懂事優秀,一個因太嬌寵條件太優越而導致孩子心理上有某種欠缺,一個是農村的,一個是城里的,這也是留守兒童里兩個較極端的例子。相對來說,農村留守兒童的生活與教育問題,更是令人擔憂的,這也是當前比較突出的農村問題之一。目前要從跟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好在全社會已在共同關心這件事。我想,通過描寫這些兒童的生活,讓更多的人來關心幫助這些兒童,這也是作者良好的愿望所在。”榮榮說。
作為一部關注現實的作品,《溫暖》在情節上同樣引人入勝。“沒想到,一拿起就放不下了,可以說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這部25萬字的長篇小說。……一部長篇小說能寫得讓人讀了放不下,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蔡康說。榮榮則對溫暖的“好讀”進行了深入分析:“故事層層推進,有懸念,細節合理,這也是本書好讀的原因。我舉兩個例子,一是楊春蓮懷上了立夏,她不得不找老實的可信任的劉麻子嫁了,后來才有了整個故事。隨著故事的發展,所有的人物,作者讓他們的所作所為看上去都稱得上水到渠成。還有一個楊春蓮出軌的情節,作者也非常微妙地作了交待和鋪墊,比如楊春蓮來到城里人的世界,也是她唯一的戀人所在的世界,內心是很復雜的,看著城里繁華的一切,她常常有這樣一些想法,即城市的這一切美好,本來也會有她的一份,也正因為有這種想法,讀者就很好理解她與東家余啟明的外遇了。”
對于《溫暖》的整體價值,作家和評論家們都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夏真說:“作者從女性角度出發,寫活了當代農民工與留守兒童,顯現了艱難生活中一抹亮麗的溫暖。”胡遐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溫暖》的贊許:“《溫暖》是近幾年來,我市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新高度!”
與《溫暖》反映關注當代不同,《三北碧血魂》則反映歷史。這部小說的作者張文勤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的根基,又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他創作該書時已年近古稀,卻以頑強的意志完成了這部二十萬字的小說。張文勤談到,在創作小說時,他先用鉛筆寫,然后一個字一個字打進去,一遍一遍改,共改了五遍。這中間,每一稿都請人看。在研討會上,滿頭白發的張文勤專門把五本厚厚的底稿帶來給大家看:“寫作的過程,對我而言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許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事情,通過這次創作,讓我知道了,了解了。”張文勤說。作者的執著也感染著現場的每個人。作家王毅說:“作者的這種精神難能可貴,是值得我本人,也包括許多作家學習的。”作家趙柏田說:“一個近七十歲的老人,以一種罕見的熱情,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寫下了這部革命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這沒有一種信念的支撐是無法完成的。”正如作家戚天法在該書序言中所言,《三北碧血魂》是作者“頑強生命涌泉的蓄勢噴發,更是人生使命感的集束呈現。”該小說凝聚了作者的心血。
小說以浙東工農紅軍第一師師長費德昭為原型,以1927年至1937年三北民眾在黨領導下開展革命斗爭為主線,書寫了這塊土地的英雄傳奇。趙柏田說:“在作者身上,當他動手寫這個故事,我想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感的驅使,他覺得有必要寫出曾經在這塊土地上浴血戰斗的共產黨人的英勇事跡,用作者的話來說,這種沖動就是‘對先輩英烈的崇敬和思念之情”。同時,趙柏田從這個角度出發,認為作者這種創作方式“往淺里說,他是很好地呈現了地域文化風情,實際上他本身就在這個文化里。所以他寫的那些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切實可信了。”評論家梁旭東說,“《三北碧血魂》是一條精神紐帶,讓我們在重溫先烈們的英勇業績之際,傳承了他們的紅色血脈與理想主義精神。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北碧血魂》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具有題材上的優勢,洋溢著英雄主義的激情。”
在討論中,與會者普遍注意到了小說中生動的地域文化描寫。梁旭東先生說:“在藝術上,這部作品有著濃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對于當地風土人情的描寫,更可見作者有著深厚的生活功底。”浙江省作協副主席楊東標說:“小說雖然寫的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殘酷的革命斗爭故事,但故事發生地的三北,其風俗人情表現得非常濃郁,如春風化雨滲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間,讀起來有一種親切感。杭州灣畔的海涂、鹽田,棉田上辛勤勞作的棉農,正月十三廟會時的舞龍、高蹺以及火龍戲珠時噴出的火焰,‘斷七祭奠儀式上的白燭酒香以及油炸沙蟹,甚至連胡叢昭當羊倌時在山林上放養時的一草一木,以及農家的雞籠羊圈,作者寫得娓娓動人,形象逼真。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只有長期生活在三北這塊土地上,才能寫出具有三北地域特色的文字來。”作家謝志強從文化角度解讀小說,強調民俗描寫在小說中的重要性:“與其說那是一場革命戰爭,倒不如說更似一場文化的戰爭。每次進入民俗的文化現場,人物就融入其中,而且借助、利用、啟動民俗的文化達到勝利的目的。”“從文化角度看,飽含著文化的農事、物產、節氣超越了戰爭和人。所以我感謝作者,用文學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之‘魂。”方向明評價該書“既是一部動人的傳奇故事,更是一部慈溪風俗的百科全書”,這是不為過的。
討論中,王毅分析了小說的語言:“作品的語言樸實無華,一些富有地域色彩的口語運用自如,例如,‘放著好好的官不做,硬要做出頭椽子,領著一幫窮光蛋造反,這種生活化的語言比起那些干巴巴的‘書面語來,無疑更有鮮活的生命力。”楊東標提到,這部小說的語言是帶著鄉土特色的,“一些當地的方言諺語都被作者吸收來溶入作品之中,如‘六月六,貓狗凈場浴,‘梅雨天,孩兒臉,一日變三變等等富有濃郁的農村氣息”。同時,楊東標還對小說精彩的戰斗場面也進行了點評:“戰斗場面寫得十分生動。如智取虎山鎮、襲擊黃家埠、火攻庵東、巧斗蜀山警察所等等,激烈的戰斗,一場又一場,讓讀者關注著戰事的發展,人物的命運。可以看出,作者是非常熟悉這些戰斗生活的,每次戰斗都寫得懸念迭起,如箭在弦,絲絲入扣,大開大闔。而且,各具特色,互不雷同。就戰斗形式而言,有巷戰,有火攻,有圍城,有水遁,有瓦上居高臨下,還有唇槍舌戰。可謂形態各異,精彩紛呈。”作家和評論家們對《三北碧血魂》的章回小說的痕跡、紀實筆法的得失、人物塑造的優劣等也進行討論。
在肯定兩部小說價值的同時,作家和評論家還對兩部小說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蔡康對《溫暖》中立夏這個人物的塑造有不同的觀點:“立夏作為留守兒童的典型意義似嫌不足,也許是她的獨特的人生命運掩蓋了她作為留守兒童的普遍特性,因此她只能成為留守兒童中有特殊意義的‘這一個。”還有許多專家學者都提到了《三北碧血魂》中胡叢昭就義之后情節松散的問題。謝志強先生做出了這樣的設想:“縱覽全書,前三章緊湊,后兩章松散。試想,故事到達‘保釋這個情節就收尾會如何?”
在寧波的作家、學者評論之后,慈溪作家代表先后發言。作為《三北碧血魂》作者的老友,吳伯洪是這部小說的第一個讀者。他認為原創、本色、正氣是這部小說的三個特點。吳伯洪說:“老張的文學實踐,必將鼓舞更多的本土文學青年,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慈溪作協名譽主席周乃復提出,盡管藝術風格截然不同,但兩部小說在題材上都有所開拓,《溫暖》關注了留守兒童這個超前的社會問題,而《三北碧血魂》則是選擇了逐漸被人冷落的革命題材。他認為,要寫出好的小說,“關鍵是你有沒有生活,關鍵是你對生活有沒有一種激動。”作協副主席俞強發言說:“兩部長篇對慈溪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來說,無疑注入了蓬勃的生機與新的希望,成為近年來慈溪作協乃至整個慈溪文藝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會議中,著名作家陳祖芬女士作為這次研討會的嘉賓,對兩部作品進行了評價。對于《三北碧血魂》的作者,陳祖芬表示出了敬意。“張文勤先生的人生,就是中國式的人生,作者年方70寫成長篇小說,是令人感動的。”陳祖芬女士認為這部小說民俗和情節融合得十分自然,比較適合改編成舞臺劇劇本。評價《溫暖》時,陳祖芬首先肯定這是一部好看的小說。“好看是小說的基礎,作者很會編故事,是一位有潛力的作家。”同時,陳祖芬說,小說中楊春蓮的人物變化很可信。“小人物折射大時代,通過一個人的掙扎,作者寫出了一個時代的變遷。”
研討會最后,寧波市文聯黨組書記李浙杭做了總結講話。李書記說,慈溪是一塊有著豐厚文化積淀的土地,很好地保存著傳統文化的精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勤勞,有商業頭腦和創業精神。這種傳統一直影響到了當今慈溪的文化精神。但目前慈溪還缺少在全國、全省有影響力的作品。這片土地上應該出現大家,出現厚重之作。慈溪市文聯舉辦這兩部長篇小說的研討會,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會上,李書記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作家要有責任感,選材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第二,作家要通過各種方式感受生活,從而獲得源源不竭的創作沖動。第三,寧波市各級文聯、作協要為文藝工作者做好服務,類似的交流活動以后還要繼續開展。
這次研討中,不同的文學思想彼此補充,各種的創作理念相互碰撞,這也為慈溪小說的創作者帶來了新的思路。正如李浙杭書記在最后總結時所說,相信在作者創作激情的推動下、經濟基礎的支撐下、文聯和作協的引導下,慈溪的長篇小說創作終會經歷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責編 榮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