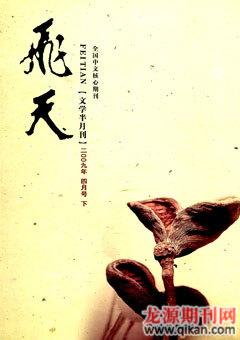一唱三嘆 紆徐含蓄
許性紅
作為宋代杰出的散文作家之一,歐陽修有他獨特的藝術風格。他不論寫說理或敘事文,都帶有濃厚的抒情色彩,通過一唱三嘆的表現手法,以其強烈的藝術魅力來打動讀者,使人們自然而然接受了他的觀點。《五代史伶官傳序》就是體現這種特定的藝術風格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前人認為歐陽修這篇史論性的序言最得司馬遷《史記》的精髓,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代史伶官傳序》全文體現著潛移默化的藝術力量。這種藝術風格的形成和藝術效果的產生,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作者是站在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企圖借古喻今,為當時和后世的皇帝如何治理天下設想,才寫這篇文章的。他對一個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強大、興盛、成功和統一,是衷心期望和全力歌頌的;而對一個做皇帝的人由腐化、垮臺、失敗而亡國,則表示了由衷惋惜,并感到深切痛心。他寫這篇文章就是希望封建統治者能以后唐莊宗李存勖為鑒,要吸取他發憤圖強的成功經驗,卻萬不可蹈他縱情聲色的覆轍。所以,他在發表意見時,是以對封建皇帝由成功而失敗抱有十分惋惜同情的思想感情為出發點的,對成功的經驗倍加贊揚,對失敗的教訓再四提醒。然而,讓皇帝引為借鑒的文章是不宜寫得過于明目張膽的。于是他把警告、戒飭這方面的意見說得比較曲折宛轉,表示他是在進行善意規勸諷諫而不是出于破壞性的揭露諷刺。我們說,歐陽修的這篇文章突出表現了一唱三嘆的手法和風格,這同他思想感情的出發點和寫文章的意圖、態度是分不開的。
第二,這篇文章的主題,歸納起來不外乎三層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亂興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這是全篇的主干。其次,所謂“人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和“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總之,目的在于說明封建統治者為什么成功又為什么失敗。這道理并不難懂。但如果作者只把這幾句話作為總結性意見直接說出來,便成為老生常談,沒有什么說服力。因此,必須用感性材料來充實、論證這個觀點。作者通過李存勖死于為自己一向寵幸的伶人之手的史實來說明這個問題。可是我們看問題并不能如此簡單。李存勖一生經歷復雜,事跡多而頭緒亂,接觸面也很廣,死于伶官謀反,只是他的最后結局,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歷史。況且李存勖由勵精圖治轉為荒淫腐化,伶人由受寵幸到專權,終于造反弄死皇帝,這在作者所撰寫的這部歷史著作《新五代史》里已有詳盡記載,沒有必要在這篇短序中重復。因此,為了闡明本篇的主題思想,作者的選擇材料既有重點,又得避免重復。這就非得有提綱挈領、駕馭史料的能力不可了。不僅如此,作者還得把史料運用得有囊括古今的概括力,有舉一反三的啟發性,才能達到用史料論證觀點的目的,起到引古鑒今的作用。作者在這里,既要體現出一個歷史家所應有的客觀冷靜態度,又要實事求是,公允正確地表達作者個人對本階級的統治者的見地和感情。這一點,歐陽修是做到了。歐陽修這篇文章誠然是學《史記》的,但他所繼承的是司馬遷修史的精神,而不是字模句范地追求《史記》行文的外貌;是學習《史記》選擇史料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方法,而不是亦步亦趨地生搬硬套司馬遷的風格和語言。
第三,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不僅要從著作中見出作者的思想見解,還須體現出作者能鑒別史料的眼光。歐陽修在這篇文章中既要用史料來論證觀點,又要使說理內容飽含感情成分。那么,對史料的要求必須選擇形象性很強的內容。史料越具形象性就越容易打動讀者、感染讀者,越能把作者的觀點表達得深入淺出,使人得到更多的啟發和體會。作者是有文學創作才能和經驗的,他體察到,只用普通的史料可能是不夠的,于是他選擇了民間傳說。他引用了北宋初年王禹傅《五代史闕文》里的一條材料,那就是晉王李克用f臨終把三枝箭做為誓物留給了李存勖的故事。這個故事原文有一百四十字,經過提煉剪裁,歐陽修把它壓成一百字。原文的枝葉重復處被刪掉了,卻加強了故事的抒情氣氛和李克用遺囑的懇切語氣。這就使文章增加了魅力和光彩。別外,我們還要注意的是,這一傳說不一定完全可靠,寫入史傳正文,可能有問題;但這個故事流傳又極為普遍,割愛也不是辦法。作者把它寫入序文,恰好兩全其美。這就表現了歐陽修做為一位封建歷史學家的卓越才能。
下面再從本篇的語言技巧來分析一下,看看作者是用什么具體手法來表現這種一唱三嘆的藝術風格,并十分成功地傳達出他的思想感情的。
首先,作者對自己所要表達的主題,做了最大的概括,那就是前面說的三層意思。然后根據這個主題的內容,又選擇了一系列十分精確的對稱性的詞匯,用它們把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史料貫穿起來,即“人事”、“天命”、“盛”、“衰”;“得”、“失”;“難”、“易”;“成”、“敗”;“興”、“亡”;“憂勞”、“逸豫”等等。這就使主題特別醒目,觀點特別感人。
其次,對于史料,作者也做了高度的概括。除引用了一個民間傳說外,序文中把李存勖即位以前的兩件武功扼要地描述了一下(三矢的故事只交代了兩件事的結果,這是文章剪裁得當,有虛有實之處),作為“憂勞興國”的正面事例;然后寫到皇甫暉兵變,“一夫夜呼,亂者四應”,以及“君臣相顧”、“泣下沾襟”的種種狼狽相。盡管是點到而止,并沒有展開場面和細節的描寫,可是文章的抒情氣氛已被渲染得很成功,讀者從這種形象化的點染中已完全接受了作者對李存勖所下“何其衰也”的結論陛的判斷。第三,為了使抒情氣氛濃烈,作者較多地運用了感嘆句和反問句,這一點從文章一開頭就表現得很明顯、很突出。試想,如果作者把“嗚呼”這一感嘆詞去掉,然后把“盛衰之理”三句改成“治亂興衰皆由人事”一句話,道理還是那個道理,可是讀者讀上去就不會那么受感動,文章自然也收不到應有的一唱三嘆的藝術效果了。同感嘆旬和反問句相配合,還要注意到文章的波瀾起伏。感嘆句和反問句必須用得含蓄有內容,有較大的概括力,否則便容易形成空泛浮夸、無病呻吟的唱嘆,和矯揉造作的反復曲折。如結尾的“豈獨伶人也哉”,既是感嘆句又是反問句,既含蓄而又有較大的概括力,這就起到了“綰攝通篇”和“包舉全局”的作用,給讀者帶來了廣闊的啟發性,使人們產生更多的聯想。古往今來,促使一個政權垮臺,甚至搞得國亡家破,難道只由于“伶人”這一個因素么!只有這樣寫,才會有引古鑒今的意義,看似虛寫,卻包涵著豐富的內容。然而這樣的句子必須同表達主題思想的關鍵詞句有著密切關聯,才能產生藝術效果。如開頭三句以下立即接入“原莊宗”三句;結尾“豈獨伶人也哉”的上文又必須緊接“夫禍患”兩句正面判斷式的排句,才顯得有力量,才不是濫調,而主題的啟發作用和教育意義才體現得更鮮明、更強烈。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反問句必須同正面語氣的句子配合使用,不宜用得太多,才能恰到好處。比如“何其衰也”是反問句,但它是同前面的正面感嘆句“可謂壯哉”相配合的,一正一反,相反相成,才起作用。如果前面也用“豈不壯哉”,那就成為濫調了。
最后,從句式上看,歐陽修是慣于運駢入散或以散破駢的,本篇和《醉翁亭記》,這方面的特色都比較明顯。本篇凡最關鍵的足以點明主題的語句,作者都用精煉而形象的四字、六字句即駢儷句式來描寫,借以加強節奏感,使文章有氣勢、有力量。但在一唱三嘆處卻又盡量使用語氣句,使文句由駢而散,以避免程式化。作者巧妙地把駢體和散體的對立關系給統一起來了。
總之,這篇文章無論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技巧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如作者強調“人事”重于“天命”,主張“憂勞”而反對“逸豫”等,對今天還有啟發意義;如何選擇史料來論證觀點,如何使說理文帶有濃厚的抒情成分,也值得讀者參考。特別是做為一篇“序言”,寫得如此精煉含蓄,深入淺出,就更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