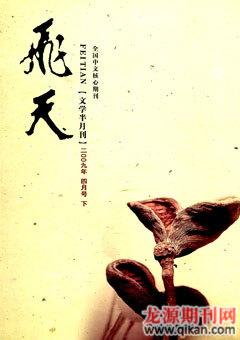靈魂選擇自己的伴侶
盧曉白
艾米莉·狄金森(1836-1886)是美國19世紀(jì)杰出的女詩人,她創(chuàng)作的詩關(guān)系到自然、生命、死亡、愛情和永恒,表現(xiàn)了女性特有的思想和情感,揭示了一個孤獨、充實、安寧、執(zhí)著的靈魂。她那樸素又含蓄的詩句,感傷又幽默的詩風(fēng)使她成為美國民族詩歌藝術(shù)的豐碑。她的詩作,是美國人民的珍寶,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財富。狄金森被稱作“與惠特曼同是美國詩歌成就最高的人”。
一、狄金森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及風(fēng)格
狄金森受愛默生“自然論”的影響較深,但她在詩歌的表現(xiàn)形式上并不模仿任何人,有著自己獨特的風(fēng)格。她把詩人置于宇宙中最高尚的地位。她說:“詩人——照我算計/該列第一,/細(xì)節(jié)然后,太陽——/然后,夏季,然后,上帝的天堂——/這就是全部名單——”她對詩的定義極其獨特:“如果我讀一本書時,全身浸透了涼意,什么火也不能溫暖我,我知道那便是詩。”她認(rèn)為詩歌應(yīng)表達(dá)真善美,堅信“美不能造作,它自然——/刻意追求,便消失——/聽任自然,它留存”。她主張要說出全部真理,追求真理,認(rèn)為詩歌必須賦于思想,她不能想象,“人怎么可以沒有思想而生存?”認(rèn)為詩歌是人情感的釋放,具有使人獲得安慰的功能。
狄金森不受傳統(tǒng)的制約,堅持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她摒棄了當(dāng)時書卷氣的詞藻,采用通俗易懂的日常用語,她的語言,一洗鉛華,不事雕飾,質(zhì)樸清新,有一種“粗糙美”,有時又有一種幼稚的特色。她的語言濃縮到了極點,簡潔如電報;她無視語法、句法、大寫、標(biāo)點等傳統(tǒng)文字表達(dá)規(guī)則;她突破傳統(tǒng)格律,大量運用破折號以示過渡、省略及跳躍起伏;她還經(jīng)常在句中大寫以示強(qiáng)調(diào);她的詩歌沒有標(biāo)題,像謎一樣;在韻律方面,她基本上采用四行一節(jié)、抑揚格四音步與三音步相間,偶數(shù)行押腳韻的贊美詩體。但是這種簡單的形式,她運用起來千變?nèi)f化,既不完全拘泥音步,也不勉強(qiáng)湊韻,押韻也多押近似的“半韻”或“鄰韻”,有時干脆無韻,實際上已經(jīng)發(fā)展成一種具有松散格律的自由體。
二、狄金森詩歌賞析
(一)揭示死亡和永生
狄金森短暫的一生中曾多次經(jīng)歷失去摯友和親人的痛楚,由于友人早逝,愛情失落,她經(jīng)歷了異常艱辛的生命體驗。悲痛促使她對“死亡”和“永生”作更深入的探索。對孤獨一生的狄金森來說,死亡無疑是最令她心靈震撼的。在詩里,她不止一次地從特殊的視角來描述她想象中的死亡全過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因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他殷勤停車接我——
車廂里只有我們倆——
還有“永生”同座
我們緩緩而行,他知道無需急促——
我也拋開勞作
和閑暇,以回報
他的禮貌——
我們經(jīng)過學(xué)校,恰逢課間休息——
孩子們正喧鬧,在操場上——
我們經(jīng)過注目凝神的稻谷的田地——
我們經(jīng)過沉落的太陽——
也許該說,是他經(jīng)過我們而去——
露水使我顫抖而且發(fā)涼——
因為我的衣裳,只是薄紗——
我的披肩,只是絹網(wǎng)——-
我們停在一棟屋前,這房子
仿佛是隆起的地面——
屋頂,勉強(qiáng)可見——
屋檐,低于地面——
從那時算起,已有幾個世紀(jì)——
卻似乎短過那一天的光陰——
那一天,我初次猜出
馬頭,朝向永恒——
這首詩被稱贊為用英語寫的最好的詩歌之一。詩人使用擬人的手法,將死神化身為一位紳士,邀請作者和“永生”坐進(jìn)四輪馬車。詩人用象征手法,概述人一生中由幼小至老死的經(jīng)歷。“學(xué)校”、“稻谷”、“沉落的太陽”意味著從生到死,成長孕育著衰落,生命蘊含著消亡。這首詩雖然對死亡和永生有一種無限迷惘的感覺,卻表達(dá)了作者向往永生的愿望。表現(xiàn)了詩人對生命的無限熱愛。“與其說這組詩是寫死亡,還不如說是寫永生”。
在詩人心中,如果死亡不是人生的一個終結(jié),至少是一個重要階段,對死亡的思考也就成了詩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狄金森總是保持客觀冷靜、不動聲色的態(tài)度,敘述死亡發(fā)生的過程。如:“正是去年此時,我死去。/我知道,我聽見了玉蜀黍,/當(dāng)我從農(nóng)場的田野被抬過——/玉蜀黍的纓穗已經(jīng)吐出——”
雖然狄金森始終懷疑人死后是否真能進(jìn)入天堂,達(dá)到永生,但她總希望死亡是通向永生的捷徑,她的詩歌總讓人感覺到死就是生的另一種形式。只有通過死亡才能投入永生的懷抱,才能達(dá)到永恒的狀態(tài)。她對永生的贊頌,揭示著生存與死亡原本就是生理的本我人格的本能這樣一個事實。
(二)感悟自然和生命
自然是狄金森詩歌的一大主題。在她早期作品中,自然是和諧、令人神往的所在,是靈魂獲得慰藉和營養(yǎng)的源泉。狄金森的詩短小精悍,遙遠(yuǎn)和重大的事物都被卑微和熟悉的意象表現(xiàn)出來。在詩人縮小的世界里,微小的東西可以幻化成巨物,她寫自然如家園,常有細(xì)致入微、準(zhǔn)確生動的描繪。有些平凡的景象,在她筆下總能使人感受到一種無可置疑,確實存在,而又不曾為常人意識到的美。
蟋蟀唱歌,
太陽西落,
工人們一個個,
結(jié)束了日課。
短草馱著露珠,
黃昏像生人那樣站著,
手里拿著帽子,恭敬而怯生,
仿佛欲留還去。
在詩人的眼里,大自然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人類的智慧無法認(rèn)清自然的全貌。生命的美好在于我們知曉生命“轉(zhuǎn)瞬即逝,不可復(fù)得”。通過自然這一主題,狄金森表達(dá)出對生命的熱愛,對大自然奧秘的探索,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對人生沉浮的態(tài)度。她對自然規(guī)律的無情和不可避免的生命更迭發(fā)出感慨,認(rèn)為自然既慈祥又殘忍。生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上帝默許這一切發(fā)生。狄金森借自然的變換如夏天的消逝表達(dá)她的感覺及觀點。
像必然離去的客人,
不需翅膀,
不用雙腿,
我們的夏天無聲無息
升入美麗的天堂日。
狄金森熱愛生活和生命,試圖多側(cè)面、多層次地探索、解釋和表達(dá)生的意義。這是她的情懷。也是她熱愛生命、向往永生的見證。
(三)關(guān)注愛情與情感
愛情是狄金森詩歌的永恒主題。狄金森一生經(jīng)歷了幾次沒有結(jié)果的戀愛,終生未嫁,但以極大的熱情關(guān)注愛情這一主題,筆下不乏浪漫的愛情詩篇,她寫道:“愛,先于生命——/后于死--/是創(chuàng)造的起點——/是世界的原型。”她敢于直言愛是人類的天性,是自然不可阻擋的情感。認(rèn)為“直到有了愛——男人和女人才成為自己”。她在詩歌里編織出對愛情的追求和對伴侶的渴望:“我一直在愛,我可以向你證明,直到我開始愛,我從未活得充分/我將永遠(yuǎn)愛下去/也可以向你論證/愛就是生命,生命有不朽的特征”口。
愛情是狄金森“本人的神秘的核心”。她將愛比作無價珍寶。“為了擁有它,她會以整個生命作代價。”為了它,她不但付出了生命,而且付出了她的靈魂。
沒有結(jié)果的感情令狄金森無比痛苦,卻也給了她無窮的創(chuàng)作源泉,她把愛投入到詩歌的世界,“打掃干凈心房,收拾起愛情,我們將不再使用,直到永恒”。雖然狄金森一生都在渴望和追求愛情,但她寧可終生不嫁也不屈從于世俗的愛情。她用一首“靈魂選擇自己的伴侶”表達(dá)了獨立的愛情觀:“靈魂選擇自己的伴侶/然后,把門緊閉/她神圣的決定/再不容干預(yù)”。
愛超越了生與死;愛是一個確定的信仰,支撐著她的生命,升華了她的靈魂,豐富了她的詩歌。正是這樣強(qiáng)烈的信仰,成為狄金森內(nèi)在生活的神秘的實體,成為她詩歌的主旋律。有批評家說:“從來沒有一位涉世不深的人能如此強(qiáng)烈地感受痛苦與歡樂,很少人能像她那樣了解愛情和死亡而又存活下來。”
狄金森的一生是不斷追求自由和自我實現(xiàn)的一生。詩歌是狄金森抒發(fā)情感的聲音,她用心靈編織著永生的夢幻,用頑強(qiáng)的意志譜寫著一首與死亡搏斗的生命之曲。她在詩歌中創(chuàng)造自己的精神家園,由此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圓滿。閱讀她的詩,我們深深感受到一個孤獨而高貴的靈魂,感受到詩人熱愛人類的崇靜情懷,更加了解生命的價值在于追求真和美,追求愛情和自由,追求永恒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