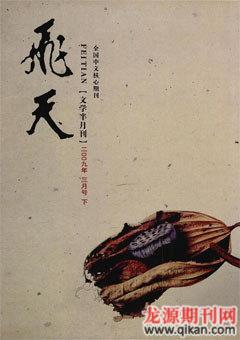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傳播
劉文榮 劉紅艷
所謂傳播,即社會信息的傳遞或信息系統的運行。文學傳播是文學生產者借助于一定的物質媒介和傳播方式賦予文學信息的物質載體,將文學信息或文學作品傳遞給文學接受者的過程。文學信息自然是社會信息的一種或者說是屬于社會信息系統的,二者之間存在著包含的關系。這是從二者概念上的比較得出的。在現實的文學傳播活動中,文學傳播的載體大多是大眾傳媒,文學傳播的受眾與大眾傳媒的受眾也存在著很大的重合。隨著電子媒介技術的高速發展,大眾傳播和文學傳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文學傳播的受眾越來越帶有大眾傳播受眾的特點,作家越來越貼近商品生產者的角色,這一切預示著文學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
從文學的發展來看,任何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學都不可能脫離傳播而獨立存在。縱觀我國的文學發展史,不同時代使用不同的文學傳播工具。人類傳播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時期:口頭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媒介傳播時代。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屬于口頭傳播文學,經后人記錄到某些媒質上才流傳到今天。因其只靠口口相傳進行傳播,充分體現了口頭文學的特點:語言淺顯,讀起來朗朗上口。唐宋雕版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文學作品大規模傳播和復制提供了可能,直接推動了唐詩宋詞的發展繁榮,文學作品更多的流人“尋常百姓家”。印刷媒介也為后來明清小說的興盛、五四時期文學的發展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個時期文學已帶有明顯的審美特征,甚至可以干預政治,推動民主、自由的發展。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了電子媒介傳播時代,文學的傳播除了依靠傳統的印刷媒介,廣播、電視、網絡成了文學的主要載體。這是一個“文學狂歡”的時代,文學戴著“高度繁榮、自由、民主”的面具,寫作不再是作家的特權,文學不再是高雅、神圣、崇高的代名詞,她從神圣的殿堂走向大眾狂歡的廣場。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對傳播媒介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做過一個高度的概括,也就是他提出的“媒介即訊息”觀點: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訊息。“人類有了某種媒介才可能從事與之相適應的傳播和其他社會活動。”當然麥克盧漢這里的“媒介”是廣義的,而不僅僅指“文學”,但是文學信息傳播作為社會信息傳播的一部分,大眾傳媒的發展對其有著深刻的影響。
新時期文學傳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傳播媒介的多樣性和豐富化。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激光排版、電腦編輯、網絡傳輸等技術廣泛運用,與曾經小作坊式的手工作業生產已不可同日而語了。走進書店,一本本印刷精美、質量上乘、散發著淡淡油墨香的圖書很快就能攫住人們的“眼球”,頗有“先發制人”的氣勢。除了傳統印刷媒介外,文學又搭上廣播、電視、網絡的羽翼,在電子媒介提供的無邊世界自由飛翔。
電子傳媒技術上的優勢大大加快了文學傳播的速度,為文學提供了更多的載體,“復制”功能為文學大面積的傳播創造了機會。傳統上。一個文學活動的完成,要經過作家創作、編輯審稿、出版媒體發表、到讀者完成閱讀四個步驟。而網絡文學,從作者創作到讀者接受,幾乎可以同時進行,網絡文學作者可以邊寫作,邊發表,輕點鼠標,作品便可與網絡讀者見面,沒有傳統投稿后焦急的等待。沒有被拒后的沮喪,作者可以充分享受隨心所欲創作的快感,并且馬上得到讀者的反饋。但這種“個性化”、“游戲性”、“自由”的寫作和傳播方式也必然導致作品質量的下降,作品題材單一,缺乏思想深度,內容單調,有的甚至走向“低俗”。總體上來看,網絡文學作品雖然“物產豐富”。但“精品”卻少之又少。
影視文學是影視與文學相結合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大量的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并且大獲成功,“名利雙收”。很多小說,改變成影視作品之后,實現了由“無人問津”到“洛陽紙貴”的轉變。以張藝謀的電影作品為例,由莫言同名小說改編的《紅高粱》。陳源斌《萬家訴訟》改編的《秋菊打官司》,因其在國際上獲獎而揚名海內外。小說作者也都跟著“水漲船高”。90年代以后,影視與文學的“合作”更為密切,二者互為資源,都賺得個“盆滿缽滿”。雖然影視為文學的普及立下汗馬功勞,但影視畢竟是“視聽”藝術,這種藝術的形式決定了受眾欣賞影視作品時的凝滯狀態,無需主動思考,直接被聲音和圖像“牽著鼻子走”,而文學作品的閱讀則是在文字符號的基礎上調動思維和想象,從而獲得充分的審美感受。與90年代以前的影視作品追求藝術化不同,90年代以后的作品更加商業化,利潤最大化是制作商的直接目的,在藝術與金錢的追求上,二者無法達到平衡時,首先犧牲掉的是文學的藝術性。這必然導致作品改編后“文學性”的降低。由此可見,媒介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一方面拓展了文學傳播的渠道,使大眾有了更多的接觸和感受文學的機會,另一方面,這種“接觸”與“感受”是淺嘗輒止的,停留在表面的,與深入感受文學的魅力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也是大眾傳媒時代文學傳播所面臨的尷尬境地。
“文學從來就沒有一個共通的本質而超時代地存在著。”作為大眾傳播時代的文學傳播,與以往相比,也呈現出了新的態勢和特點。傳媒的每一次發展進步,都帶來了文學傳播樣式、文學觀念、文學生存狀態的改變。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到大眾傳媒時代文學命運的問題,如何在大眾傳媒時代承傳文學的“薪火”,是這個時代留給我們的思考。